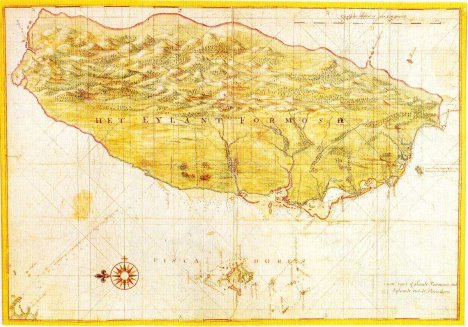作家陳芳明:《福爾摩沙三族記》是一部多元史觀的小說,但又可以當做歷史作品來閱讀。 作者陳耀昌自己則說:《福爾摩沙三族記》或許才是我對母親台灣的最大回報。這本書,如果沒有我的成長背景──出身府城老街、與陳德聚堂的淵源,也夠LKK,還來得及浸潤於台南的古蹟氛圍與寺廟文化;又正好身為醫師,懂得一些DNA及疾病鑑別診斷知識──其他人不見得寫得出來。 陳耀昌醫師這本巨著,之前曾在新頭殼〈開講無疆界〉欄目中刊載,新頭殼這次重新編排以系列推出,以饗讀者。
今天是烏瑪大喜的日子,從今天起,她和直加弄就可以互稱「牽手」了。
烏瑪穿起她最漂亮的衣服,頭戴著檳榔花和雞冠花編成的花圈,嘴角含笑,卻又嬌羞不勝似的低著頭,右手則緊緊牽著直加弄的左手。梅雍,烏瑪的伊那(母親的西拉雅語)則高興得合不攏嘴,和直加弄的母親一直有說有笑。烏瑪的生父桑布刀已經過世,現在梅雍和桑布刀的弟弟黎卡在一起。黎卡雖然掩不住心中的喜悅,但卻仍然保持一貫的威嚴,直挺挺地坐著,有一搭沒一搭地和直加弄的父親提大羅邊嚼檳榔邊交談。
身為麻豆社最孚眾望的前長老桑布刀的獨生女,又是部落公認的第一美女,烏瑪自然是全社男子的夢中情人;但也因為他是桑布刀的女兒,所以社裡的男子不免雖愛在心裡,卻又躑躅不前。
桑布刀在麻豆社裡是個傳奇,但也是半個禁忌。他在十七年前率領麻豆社,一口氣殺掉六十三個荷蘭兵士,那是荷蘭人來到福爾摩沙的第五年。荷蘭人和麻豆社人結怨甚早,早在一六二三年荷蘭人正式到來之前Ripon司令帶著荷蘭士兵及奴隸來勘查時,就有衝突,雙方均有死傷。而自從荷蘭人來此,本地人變得要繳稅,麻豆人更是不爽。再加上當年的荷蘭長官努易滋(Pieter Nuyts)年少高傲,被日本武士綁架過(註一),好不容易被釋放後竟還不知悔改,對本地人不但頤氣指使,而且愛好女色,有時要本地人女性去陪睡,本地人更是氣他在心。而他竟然在他離職前九天率領了六十三人的隊伍來麻豆社。荷蘭人此行的目的,號稱是搜捕「漢人海盜」,順便也要求麻豆社人允許荷蘭人以及中國人進來墾殖、種甘蔗、種稻、捕鹿、捕魚等。
那時已擔任長老多年的桑布刀認為,荷蘭人也不是第一次來了,但這麼大陣仗前所未見,根本是武力示威。這個看法,得到了其他十一個長老的支持。於是表面上虛與委蛇,假意協助搜捕逃犯,還拿了二、三罐酒出來,大家和荷蘭人盡情飲酒。荷蘭軍隊準備離開時,麻豆社人假意禮貌的護送他們離開村莊。當一行人離開部落往南約一哩遠,來到一處需渡河的地方,麻豆社人依照規定及慣例幫忙扛武器,然後揹荷蘭士兵過河(註二)。結果麻豆社人到了河中,一聲暗號,所有麻豆人側身把荷蘭人翻落水中,沿著河岸藏匿在樹叢後的麻豆社人紛紛現身,荷蘭士兵不是被麻豆社人強壓淹死,就是給一刀斬了,除了一名小孩和一名奴隸外,沒有活口,還好長官在飯局之前先行回城,逃過一劫。震驚了大員的所有荷蘭人。
九天之後來到大員上任的荷蘭長官普特曼斯在情況不明下,遲遲不敢採取報復行動。麻豆社人好生高興,一時在西拉雅族中聲威大盛,桑布刀也因此成了英雄。
可是,六年後的冬天的一個晚上,可惡的新港社人,竟然甘心為荷蘭人的馬前卒,突襲麻豆社。
那一年,烏瑪九歲。烏瑪還記得那恐怖的一夜,有些荷蘭軍士騎著馬突然闖入村落。荷蘭人的槍聲劃破了寧靜的夜空,狗群則在馬後狂吠,荷蘭步兵擊鼓跟進,新港人則吆喝著放火燒麻豆人的房屋,麻豆社的房屋幾乎都給燒光了。本來十一月的晚上已有寒意,但火焰反而讓大家覺得炙熱。火花四處飄飛,甚是恐怖。烏瑪和族人躲在河邊的叢林中,流著眼淚,又不敢出聲,瑟縮在媽媽的身邊,媽媽則抱著弟弟阿僯。每次槍聲一響,大夥兒就趕緊把眼睛閉起來。那是烏瑪第一次聽到槍聲,第一次聽到鼓聲,也是第一次看到馬。那些荷蘭人並不高大,但在馬上卻顯得好猙獰,來去如風,加上那些槍可以殺人於遠距離外,烏瑪覺得他們不是人,是魔鬼。
麻豆社裡反應最快出去抵抗的勇士,在還沒有接近到敵人的時候,就應聲倒地,讓全村大駭。桑布刀與長老們因此下令不要抵抗,去做無謂的犧牲。還好敵人並沒有進一步屠殺全村,他們進來以後只是放火燒屋,雖然有幾位勇士和可惡的新港人力拼,不幸被新港人割了人頭。處在隊伍最後掩護族人的桑布刀,也不幸被新港社人所擒。當麻豆社人集結成小隊逃離村落時,荷蘭人卻也制止了新港人對麻豆人的追殺,因此麻豆人才能保存大部分的族人,逃到海邊。(註三)
火燒部落後第三天,荷蘭人先回到赤崁。麻豆社長老們出面向新港社人表示希望贖回桑布刀。沒想到新港社人反而把桑布刀砍頭,把頭高掛在竹竿上。梅雍哭得昏了過去,烏瑪也大哭,黎卡和麻豆族人咬緊牙關,誓言要取新港社至少三個人頭來復仇。
長老們清點了一下,發現有一共有二十六個勇士被殺害。黎卡反而鬆了一口氣,他說,六年前,我們殺了六十三個荷蘭人,聽說那是大員荷蘭軍隊的十分之一,現在他們來了近五百名荷蘭人加上一千二百名新港社人,只殺了我們二十六人。麻豆社人突然覺得荷蘭人沒有這麼壞了。麻豆社有好幾千人,如果荷蘭人也放任新港社人殺個十分之一,那麼麻豆社就將鬼哭神嚎了。長老們於是先拜託宋哥,綽號叫「烏嘴鬚」的一位住在麻豆社很久的中國人,請他出面代為乞和。烏嘴鬚長年向荷蘭人付租金承包麻豆社的獵鹿執照及進行鹿皮生意,西拉雅話和荷蘭語都懂,和荷蘭人關係也不錯。
烏瑪記得,接到荷蘭人的議和條件後,麻豆社的頭目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荷蘭人沒有要求再處決任何人,要求的財物也不算多,就是歸還當年自荷蘭人身上取得的東西,以及奉獻一些豬、牛,還有檳榔。他們要麻豆人發誓不再殺害荷蘭人,不可以干擾漢人;如果其他社的人到大員去開會,麻豆社人也要派代表去;如果將來荷蘭人要求,麻豆社人必須協助他們作戰;如果荷蘭代表來訪問,麻豆社人應該接待。然而對荷蘭人提出的第一個條件,麻豆社的長老們則起了爭吵。荷蘭人要麻豆社人「讓渡所有權」給荷蘭,用檳榔和重在土上的可可樹送到他們在大員的城堡為誌。
麻豆人對「所有權」的字眼的起了爭執。六年前,桑布刀會設計殺荷蘭人,就是因為荷蘭人常常讓中國人未經他的允准而經過麻豆社獵鹿或去魍港從事捕烏魚。雖然麻豆人並不吃烏魚,但是桑布刀認為那些中國人必須經過麻豆社人的允准,而不是經過荷蘭人的允許。同樣的,中國人來捕鹿,必須經過麻豆社人的允許,必須付錢給麻豆社人,可是這些漢人認為只要向荷蘭人包租就可以了。烏魚還好,鹿群可是麻豆社人的命脈,而且可惡的是,這些中國人常常在不應該捕鹿的季節去捕鹿,而且陷阱又設得特別厲害,因此連小鹿也被殺死了。
如果依照荷蘭人的條件,後來繼任長老的黎卡說,把「所有權」讓渡給荷蘭人,是單指這些捕魚和捕鹿的權力吧?還是將來這些種出來的糧食,種出來的檳榔,養出來的豬,都要繳給荷蘭人來做分配嗎?烏嘴鬚說,荷蘭人的意思是,荷蘭人要求的只是「捕魚權」、「捕鹿權」的讓渡,至於住民生產出來的東西,荷蘭人只會要求麻豆社每年繳納一定數目的鹿皮、豬、檳榔、椰子等當做「稅收」。烏嘴鬚向黎卡說,荷蘭人對他們中國漢人,不但有各種包租稅、贌稅,還有「人頭稅」;而麻豆社人因為荷蘭人認為他們原先擁有這塊土地,所以不必繳人頭稅。這是麻豆社人第一次聽到這些「主權」和「稅」的觀念,覺得非常新奇。
烏嘴鬚又說,新港社、蕭壠社、大目降社等也都已經答應了荷蘭人的條件,如果麻豆社人也答應了,將來麻豆社人到新港,哆囉國社也都會受到友善的招待。這在麻豆社人聽來,是不可思議的事。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部落,聽命於一個「政府」的「法律」,彼此和睦相處,就叫做「秩序」?
烏嘴鬚說:「我們從中國那邊過來,中國那邊也是這樣的。」黎卡問烏嘴鬚:「那麼你們中國那邊的政府好不好?為什麼你要過來麻豆社生活,不住在故鄉中國?為什麼你們要離開你的故鄉和你的族人?」
烏嘴鬚嘆了一口氣說:「這事情說來話長。首先,這幾年,中國國內有戰爭,實在不怎麼安定。再說我們在中國的土地,沒有你們土地這麼肥沃,種起甘蔗來,長這麼快,這麼甜,這麼茂盛。我們那邊海裡的魚群雖然也多,但你們這裡有烏魚,比那邊多得多,我們很喜歡吃烏魚的卵,我們叫做烏魚子,是下酒的好菜。我每年冬天在這裡抓一個月的烏魚,運到國內去賣,可以讓我們發一筆小財,讓故鄉的父母妻子兒女有錢可以過個好新年。」至於官員嘛,烏嘴鬚說,中國和荷蘭的制度各有其好壞。不過他認為荷蘭的官員算是公平的,而荷蘭傳教士的精神更是讓他很感動。
「荷蘭人來這個島有兩個目的,一是佔據這裡的港口來做貿易的轉運站,收集他們國內喜歡的東西運回去,只要能大賺一筆就好。還好荷蘭人不會把我們當奴隸販賣,雖然我們在這裡辛苦到有些像奴工,不過是志願的」。
烏嘴鬚苦笑了一下:「我聽說,在南洋有些地方,島民會被抓到別的地方當奴隸,我自己在大員就看到一些他們自南洋一個叫班達的島嶼抓來的黑奴。其實除了荷蘭以外,還有其他的國家,也會這樣,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聽說西班牙人很兇暴,在呂宋動不動就殺死上千華人。」
「荷蘭人除了來作轉口生意外,另外有一些熱心的牧師,來這裡的目的是傳播他們的宗教。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也傳教,但這兩個國家傳的是天主教,荷蘭人的宗教聽說是叫做『改革教派』。」烏嘴鬚說:「不久以後,這些牧師也會來要求你們信他們的上帝」。
黎卡則表示不願意接受荷蘭人的「主權讓渡」的條件的,但其他長老大多贊成。黎卡知道不答應也不行,因為麻豆社人打不過荷蘭人。他也不願意去信仰荷蘭人的上帝,他信的是麻豆社祖先們傳下來的阿立祖。於是黎卡決定辭去長老,以利和議進行。麻豆人先交付了九隻活豬及六隻他們最大的鏢槍給新港人,請求和平相處。
註一:就是有名的「濱田弥兵衛事件」。
註二:就是現在的將軍溪。
註三:那時的麻豆社面臨台江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