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柯P上任後提出的公共住宅政策,讓各地的聯開宅住戶紛紛傳出不一樣的聲音。有人支持柯P,希望可以人人有房住;但也有人反對柯P,擔心引發周圍生活品質下降,導致附近房價下跌。也拜柯P引爆的社會住宅議題,讓網路鄉民可以暫時揮別電玩與女神,一起來討論「青貧」亂象。因為月領22K的年輕人,在台北市僅能三餐糊口而已,絕無可能存到買房的頭期款。
從事自然觀察寫作,稱號「鳥人」的四年級作家劉克襄因此有感而發,在臉書上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發文,直言三、四年級台灣人自私的心態拖垮了台灣,「未留下一個安心可以奮鬥的環境」,讓年輕人找到生活目標後努力打拼。許多學者專家仍像部落的巫師,愛當社會的預知者,在年輕人身上貼上許多標籤,「威權式地批判年輕人不願意低就、又過度迷戀網路世界」。但劉克襄認為,社會批判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指控。
劉克襄這篇代表四年級的懺悔文,在傳統媒體與網路上都引發一片叫好聲。記者蘇瑋璇以〈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回應劉克襄,痛陳他所面臨的經濟及社會困境,「像我這樣的七年級生,我們和朋友PK誰在這城市過得更慘」,描述得比劉克襄形容的還不堪。
接著六年級後段班的姜洋,也在《蘋果日報》投書〈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敘述他們這一世代的困境。在這種各自代表年級發言的詭譎氣氛下,社會上出現了世代剝奪的怨懟情緒,年輕世代天真的人云亦云,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上一代的錯」。
身為五年級前段班的網路資深鄉民,不願落入劉克襄精心預設的「世代陷阱」,也來代表五年級發言。從歷史來看,階級問題無分古今中外,就是這麼簡單的弱肉強食。但既得利益者卻偽善狡詐的把此一矛盾,包裝轉化成省籍、黨派、城鄉、宗教到統獨。當這幾招都用爛了之後,現在最新流行的藉口則是世代,甚至更細分為年級。這些炒作土地的政客、財團與自稱是上人等等的既得利益者,現在一定又在偷笑:「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
劉克襄不會告訴你,年輕的鄉民大概也無法想像,四年級這一世代當年就業時,職場的環境如何?在還沒有新竹科學園區之前,台北這裡的凱普、飛歌、通用等超大型工廠,都是女工上萬的大公司。但是兩蔣時代的勞動條件、工安比起今天,那才真叫地獄與天堂。
我在北投住了半世紀多,除了當兵那兩年以外,從未離開過這個小鎮。資深鄉民應該與我有同樣的印象,在淡水線鐵路的竹圍車站外的民族路上,有家生產電視遊樂器和家用電器美商阿泰利(ATARI)集團的飛歌電子廠。那年代公家機關與大眾交通工具都沒裝冷氣,大部分的電影院與餐廳也沒有,但飛歌的廠房裡竟都裝設了冷氣,因此飛歌的女工很自豪,連放假都還穿著工廠制服,就像如今的空姐那樣。
但1972年7月起,飛歌電子廠忽然傳出「怪病」,女工一個又一個暴斃,門口就擺著一具一具的年輕女屍;因為覆蓋的白布不夠,有時甚至是兩具或三具女屍合用一塊。當時還沒有《蘋果日報》,這種女體加屍體的聳動畫面,根本沒有記者會有興趣。但廠家附近的居民早已人心惶惶,平日熱鬧的廠區附近商家也都關門,瞬間變成了鬼域。當時飛歌是台灣很重要的電子大廠,也是退出聯合國之後美商還續留在台的重大投資,因此兩蔣鷹犬也在這裡很認真的「抓匪諜」。
後來女工暴斃的案例越來越多,連高雄那裡的日商三美與美以美也傳出同樣災情,最後政府工安部門不得不入廠追查,才發現根本就不是什麼匪諜在「下毒」,而是美商與日商為了節省成本,而戒嚴時代台灣什麼也沒有,就剩人命特多也特賤,因此他們竟然都用毒性甚高的有機溶劑三氯乙烯與四氯乙烯,但在冷氣房內工作的女工卻毫不知情,以致在廠房裡吸到了過量的乙烯中毒身亡。
年輕鄉民或許不解,兩蔣既然要封鎖女工接連暴斃的新聞,為何廠方反而要這麼殘忍的曝屍?原來那時雖已實行9年國教,但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下,很多鄉下小女生,小學一畢業就必須上台北打工;但未滿14歲,工廠不能錄用,偏偏趕貨時又缺工,於是工廠要她們自己拿其他超過14歲在學女生的名字當人頭,用來領薪水與應付安檢。很多鄉下未成年少女為了進廠,於是冒用正在就讀高中女生的姓名個資來應徵。
資本家草菅人命,兩蔣鷹犬助陣,害得這些小女孩因工安意外暴斃,卻連微薄的勞保給付也拿不到。由於死者有些是廠方也不知真名,用假名在打工的小女生,偏偏一時間又無法通知家屬,只好曝屍以供家人指認。消息傳開後,一方面有些中南部的家長聞訊趕來,急著連薪水也不要了,只想把確認還活著的女兒帶回家;但另一方面在廠方加薪再加薪之下,也有些貧困的少女,明知這裡已死了好多人,仍在真相未明之前趕著來應徵。
當年逃過一劫的飛歌倖存女工,後來下場也沒多好。1984年美商阿泰利將股權與廠房,移轉給另一家美商TTL公司,卻未發放資遺費。除了飛歌事件外,1973年9月3日清晨,一艘由高雄旗津開往前鎮的民營渡輪高中六號,因超載且機械失靈而翻覆沉沒,造成25位住在旗津中洲,要趕往前鎮的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年輕女工罹難。這些可憐而早夭的四年級的女工,她們剝削了誰?她們又怎麼能為今天的居住正義負責?
吳念真也曾寫到,鄉下的女工在工廠裡被檢查出來有肺結核反應,廠方就通知家長領回。小女孩想到回家後沒辦法賺錢,反而還要浪費糧食,就在同事都去上工後,在宿舍裡上吊自殺。台灣經濟的起飛,靠著就是兩蔣這種黨國資本體制剝削廉價女工。今天RCA罹癌的女工,聯福製衣、福昌紡織電子、耀元電子、興利紙業、東菱電子、太中工業等遭黑心老闆惡意關廠的工人,很多也都是四年級生啊!
那年代工廠裡的三班制,生產線上建教班的女生若生病,上課可以請假,上班卻不能請,因為生產線趕工時,上課沒來學校睜一眼閉一眼,但上班缺勤會毫不通融的退學。而且加班領的費用,不是像現在乘以1.35或1.7,而是乘以0.3或0.6,而且不加還不行。我能理解六七八年級的孩子們投入職場後,一定有很多不滿,但你們又怎能想像,三四五年級當時的職場又是什麼光景?
我在戒嚴時代,也在某一國民黨中常委的工廠裡工作3年,見過生產線上有當了20年的計件工,公司就是不給正式職缺(不想付勞保與退休準備金),懷孕的就想方設法調她去粗重的、骯髒的、汙染的地方。3年裡我親眼看見2次職災,一個工人頭被夾斷在生產線上,當場死亡;另一個被斷掉反彈的刀片刺入胸中,送榮總不治。但生產線依然沒停,勞動檢查完全是虛應故事。戒嚴時代的工殤血淚,真的是罄竹難書。
女工與老兵的命運一樣,像牲畜一樣的成了黨國體制的奴工。因此女工在工安事件中,面對生產線上同事的死亡,也跟軍中與眷村裡的人,面對身邊的人遭到白色恐怖凌遲時同樣的「淡定」。一條生產線每一班都上百人,三班制趕工,即使身邊的同事慢性中毒倒地昏厥(像飛歌),甚至意外身首異處、血流遍地(像那家中常委的工廠),生產線還是不能停,死傷者由主管負責,工人不能擅離崗位。在戒嚴體制下,這種上萬人的保稅工廠,就跟眷村與戰場一樣冷血。
唉!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四年級的人到底是招誰惹誰了?鄉民們別再落入當權者為我們預設分類械鬥的世代陷阱中。土地是有限資本,有本事操作的一定都是特權階級。這是階級問題,與誰是幾年級無關。無關,無關,無關(丟筆,沉思中)。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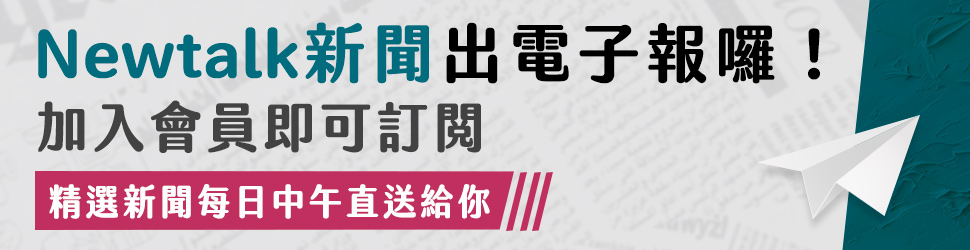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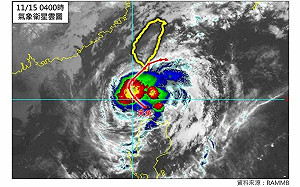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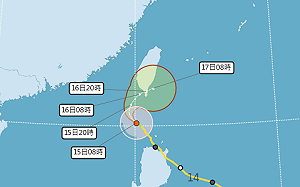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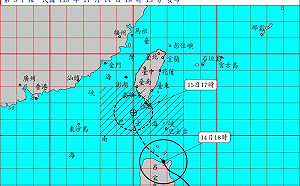
![11/30-12/1 [短影音新勢力養成營隊] 免費報名參加](https://images.newtalk.tw/resize_action2/300/album/project/1/672ad0d4ad3ff.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