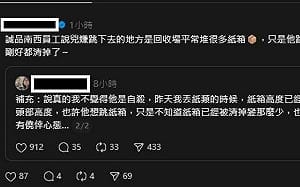「大戰略」(grand strategy)是一個國家為了追求國家利益,統合其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等各方面的工具的一套計畫和政策。最出名的「大戰略」莫過於「圍堵政策」。自從冷戰結束以來,這個詞彙已經不太常見。美國外交學者費佛(Peter Feaver)便曾指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最後一次用到「大戰略」這個詞,是1999年討論科索沃事件。然而,近來中國和其他新興強權的崛起,卻使各國外長、智庫和國際關係學院再度關注「大戰略」。
現正最夯:北捷擲彈砍人案4死9傷疑預謀! 警搜索兇嫌張文租屋處扣爆裂物材料
路透社昨夜發自倫敦的報導指出,幾年前畢業的學生想要投入外交和國安工作,必須關注的是「反恐」相關議題;但如今需要的人才是對於強權間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棋局之理解。在各國攻防之間,經濟力和媒體的掌握力之重要性,並不遜於船堅炮利。
儘管茉莉花革命的發展讓人無法忽視中東與北非局勢,賓拉登之死也不意味著可以就此不管那些好戰組織,但對西方世界而言,中東與蓋達組織已經不再是他們唯一關注的焦點。
肯塔基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法利(Robert Farley)指出,反恐戰爭的確使人忽視「大戰略」的重要性,但現在的學生知道自己將來無論朝公部門或私部門發展,都需要懂「大戰略」。他舉例說:「我們最近就曾因有學生無法回答中國崛起的問題,而將他們當掉。」
法利教授說,在暑期選修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密集課程的學生不斷減少,原因是學生預期將來那個區域需要的軍事和外交工作會減少。學習基礎中文的人數正在增加,學生急著展現自己懂經濟、網路戰爭、社群媒體對政治的影響等廣博的知識。除了中國之外,學生也需要對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崛起中的強權有相當的了解。不同於冷戰時代的前輩,只要懂得蘇聯的某個政策領域,就可以一輩子不愁吃穿;現在的學生面對的是一個更複雜的世界。
不同於以往的軍事衝突或殖民地爭奪戰,新時代各國的衝突往往是看不見的網路戰和經濟戰。
這個世界正面臨極大的變化。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指出,當前有兩個權力轉移的現象:其一是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主要是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其二是權力從國家轉移到非國家組織的現象。兩者都必須加以正視。
這不是說反恐這個領域會就此消失,而是有迫切的需要讓年輕的畢業生和資深的研究人員發展出更廣的專業領域。哈佛大學歷史與國際關係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把賓拉登想像為西方世界在地緣政治上最主要的威脅,老實說是相當荒唐不合理的。他說:「對美國而言最主要的地緣政治問題就是中國的崛起。我們需要一套戰略來加以面對。如果沒有一套將印度和日本等區域盟邦整合起來的戰略,美國將無別路可走,只有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