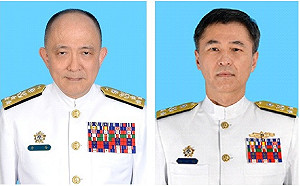審計部日前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查報告中指出,自108年至113年8月底,全國法院適用《刑法》第339-4條「加重詐欺罪」的有罪判決累積達80萬件,然而實際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竟僅佔千分之二。
立法院雖於113年7月三讀通過「打詐新四法」,強調以更嚴密的法網對抗日益組織化、科技化的詐欺犯罪。政府也陸續推出刑度加重、跨部會聯打、資金流追蹤、通訊管控等措施,立法與行政部門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然而據法務部公開資訊,114年地方檢察署執行詐欺案件裁判確定人數統計資料分析,2年以下刑期佔比近78%,2–5年中長刑僅佔不到1%,對高額或組織型詐欺威懾力不足。社會依舊一再見到詐騙機房不斷破獲,帳戶人頭層出不窮,受害者血本無歸。究其根本,問題出在司法體系未能同步「跟上節奏」,特別是量刑與社會期待間的落差,正成為政策破口。
此一困境,犯罪經濟學提供了最直接的解釋框架:犯罪行為是一種理性選擇,其發生與否取決於「犯罪成本與預期收益」之相對關係。犯罪人會衡量其犯罪後可獲得的利潤、被抓風險、以及一旦被捕後的懲罰程度。換言之,若法律制裁輕微,即便抓獲率提高,也可能無法真正提升犯罪總成本,反令犯罪成為一種「高報酬、低風險」的合理選項。
對照台灣現實,法院針對詐欺案件的低量刑正是在「犯罪成本」公式中最弱的一環。縱使警方查緝、檢方起訴力道加強,最終在量刑過程中若無明確懲罰作為,反而會形成一種逆向激勵:詐騙集團計算風險後,發現即便遭偵破起訴,多數仍可輕判、緩刑、甚至「折抵羈押期」提前獲釋,實際服刑時間極短,犯罪報酬遠高於成本,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誰還怕被抓?
事實上,法院現行量刑多採個別化處遇,傾向以「初犯」、「年輕被告」、「具悔意」作為減刑依據,卻常忽略詐欺犯罪背後的組織結構與網絡分工。諷刺的是,明明加重詐欺罪已經入法多年,法院仍舊以個人情境為判決主軸,輕判乃至給予緩刑者屢見不鮮。這種法律現實的「低懲罰機制」,無疑是對犯罪經濟學中「成本必須高於預期利潤」原則的實質背離。
更進一步觀察,司法院雖於110年提出《刑事案件妥適量刑法》草案,擬設立量刑準則委員會制定統一規範,提升量刑一致性、透明性與預測性,但該草案至今仍因立法程序未竟而停滯。司法院雖透過「量刑參考表」、「量刑建議系統」等軟性工具,試圖為法官提供決策依據,但因無強制力,效果有限。結果便是,國人一方面見證「打詐新四法」雷聲大作,另一方面卻也親歷詐欺犯「輕判出獄」的荒謬事實。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殘酷真相:當法律無法有效提升犯罪成本,便等同默許犯罪者繼續行動。在詐欺產業鏈中,每一筆騙得的鉅款、每一通欺騙電話的背後,都可能是司法體系對犯罪成本定價錯誤的結果。
因此,改革的方向絕不能僅止於口號與法條,而必須落實於制度設計與判決文化之中。首先,立法院應儘速重啟《妥適量刑法》立法程序,給予量刑準則法源依據,提升其拘束力。其次,應針對組織型詐欺設計最低量刑門檻,避免法官僅以犯罪個人面貌作量刑依據,忽視其在整體犯罪結構中的角色。
司法改革不是單一機關的任務,而是國家制度如何有效運作的試金石。若任由量刑失衡繼續發酵,即使行政單位再努力、法律條文再嚴峻,仍無法補救犯罪成本低落所造成的制度性崩解。當法律對詐欺的處罰成為可預期的輕微懲罰,那麼,詐欺的蔓延,也就成了可預期的國難!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