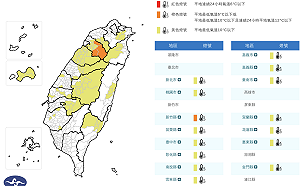《名畫的控訴》是一部由英國與美國合拍的傳記片,其電影內容主要改編自瑪麗亞・阿特曼的真實故事。女主角瑪麗亞・阿特曼是一位住在美國洛杉磯的猶太難民,作為家族僅存的唯一繼承人,她決定從奧地利政府手中奪回古斯塔夫・克林姆的名畫《艾蒂兒肖像一號》,因為此幅畫中所描繪的人物正是瑪麗亞最親愛的姑姑。為此,瑪麗亞與身為律師的男主角藍道・荀白克攜手合作,共耗費六年的時間,終於在2006年成功地贏得了這場官司,使奧地利法院宣判此作歸還鮑爾家族合法繼承人瑪麗亞・阿特曼。
此部電影中所訴諸的核心訊息,無非是「轉型正義」的主題。然而在初次欣賞完這部片之後,它整體的敘事方式並沒有非常地打動我,若可以選擇,我想我應該不會重看第二次,更不用說大力推薦給他人。剛開始我以為這樣的想法是由於自己對政治議題沒興趣或不敏感、沒有特別喜歡《艾蒂兒肖像一號》,或不常接觸這類題材的電影,才導致個人無法對其產生巨大的共鳴,可經過觀影後的持續反思,我逐漸觀察出一個相反的論點:就是因為它太過直白且平淡地刻畫整個事件——戲中不僅沒有誇張激烈的仇恨展現,也沒有過分高潮跌宕的戲碼——如此的寫實呈現無法滿足我平時觀影的心態,使我未能從過去的認知經驗、自身長背景的文化脈絡中,提取相關的情緒經歷或挖掘相似之處,以至於自己無法全然沈浸於劇情之中。而這種「與我無關」的心態,恰恰反應出轉型正義為何需要被重視,也正是其難以落實的致命傷。
人們往往因為無法對某些事情感同身受、資訊理解量匱乏,或是本身為既得利益者不希望現況有所變化,選擇將錯誤視而不見或解釋成無關緊要,甚至是完全無法察覺錯誤的產生。而這種與「與我無關」的思維看似微不足道,卻迫害了歷史上少數族群的利益,危及、犧牲了無數人的性命。在心理學的概念中,探討社會裡出現的「多數人的無知」與「從眾」歷程,都是源自於團體壓力以及個人自行想像的情境。例如在多數人的無知中,人們因為觀察到他人對事件沒有作出反應,進而判斷事件不重要、不需要被處理,或擅自認為有其他人會解決問題,導致自己也沒有做反應。而這樣的結果,帶來的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事件插手,使其完全被忽視,無形中塑造成多數的無知。就如本片的核心主題,倘若瑪麗亞沒有執意要回《艾蒂兒肖像一號》,千里迢迢從美國飛往奧地利去展現決心,奧地利政府是不可能主動歸還畫作的。即使他們深知真相為何,也因為其他利益而選擇閉口不談,如此一來,猶太人當年被迫害的命運,以及其悲慘的經歷又該如何被緬懷和彌補?
電影是虛構的,若以「真實事件的改編」一句話來證明它是真的,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再現的真實。閱聽人跟作品之間的連結奠基於呈現媒介之上,如果媒介無法回應閱聽人的期待,就很可能使創作無法走入觀者的心扉,使作品無法召喚出觀眾的強烈情感共鳴。這無關乎個人是否擁有同理心,而是在於議題(作品)的呈現手法,會大大地影響人們的感知事件的狀態。例如我雖然對這部片的感觸不深,但我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十二歲時去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震撼,即便當時的沒有足夠的英語能力去讀懂導覽,對猶太人的歷史也一知半解,但因為整個博物館的氣氛營造、擺飾與場景架設真實而精細,讓人有種身歷其境的嚴肅與沈重,使我對那時的回憶都還歷歷在目——我永遠都忘不了博物館的出口前有一條廊道,四周擺滿的破舊、遺留的髒鞋子,好似屍體堆積於四周,環繞在路過的每一個人身旁。
除了議題的媒介呈現,我認為情境脈絡也是喚起人們對轉型正義的意識很重要的因素。好比我若是在與台灣歷史文化相關的課程欣賞此電影,也許會有不同的見解。我極有可能把猶太人在歷史上不公正的遭遇,和課程中提及的二二八事件作出連結,將猶太人和台灣人令人心酸的無辜迫害劃上等號,感受到悲憤的情緒,更加確信了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為此,我認為轉型正義的實踐,必須將「與我無關」的態度轉變為「息息相關」。唯有喚起他者的同理、取得信任與認同,所謂的正義才有立基的可能性。而人們對於某一社會議題的接受與否,與此議題傳播時樣態有高度連結,若能把握住媒介的操作,以及搭配情境去扣連閱聽眾的文化與情感,轉型正義的實現或許不會像電影中,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那般艱澀又使人卻步。
我們很容易安逸於太平盛世的平凡無奇中,忘卻世界還有一隅角落正默默承載無盡的傷痛。這種痛是淌流在血液裡,難以被時間完全治癒,它不僅僅代表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也被狠狠地刻畫於歷史的脈絡中,用血腥及哀慟去告誡未來的你我,人類善與惡的界線,是何等的脆弱與模糊。
人活於世間,若能有多一點的傾聽,少一點的謾罵污衊,正義也許就不需用金錢去攫取或償還,而是如空氣般,理所當然又自然的存在。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