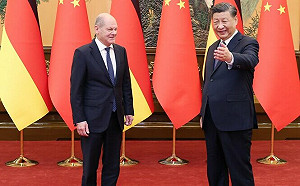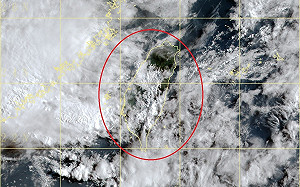在冬寒凜冽的台北,我讀到一則令人心酸的新聞︰新年期間,日本大阪一對六十餘歲姐妹,被發現死在家中,身邊只剩90日圓(約新台幣32元),胃裡空無一物,顯然是餓死。
這對姐妹的父親曾經是銀行高幹,擁有房地產。父母去世後,姐妹靠遺產過活,但因房屋改建大樓,向銀行借的錢還不出來而生活陷入困境。日本經濟雖然長期停滯發展,可是社會福利仍然高過亞洲各國,應該不致於聽任國民飢餓死亡。兩姐妹竟然死於飢寒,恐怕是羞於向人求助的個性所致,這固然多少反映出許多日本人共同的國民性,本質上還是個人的悲劇。
不同於此,許多地區人民的貧窮則帶有集體性;集體的貧窮一定帶有社會印記。
1992年秋天,我三個月的旅途最後一站抵達俄羅斯。從莫斯科城市邊緣的「五星級」宇宙大飯店(Hotel Cosmos),每天我必須步行大約15分鐘,經過好幾棟龐大的蘇維埃集體住宅,才能走到地鐵的最終站,搭車進城。
到今天還深深印在我腦海裡的,總是那一長排從地鐵站前伸延出來,手上都拿著一兩樣物品,等候交易的人列。好幾次我注意到一位老先生,留著灰白但梳理整齊的鬍鬚,戴著呢帽,裹著圍巾,披著大衣,雙手拿著一長條麵包,靜靜地站在行列裡。他臉上一副古意盎然的框邊眼鏡,流露出無法掩飾的斯文氣質。每次看著他,我就一直在想,這到底是國家科學院剛丟掉工作的核子科學家,還是大學裡被迫離開教職的古文學教授。似乎他現在唯一的生計,便是在寒風中販售家中老婆烤出來的幾條麵包。
那是共黨紅朝剛墜落的年代,國營企業陷入混亂,私人小生意才開始萌芽,物資嚴重缺乏,盧布天天貶值,紅伶流落街頭賣唱,黑幫橫行郊衢打劫。這時候的俄羅斯一片蕭瑟,放眼看去都是敗落的景象。國家體制的崩潰,讓俄羅斯人民十幾年處於集體貧窮的狀態,一直到新世紀開始,國際油價狂飆,才讓產油的俄國經濟,又浮了上來,不過新的問題,嚴重的貧富不均,隨即開始。
貧窮不會只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資本主義照樣帶來蕭條,而且禍延動物。
在歐洲沒有其它國家的人,像愛爾蘭人那樣狂熱於養馬,愛爾蘭人養的馬全球都有口碑,一匹好的純種賽馬可以賣到一百萬歐元。愛爾蘭平均每人養馬數,歐洲沒有那個國家可與相比。可是現在,卻大約有20,000頭各式各樣、各種品級的馬,必須在飢餓的狀態下,接受愛爾蘭今年寒酷冬天的考驗。
幾年前,愛爾蘭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典範,一度是歐盟第二富有的國家。在經濟不斷成長的迷思下,新社區不斷開發,金融信用不斷擴張。有錢的建商搭乘直昇機在不同工地起落。至於一般平民,則是熱衷和別人共同認養賽馬或是休閒用馬,藉此賺錢拼經濟。
當時愛爾蘭的經濟成就是許多新聞報導的焦點,連台灣媒體都派記者專程採訪,作家吳祥輝還為此寫了一本名為「驚嘆愛爾蘭」的暢銷書。
然而前年金融海嘯讓愛爾蘭經濟一趴倒地,建商接連倒閉,也拖垮了金融業,國家財政瀕臨破產,不久前歐盟國家同意出手救援,愛爾蘭才稍微鬆了一口氣。
可是歐盟的救援計畫附帶有嚴苛的節約條件,未來一、二十年愛爾蘭民眾恐怕都必須勒緊腰帶才撐得過去。至於突然嚴重過剩的各類馬匹,命運就更悲慘了。
歐洲媒體報導,現在只有最高檔、最純種的賽馬,才在市場交易得出去,二級、三級馬匹市場則已經崩潰。要把這些馬匹養過冬天,對許多飼主已是承擔不起的負擔。都柏林大學一項研究說,這些多餘出來的馬匹恐怕必須被「人道地處理掉」。
從前年開始,輸往法國的馬肉突然增加了五倍。可是歐盟的肉品衛生嚴格規定,只有具備完整飼養文件的馬匹才可屠宰當肉品交易,原本為騎乘用途的馬匹,則大多被餵食過不合肉品規範的抗生素。
於是為數甚多養不起的馬匹,包括不少純種的賽馬,成為被遺棄的流浪馬,散落在高速公路旁的荒地和已成廢墟的未完成工地,瘦骨嶙峋像孤魂野鬼,低頭找尋一點都引不起食慾的荒草。最近「保護動物協會」電話響起,有七成是為了流浪馬,馬匹餓死的消息此起彼落。
這些都是遙遠的貧窮景象。
台灣似乎不曾再聽說有餓死者的新聞了。入夜後,城市外郊暗巷裡只有看到流浪狗,不見流浪馬。流浪狗應該也不是因為飼主貧窮才被棄養。
沒有日本婆婆寧願餓死的自尊,台灣街民會尋找垃圾桶裡殘餘的食物,懂得門路的,還會午夜過後,到若干便利商品領取逾期的便當。
這是富足的台灣?
其實翻開報紙,因為無力償債,父攜子服毒自盡,母攜女燒炭死亡的新聞愈來愈多。台灣的貧窮,呈現另外一種絕望的景象,它愈來愈帶有強烈的社會印記,在訴說一種政府不願面對的集體貧窮。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