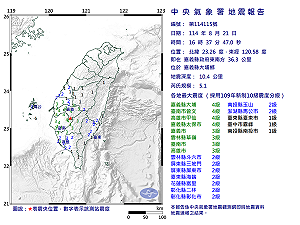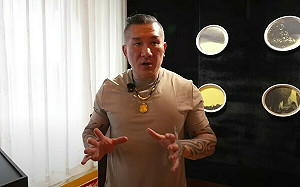(版主有話說:我一直對指揮林光餘首開國內音樂人走訪美國交響樂團,研習交響樂團經營管理術,深感興趣。很高興林副團長把以前刊登在音樂月刊的文章,花時間重新打字修訂,分享在我的部落格。事實上他在研習完畢後有出版專書,只是現已絕版,不過許多圖書館都有這本藏書。文章中他談羅斯托波維奇,也談祖賓‧梅塔的軼事。)
走訪美國職業交響樂團
林光餘
回憶起兩年前(指1984年)燠熱的盛暑,經過一番煩人的行政申請程序,我開始一連串冗長、煎熬,緊張的出國考試。這類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辦的公務員公費出國進修考試,前後歷經數月之久。經過半年的折騰,終在七十四年底獲知錄取。當時全無興奮之感,只知道另一場仗正等著我打。
由於我報考的科目與核定研讀範圍為「社教機構行政管理」(注一),又鑒於本身職務性質,我明白,如果按照一般美國大學進修方式,應就讀與「交響樂團行政管理」有關的科目。可是一來未聞美國大學有單獨的「交響樂團行政管理」科系存在,而設有相近的「藝術行政管理」科系的學校又少。於是,我大膽向我上級主管單位提出一種較切合實際、收效亦大的進修計畫:就是乾脆直接攻堅,捨學校進修,直接進入美國職業交響樂團研習攸關樂團運作成敗之核心課題──交響樂團之經營管理術。我想這樣方才具有實效意義。事後證明這是明智抉擇。
整個進修計畫就安排技術而論並不好處理。首先,我為了要多跑些地方,多看點東西,一口氣申請了十幾個依照「美國交響樂團聯盟」分類訂為「第一級」的交響樂團(注二)。可能因為申請信函內容得體實際,首肯者竟達十之八九。然而問題接踵而至;如果只有三兩個這類樂團應允,安排工作倒也容易;如今可去之處有十來個,只得就整體情況過濾掉實在無法兼顧的。結果忍痛犧牲了克里夫蘭、辛辛那提、密爾瓦基等聲名卓著的樂團。在緊鑼密鼓的安排下,獨自辛苦了半年多;其間還與馬水龍兄同獲傅爾布萊特基金會的資助,直到第二年八月底才整裝上道。展開了一場美國交響樂團走訪之行。
國家交響樂團(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與羅斯托波維奇
我研習的第一站是位於華盛頓的「國家交響樂團」。這個曾來華訪問過的樂團,雖然冠以「國家」之名,卻不隸屬美國政府。其名之由來,實因身處首都而得名。其實美國政府從不設置公立演藝團體。所有一千五百多個美國交響樂團,全屬私人經營;因此維持營運至為不易,關門倒閉時有所聞。
「國家交響樂團」最近亦因經營不善,被其房東「甘迺迪中心」收購兼併。我去時正值赤字高峰,行政人員都深恐被新合夥人「甘迺迪中心」改組裁掉。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也體會到「洋同行」為生活發愁的一面;慶幸自己在國內制度庇蔭下,尚勿需為這種事擔憂。
有關樂團營運出現赤字,據重要行政人員透露,一部分原因是由於華盛頓市所在的哥倫比亞特區性質特殊,它不像一個實質的州,演藝團體的各種經費及政府補助不易爭取。但也有人說,此事與身為音樂總監(首席指揮)的20世紀大提琴巨擘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的指揮術有關。
團員對指揮的批評
一位資深團員在一場演奏會過後,與我談到剛結束的演奏會狀況。由於我本是樂團團員,與他都是「上過戰場」的同行,因此談話投機。我不保留地直問,為何剛才有一位小提琴團員在台上連續兩次出錯,而且出錯地方都一樣?(其實我知道原因所在,是指揮問題。至於所謂「出錯」,不是指這位團員拉錯音,而是指他「搶入」或「搶拍」;這種出錯如果聽眾耳尖是可能聽得出的。)出我意料是,他竟說:「那傢伙是喝了酒上場的。」
「怎麼可以這樣?」
「都是因為羅斯托波維奇指揮太不保險,害得那小子要借酒壯膽才敢進來(注三);結果膽是壯了,還是「進」錯了。
聽了這樣答覆,我吃驚之至,心想天下團員原來一個樣,批評起指揮都恁不留情,不論對象是20世紀音樂奇葩如羅老者,或真是樂壇三流人物。不過看他表情嚴肅,不似玩笑話,他似乎已火透了羅老。其實,羅老問題勿需他講大家也看得出,只是我想聽聽團員的看法。
選聘指揮之道
有人一定會問,既然羅斯托波維奇的指揮能力差,為何能位居世界級的國家交響樂團指揮(音樂總監)寶座?依我看法是,羅氏只是「棒」藝稍弱,其大提琴藝不但爐火純青,無與倫比,詮釋俄羅斯作品尤有一手;加上他與「飛越蘇聯」(1985電影)的芭蕾舞星巴瑞希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具有一樣的特殊政治背景,擁有十足的世界級魅力,足以傾倒廣大的老美聽眾。
說到此,可一談美國職業交響樂團的基本經營理念。其實羅斯托波維奇的這些條件,正合美國一般職業交響樂團一切以「行銷」掛帥,講求現實的原則。指揮家的「棒」藝,只是樂團遴聘指揮的條件之一;參與指揮甄選者縱使是天才橫溢,若無名聲,樂團可能連正眼都不瞧。所以羅氏必有其他「行銷」可取之處,否則不可能居其位。
我在美期間,美國樂界謠傳另一位著名指揮家祖賓‧梅塔(Zubin Mehta)的紐約愛樂指揮位子也有些動搖。但他現在既然仍留在紐約愛樂,想必有其可取之處。不過我利用研習空檔,曾細觀其指揮;沒話說,他指揮之清晰又乾淨俐落程度,羅斯托波維奇不能相提並論。至於兩人對於音樂的深層詮釋,倒是見仁見智的。記得有幾次,梅塔為了要與「茱麗亞音樂院交響樂團」合作,指揮該樂團演出史塔文斯基的《春之祭》,而移駕位在紐約愛樂隔壁的茱麗亞音樂院進行排練;我也隨行旁觀,發覺其背譜能力驚人。《春之祭》是高難度大曲,其節奏千變萬化,可使指揮者稍一恍神即出大錯。梅塔不愧為指揮老將;排練時,我注意到他徹頭徹尾未翻開總譜瞧一眼,卻能夠將變幻無窮的《春之祭》每一段落背記得一點都不差,還兼使出一手精湛棒藝與梅塔標誌式的「秀」勁,讓自視甚高的茱麗亞音樂院師生演練得大呼過癮,而且對梅塔敬佩不已。(27年後加註:上面這件事發生在1986年,幾十年後的2013年,我早已將其中細節忘淨,卻想起2011-12年左右一場在維也納舉行的,觀眾總有上萬的戶外超大規模演出。在電視轉播中,我看到鬢鬢白髮的梅塔帶領著世界頂級的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先以韋伯的《奧伯龍序曲》開場;完畢後,接著是蕭邦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將由1982年才出世的郎朗擔綱主奏,梅塔當時早已是紐約愛樂指揮。此時,只見舞台上要給朗朗彈奏的巨型平台大鋼琴早已安置定位,只待舞台工作人員將琴蓋掀開撐起,然後等郎朗一出台,梅塔步上指揮台,這場由樂團搭配鋼琴的美妙鋼琴協奏曲的演出即可開始進行。這本是這類音樂會的標準作業程序與過程,是無話可說的;台下聽眾也鴉雀無聲靜待著郎朗出現。但妙事發生了。就在此刻,原站在台上等待郎朗出台的梅塔,卻一箭步走到鋼琴旁,將幾十公斤重的琴蓋一把撐起,讓原該做此事的工作人員一時傻眼。需特別說明是,這琴蓋的尺寸與重量,絕非一般家用豎型鋼琴的琴蓋可比;這實心木製成的琴蓋,長度總有三米,最寬處有一米半以上,我估計琴蓋總有幾十公斤重。一般人要很費力才能將它完全撐起。而且以舞台工作倫理而言,這掀琴蓋工作就算什麼人都可以做,也輪不到梅塔來做。梅塔可是當今頂級天王指揮家,被人奉承還來不及,怎可能由他去撐起琴蓋?但他真的這樣做了,而且做得自然不做作;讓人不得不聯想,他大概是超喜歡郎朗琴藝,以致掩飾不住他像幾十年前與茱麗亞音樂院學生打成一片那樣的提攜後輩之心,做了為後輩撐開琴蓋的驚人動作。)
步入正題
觀察大師們的排練,並非我的主課;以我所學與實際經驗,作夢也描繪得出這類樂團的演奏情形。而我所要探討的卻是精采絕倫演奏的「幕後」;那如同作戰計畫般細密的整體作業是怎樣形成?為何能在經費捉襟見肘,政府補助不足下,他們仍有成效卓著的演出?
研習的條件
然而,研習國外樂團的行政作業並非易事,本身條件不足就可能導致霧裡看花,抓不到重點。所謂條件,無非是研習者最好具備樂團的「實戰經驗」,加上對於現代管理的基本認知與語文能力。以我而論,出國前我曾任團員、副指揮,行政主管、副團長等職務。但研習者若能具備企管學位則是上上人選了。這樣條件人物在此可能罕見,在美國卻不少。我即親身遇上不少當地樂團行政人員,既具音樂學位,又有「企管」學位。他們為何如此?很簡單,在美國的音樂飯並不好吃,主修器樂學位的音樂系學生在畢業後,即使演奏技藝超群,一時絕進不了高薪的知名職業交響樂團,因為這類樂團團員的職缺極少。儘管如此,心儀知名職業交響樂團工作者卻大有人在。於是不少音樂系學生進入大學時,自始就多唸一個學位,以便日後增加工作機會。有些人就因此打入了著名交響樂團,從行政人員幹起,但這不表示日後他必能成為演奏團員,他仍須經過嚴謹測試。不論如何,具有這樣學歷條件的樂團行政人員辦起演出業務,工作成效當然不會差。
值得借鏡參考的業務
我個人由於早在數年前即有計畫收集美國各級樂團的經營管理資料,故對於他們行政運作本稍具概念。到了實地,卻發現不少運作方式雖與原本想像完全符合,仍有一些組織與其作業出乎我意料。可見閉門造車式閱讀資料書籍,是無法模擬全盤情形的。讓我試著分述一些值得我國交響樂團借鏡的行政業務….
第一、美國樂團的「行銷與公關」組織的業務量之重,超過我想像。其工作網絡與相關社會人脈組織之綿密,作業之精細,猶如戰情管制。這點讓我聯想到,原來台灣公立交響樂團的銷票率始終不甚理想之因,不就是我國樂團不若美國樂團重視「行銷與公關」工作,以致與社會互動不足,進而影響銷票成效嗎?
事實上這類組職與一般公司的行銷公關業務完全相同。交響樂團若在這層業務工作上成績不彰,如同公司工廠不善經營,任產品滯銷而不顧,更無售後服務工作,這樣公司自然容易步上關閉命運。交響樂團也一樣,不論公營或私營,光談演出而不顧行銷與公關,就只能庸庸碌碌地存活於社會。然則我國交響樂團為何如此不重視行銷與公關?這與我國交響樂團的組成性質有關。我國交響樂團數量上原本不多,主要的幾個樂團都屬公立,說穿了也就是這些樂團的行政費與人事費悉數由政府負擔。國內完全沒有如同美國職業交響樂團型式的,以售票方式營運的私營樂團。但各國都一樣,舉凡一個演藝團體不愁吃穿,組成是徹底的「公立」,大概不會主動擔心票房(不論是有價或免費票)業績了。既無票房壓力,就不會想開拓觀聽眾「市場」,自然也不會在專業行銷與公關工作上下功夫。於是,除非我國公立樂團主事者心繫社會,以民眾樂教為念,善加利用國外職業樂團所不敢奢望的「公立」優勢,做好有行銷之實,無行銷壓力的「行銷」工作;不然,我國公立樂團日久玩生,雖自以為很盡推廣「樂教」之責,卻可能淪為制式公務機構,成效不彰而不自知。其實美國除幾個世界級交響樂團薪資出眾之外,一般職業交響樂團團職員生活並不富裕。他們終日汲汲營生,每日行程盡是上午參加樂團練習,下午教琴,晚上上台演出,人忙得像個無休止陀螺。因此一聽到我說台灣的主要交響樂團是「公立」,是純粹由政府資助,都稱羨不已,甚至有人想來台工作。
第二、「籌募」組職的設置。這種組織的主要功能是專門替樂團開拓財源。美國職業交響樂團在財務分配上,大約是「售票」所得占全部收入的1/3,「勸募」與各類政府補助占其餘2/3,故此一組織之工作負擔十分沉重。組員們天天四處張羅勸募之外,有時還要聘請「籌募顧問公司」專家蒞團指點迷津。我在印第安納波勒斯交響樂團時 (請參閱「拾穗」九月份,頁113),及躬逢其盛。
事實上,美國職業交響樂團命脈就操在這兩組人員身上。他們工作的成效,很影響大局。而這些人的工作壓力與身心負擔亦大。樂團主事者與他們所談的,就只有錢,其他全不談;主事者只談他們工作聘約上今年籌款業績應多少錢(大樂團的「多少錢」單位是「百萬」美元。);言下之意,達不到這個標準,明年就與樂團說再見了。至於他們的學經歷背景,則多係經驗豐富的專才,或原本就是地區著名的「行銷」、「公關」、「財經」專家。
第三、在樂團裡專設「義工」單位,招募並管理成百上千以樂迷為基礎的「義工」。所謂「義工」(志工),絕非像台灣樂團某些樂友團體,逕自冠上「XX樂團之友」,就光拿便宜票卻不做事。美國樂團是要設法實際指使義工參與樂團行政工作、以及銷票,甚至季票的認購。工作範圍包羅萬象,從清掃、打字、劇院門衛、領位,到主持大型餐會、邀約市長、州長參與關乎樂團前途發展的會議等等的「非立法性遊說」(Advocacy)工作都是。從另一角度看,如此一來,樂團等於平白增添成百上千不支薪的工作人員。
這些「義工」團體中有不少是地方仕紳之夫人。她門平日熱心公益,看待地方上的交響樂團,一如我們在地人士看待我們的「楊麗花歌仔戲團」。她們迷捧「指揮」的勁兒,一如我們廣大戲迷群眾擁戴楊麗花一般。有一點必須一提:歐美地方仕紳、群眾之所以如此對待他們在地交響樂團的指揮,是因為「交響樂團史」與「指揮史」的發展,在西洋音樂史上與西洋音樂本身無法切割,兩者皆是同根而生;再加上西洋音樂原本就是洋人唯一音樂文化的「根」,因此,廣大洋人群眾自然會將地區交響樂團指揮視為地方「樂神」;不像我們因文化差異與後天樂教不足,迄今無法將「洋樂」視為音樂文化的根,自然也不可能如同洋人一般珍視交響樂團指揮。當然,如果捨音樂文化認同上的先天缺陷不談,我們樂團指揮若真具有大部分國外大樂團音樂總監(也就是指揮)所具備的明星魅力或政治交際手腕(請看卡拉揚就是),在音樂的社會影響力上,仍可作出相當程度的彌補。
話歸正題,且說樂團的「義工組」負責人卻對我抱怨道:「義工人多雖好,每天跟成百太太女士們周旋,要有絕大耐心與毅力;否則不小心就身陷是非泥淖。」可見組織起來讓她們發揮功效當非易事。
第四、是交響樂團的「樂教業務」的推展。這項業務頗似國內樂團的「地區巡迴演出」與「學校演出」計畫。不過他們的演出計畫制定得極周詳,執行時鮮出狀況。但我見到有的樂團的節目內容設計,不一定比我們高明;他們只是在給聽眾閱讀或試聽的「音樂會前教材」上,提供了充分的資訊。有的學校老師為配合樂團演出,早將演出曲目內容向小朋友解釋清楚;有些樂團為「到校演出」,甚至派出由義工組成的先遣「教導團」(Docent),分赴各校講解;這樣下來,其最終教育成效自然頗佳。
在休士頓交響樂團期間,我曾隨團前往鄉間學校演出。樂團團員心態一如我國樂團團員,對於巡迴鄉間的演出頗不帶勁;然而這些團員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在小學生時代沒有見識過這樣大陣仗的交響樂團校園演奏會,可能至今對音樂毫無興趣,一輩子也不會幹上這一行。事實上職業交響樂團(包括幾個美國世界級交響樂團)的下鄉教育性演出,除了可自州、郡教育局爭取到微薄的演出報酬外,最重要目的是藉著下鄉蒞校演出,一面達到樂教功能,同時培養了下一代聽眾以及下一世代音樂家;進而使樂團在幾十年後仍能永續經營,既有新一代聽眾,又有新一代音樂家入團參加演出。其竅門則在於,當在演奏台上面對成千上萬孩童時,搖身一變為節目主持人的樂團指揮,須在其言詞中滿口「我們的樂團如何如何…」,以使孩童們對「我們的樂團」產生親切認同感。譬如著名的舊金山交響樂團在舉辦的教育性演出中(並非到校舉辦,而是直接將孩童用校車接到著名的舊金山市的戴維斯音樂廳),指揮開門見山第一句就是:「歡迎小朋友來聆聽舊金山交響樂團的演出。我們舊金山交響樂團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交響樂團,它也是屬於你的交響樂團…..」。言詞之間盡量使舊金山地區孩童從小就知道有這麼一個「舊金山」交響樂團存在,進而讓孩童以及陪伴的家長去關心它。
有些樂團推動教育性事業更為積極;除了舉辦樂教性質演出之外,另設置青少年交響樂團;以便一面教授該地區青少年學習樂器,一面拉攏為孩子付出心力的家長,使家長很自然地成為樂團基本聽眾。傑出華裔指揮家林望傑就在擔任舊金山交響樂團副指揮的同時,草創該團青少年交響樂團。他現在已跳槽,除專任克里夫蘭交響樂團常任指揮(Resident Conductor)之外,另創辦了隸屬該團的青少年交響樂團。
(27年後加注:林望傑先生,Jahja L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hja_Ling,目前是聖地牙哥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該團也附設一個青少年交響樂團。)
基本運作架構
走筆至此,應將美國交響樂團的基本運作架構略提一二。前文已提到,美國所有交響樂團皆屬私營;它們在法律上是合乎美國國稅法第501(c)(3)條文所規定的免稅非營利事業財團法人組織(注四);一般樂團整體架構概分三部:1. 董事會、2. 行政部門、 3. 演奏領導部門(即以音樂總監Music Director為首的「指揮」群,包括音樂總監(首席指揮)、常任指揮(Resident)、副指揮(Associate)、助理指揮(Assistant)等等一干人。)。 董事會設有總裁(President)一人,副總裁數人以及董事會幹部組織與各種工作委員會等;其職責是督導行政部門推展工作。行政部門則設各類工作組織:例如演出業務組、籌募組、行銷組、公關組、教育組、票務組、義工組等等。行政部門及其成員皆受董事會聘請的「行政總監」(Executive Director)所節制與領導;至於演奏領導部門在行政層次上與行政部門完全平行(音樂總監也是由董事會所聘請),行政總監與音樂總監必須相互協助,尊重對方,方能使各種業務順利推動。董事長看來像總舵把,但其實他也只是依照董事會決議,做出原則性裁示,或擔任制衡仲裁角色而已;董事長絕不類似我國首長制的樂團團長,權力無限到無人能制衡局面。
簡言之,美國交響樂團的核心架構建立在誰都不是老闆的等邊三角權力基礎上。三角邊各為「董事會」、「行政部門」與「演奏領導部門」,三角尖端則是「董事長」、「行政總監」與「音樂總監」。他們須嚴守相互尊重與合作的工作原則,這樣,工作方能順利進行。
行政部門、演奏會與「工會協定」
由於美國職業交響樂團演出場次多得驚人,一年少則百場以上,多則幾乎好像天天在演出(自然包括非正式演出,如校園教育性演出與不見報的非正規演出),因此行政部門中的演奏業務量極大,以應付有時一天甚至兩次演出的局面。演奏業務部門最主要是須將排練與正式演出的時間表等安排適當,不致發生排練時間不足或過多而讓樂團「燒錢」放空。(華盛頓的國家交響樂團的演奏業務部門,就因為指揮羅斯托波維奇超時排練,使樂團必須額外支付音樂廳超時費,而狠狠在羅老指揮檯面前擺上一面大鐘,「以資警惕」。這是我親眼看到的。) 值得一提是,職業交響樂團所謂排練或練習(rehearsal),係指「集體演練」,旨在熟悉即將演出的樂曲,並非為增強合奏技藝的訓練式排練。舞台上一切音樂問題,演出後外界之反應,皆由指揮(群)負責;他人包括行政總監或董事長等,無權也不便干涉。至於樂團與團員之間的工作關係,全憑一紙「工會協定」(Master Agreement)與個別聘約決定一切;雙方法律上地位完全平等。以行政部門為首的「樂團」(甲方),若因違反「協定」而引發嚴重事件時,團員可依法控告。在這種企業化營運下,演出成效自然是好,卻也出現不正常現象。有的樂團行政部門為樽節開支,將「排練次數愈少愈好」(注五)奉為圭臬;其本末倒置做法,使得演出可能在排練不足下進行。我曾遇不少團員抱怨此事,但為飯碗,也無可奈何。
結語
在概略勾勒出美國職業交響樂團經營管理之輪廓後,我們會發現這套法則是根據西方人文背景與社會環境發展形成的。我們可善加利用其中適合我們文化與社會環境運用的部分。其實台灣自光復初期設置公立交響樂團以來,轉眼四十年過去。其間,我們社會型態與大眾對文化品質之需求不斷地在改變,但影響音樂文化發展至鉅的音樂火車頭──交響樂團,卻未隨社會變遷轉型而大幅提升自身水準。我認為其原因在於我國公立交響樂團欠缺長期工作與經營目標,典章制度與行政管理亦欠周延妥實。目前,一個嶄新的國家級交響樂團成立在即,我們由衷盼望其運作上,能事先制定合理有效率的規章法則,不走原公立樂團閉門造車而來的過時老規則與老路,使新樂團能徹底發揮其社會功能。
注一:交響樂團本是不折不扣的演藝團體,「社教」僅屬其功能之一部;但目前公立交響樂團之性質與功能則完全被歸類為「社教機構」。不過美國國稅法501(c)(3)也以職業交響樂團是否合乎「以教育為經營目標」,來決定其所得稅減免資格。
注二:「第一級交響樂團」實指由「美國交響樂團聯盟」依據各樂團年度預算數所訂定的樂團分級標準中之首級交響樂團。這類交響樂團之預算數在五百萬至二千萬美元之間,其原文為Major Orchestra。「美國交響樂團聯盟」所制定的各級樂團分類名稱如後:
(A) 全職業與半職業性
1. 國家級(Major Orchestra)
2. 區域級(Regional Orchestra)
3. 都會級(Metropolitan Orchestra)
4. 市鎮級(Urban Orchestra)
5. 社區級(Community Orchestra)
6. 室內樂團(Chamber Orchestra)
(B) 非職業性
7. 大專樂團(College Orchestra)
8. 青少年樂團(Youth Orchestra)
注三:「進來」純係排練時的技術口語。當時狀況是樂團正在演奏一首韋伯的序曲。所指的團員分別在樂曲「呈示部」與「呈示部」反覆時,兩度「進錯」。這應說是指揮的down beat不明確,造成他「誤判」而出錯。不過出錯的聲音微弱,一般聽眾不易發覺。
注四:簡單說,美國職業交響樂團雖售票卻不藉此圖利。其收入除支付團員人事費用及一切開銷外,如有盈餘即再轉運用於演出業務之中;任何獲利不可歸私有。若違反此規定,經國稅局查出,即取消樂團免稅資格。
注五:職業交響樂團團員上班,無分「練習」與「演出」,概以「出勤」(service)數計算。「工會協定」中若書明每週為八個「出勤」,即指無論排練或演出,一週應上八個班。行政單位當然希望樂團對外演出次數愈多,練習次數則愈少愈好,這樣可增加營收,符合成本效益。
(寫於1987年,原載音樂月刊第66期)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