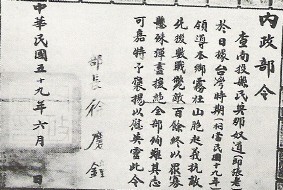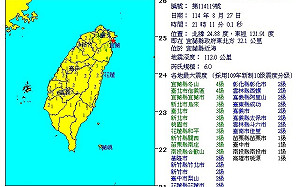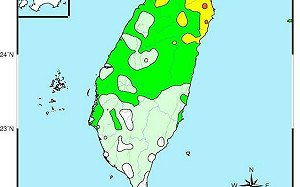距離7月19日國民黨召開全代會,提名2016年總統參選人的日子逐漸逼近,《條仔姊選總統》的鬧劇也就越演越誇張。不知是編劇太天才,還是演員擅自加戲,條仔姊超勁爆的「王金平若下屆要再回到立院,唯一辦法是參選區域立委」、「若訪美規格沒有比蔡英文高,幹嘛要去?」、「課綱微調調得不夠」到「一中同表」等言論,不斷引發藍營內部反彈。直到「不能說中華民國存在」,終於搞到連眷村老杯杯都「凍未條」了。
現正最夯:林俊言逼咬柯文哲不正訊問?北院今勘驗彭振聲認罪偵訊光碟
為了替條仔姊的失言(其實明明就是她的真言)消毒,7月5日國民黨在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時,特別邀她出席致詞。條仔姊2度提到中華民國的存在,還說「沒有先烈用生命抵擋侵略與暴行,用鮮血捍衛國家尊嚴,哪來的抗戰勝利?哪有中華民國的延續?又哪有今日台灣的民主自由與安定?」為了穩住眷村基本盤,其他權貴子弟出身的九趴馬、砂石朱、連爺爺與好兵兵等人,也都列席慶賀。
然而,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條仔姊比愛國同心會還激烈的言論,已經把總統大選提前OVER了;再找黨內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高級外省人來提油滅火,或許她心裡想的是,連落選都還嫌票太多了。舉個例子來說,《聯合晚報》7月4日由記者蔡佩芳、李光儀報導的〈郝批柯「意識形態 扭曲歷史」〉,又延續去年大選連爺爺與好杯杯的「皇民說」。
「郝龍斌說,不能否認台灣原來是殖民地,因為抗戰勝利才回到中華民國懷抱,台灣人民的地位才由二等公民改變過來。許多台灣人與大陸上的人一起抗戰,光復那一刻,台灣人歡欣鼓舞歡迎國民政府軍隊到台灣,只可惜當時的國民黨不爭氣、沒有做好,但不能否認光復那一刻,民眾是高興的。
郝龍斌說,很多人質疑光復只是被另一個政府殖民,兩者完全不相等。如日本人殖民時推動皇民化,僅限少數有地位有財產的人,必須改日本姓、燒毀祖宗牌位、改信奉神道教;或許有些台灣人對國民黨不滿意,但國民黨沒有摧毀大家原來的文化、沒有逼人改姓,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沒有不平等待遇,大家同受教育,只要考試成績優異升學不受限制。」
好兵兵要宣揚當年兩蔣奴化教育裡那些歷史課本的荒謬內容,那是他的言論自由。但有些人不說話,你只知道他無恥,聽了他說的話,才會證明他還無知。二戰期間日本對殖民地台灣實行的本島人「創氏改名」,那是「許可制」,不但沒有強迫性質,想改日本姓還有資格限制,例如必須是國語常用家庭,因此,只有柯文哲、李登輝等這些父母要當日本公教人員,或是林挺生、辜振甫等這些要與日本官方做生意的少數家庭。
簡單的說,日本領台末期所搞的皇民化運動,真正得以改姓的家庭不過2%而已。但1945年老蔣的亂軍一入台,針對原住民所惡搞出來的「逼人改姓」與「摧毀大家原來的文化」,好兵兵喜歡鬼扯歷史,就請鄉民們看一下這2個例子,自然能了解當年老蔣是怎麼亂逼原住民改姓,比日本更誇張的摧殘原住民文化。
第1個例子就是「李光輝」。1974年11月,印尼駐摩祿島空軍中尉蘇巴迪據村民報案,深山裡有個「野人」,就在12月16日率領了11人的搜索隊,經過30小時的跋涉,於18日在深山裡發現一間簡陋草房,屋外有個裸體男人正持刀劈柴,他雖然有日式38式步槍卻沒抵抗。透過翻譯才知他是日軍二兵中村輝夫,從1944年11月與部隊失聯後逃進叢林,就在這裡獨自生活了30年,根本不知道二戰已經結束的消息。
然而中村輝夫雖是二戰時的皇軍,卻不是來自日本,而是台灣的阿美族原住民,原名史尼育唔,出生於台東縣成功鎮都歷部落,8歲就讀都歷公學校,不但品學兼優,且擅長相撲和棒球,曾代表台東廳來台北比賽,被譽為最佳捕手。1943年10月奉召入營,編入「高砂義勇隊」,接受短期訓練後,被調往印尼參戰。但如今台灣已不是日本領土,史尼育唔該被遣返到日本?還是老蔣統治下的中華民國?立刻成為難題。
日本與印尼政府交涉後,對於史尼育唔要回日本或台灣,尊重他個人意願。1975年1月8日,史尼育唔自印尼首都雅加達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1月9日返回他闊別31年的老家台東。當年他奉召入伍時,家中有父親拉瓦、母親尼卡魯,另外還有4兄3姊,如今只剩68歲的大姐賴全妹與60歲的三姐林生妹還在人世。
為何史尼育唔的大姐與三姐都被改成漢名,而且一個姓賴,另一個姓陳呢?原來老蔣在台灣強迫原住民改名,就由戶政人員亂填,以致一家人有好幾種不同姓氏。史尼育唔雖然在戶籍上是死人,但他的日本姓名「中村輝夫」也被改為「李光輝」,他的妻子「中村良子」被改為「李蘭英」。老蔣為原住民的亂改姓名,連戶籍上已經死亡的都不放過,「李光輝」的例子以外,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劇中描述的霧社事件,被老蔣改名的事例更讓人噴飯。
霧社事件裡起義抗暴的乙種巡察花岡一郎與警手花岡二郎,2人並不是兄弟,也不是日本人。一郎本名拉其斯.諾敏(Dakis Nomin),二郎本名拉其斯.那威(Dakis Nawi),他們都是荷歌社的原住民,因為從小聰慧,公學校畢業後,主管「理蕃」事務的能高郡警察課,保送他們進埔里小學高等科。荷歌社位於高海拔山區,春天時緋櫻(山櫻花)盛開,在熱帶的台灣是少見的景象,日本老師就以「花岡」為他們的姓氏。
一郎與二郎是日本當局「理蕃」政策下的「樣板」,尤其是一郎,他還不是頭目之子,但成績優異,連劍道與柔道都很好,證明日式教育的成功。1925年(大正14年)入台中師範就讀,畢業後擔任霧社分社乙種巡察,都被當局與媒體大肆吹噓。乙種巡察其實並不負責治安,而是擔任教師。由於他日語流利,所以也是日本人類學者的得力助手。至於二郎在小學高等科畢業後擔任的「警手」,就是警局裡的雜役。
日本的「理蕃」政策不只是栽培原住民男性而已。一郎的妻子川野花子原名娥賓.那威(Opin Nawi),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原名娥賓.塔達歐(Opin Dado),她們是表姊妹,都出身荷歌社的頭目家庭,因為聰慧過人,被送到埔里小學高等科就讀。1929年(昭和四年)八月,高郡警察課命令花子和初子輟學,10月27日「南鎮神祭」(台灣神社祭典)時與一郎、二郎結為夫妻。
霧社事件剛爆發時,整個霧社山區被原住民制控,對外交通和信息全部中斷,「霧社皆亡」的音訊傳遍台灣各地,連日本中央政府也非常震驚。因為一來霧社原本是日本理蕃政策的示範區,教育、醫療等措施好過其他漢人居住的村落,甚至超過國內,但原住民竟然用「滅族」的手段來對抗。二來事件爆發後,外界隔了一天才知道,以致日本人死傷慘重。但警局的電話線卻一直都是暢通的,為何沒有通報?(莫那並不笨,如果切斷霧社對外的聯絡,附近軍警一定立刻來查線)
台灣總督府與台中州廳的官員原本認為,這些「未開化蕃」不可能發動如此完美的攻擊,讓當地日人完全被殺,就推論一定受過「撫育」的花岡一郎、二郎2人,控制電話線的2人不讓消息外洩,即使不是首魁,最少也是共謀。報紙的「號外」刊出後,日本人都憤憤不平地指責花岡2人「忘恩負義」,也反對懷柔教化式的「理蕃」政策。
但到了11月12日,更震撼的消息從濁水溪畔的軍警傳來。一郎與花子著日式和服,還有剛滿月的嬰兒幸男,一家3口成川形淌在血泊中。經過檢驗,一郎先殺了花子、幸男再切腹。二郎則穿著賽德克勇士裝在樹上自縊,其他20具花岡2個家族的上吊屍體,結實纍纍地把大樹的樹枝幾乎折斷。
一郎與二郎壯烈的自殺方式和淒美的死姿,再次震驚了日本當局,更撼動台島的各方人士。因為一郎的「武士道」死法,是一種謝罪的方式,也是一種義理。為了族人,他必須與日本對抗,但他確實也受過日本當局與師長極大的恩寵,所以他用切腹的方式還報他的上司與師長。而二郎及其家族選用原住民的自殺方式:上吊,集體自縊的照片也被日人尊崇不已。讚美聲從日本內地和全島各地傳來,也讓日本軍警在征剿行動上受到「節制」。
二郎的妻子初子,當時已經懷孕,後來生下二郎的遺腹子花岡初男(阿威.拉其斯)7個月後,在日警安排下,再嫁小她3歲的荷歌社青年中山清(畢荷.瓦歷斯)。1945年8月,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台灣重歸「祖國」懷抱,原住民莫名其妙的又換了一批主子,歷史又要重新被改寫。霧社的日本人殉難記念碑被拆毀,改立一塊抗日紀念碑。
老蔣1969年還批示,要將日治時期以武力對抗的抗日份子也送進忠烈祠,於是莫那魯道與花岡一郎2人,就這樣與福佬人簡大獅、柯鐵、余清芳、羅俊,還有客家人吳湯興、徐驤、羅福星等人,成了中華民國的「烈士」。
至於當年日本的殖民把戲,老蔣當然更要發揚光大。於是中山清被改名成「高永清」,初子被改名「高彩雲」,初男則被改名「高光華」。最可笑的是,改活人也就算了,老蔣是連死人都要改。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被改名為「張秀妹」後,1970年內政部明令表揚莫那魯道的褒揚令這樣寫著:「查南投縣民莫那奴道(即張老)於日據時期領導本鄉霧社山胞起義抗敵……」。
莫那魯道是為了他自己的「祖靈」去對抗日本,不是為了中國去對抗日本,他一定無法搞懂自己為何死後變成了「張老」。日本改原住民的名字之前要教育10多年,老蔣卻不必花半點力氣,就可以從花岡三郎、四郎、五郎一路改到N郎。唉!要玩「改名」遊戲,小日本哪裡是我們大中國的對手?好兵兵要比較歷史上日本與老蔣怎樣強逼台灣人改名,就請看一下這2個例子。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