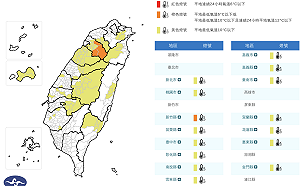生命的道路玄妙難測。
1969年我在印大的第三學年度開始後,我要跟隨的論文指導老師Charles Krebs突然決定轉校到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職。我因剛結婚的關係,希望能過著平靜求學的新生活,決定留在印大,不隨他到加拿大。Krebs教授的離開引發了我很多必須面對的煩惱,我必須找一位新的指導教授;必須從一個比較熟習的專業領域,再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回到學校後, 我內心感到十分挫折懊惱,似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揮之不去。 剛結婚成家,又一無所有,又已年過三十,想到未來學業的壓力,想到家庭的責任,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還有像以前那樣「什麼都不驚,向前走」的意志力,心情自然更煩悶、恐慌。當時很多結婚的同學得到PhD 學位 (Doctor of Philosophy) 時,都幽
我選擇了一位專門研究有關爬蟲、兩棲類的生態的年輕教授Craig Nelson作為我的指導老師。 Nelson教授,在所內被譽為十分smart的年輕教授。我十分欣賞他的演化學課。 那年他從科學基金會拿到一筆研究經費,研究兩棲類的生態區塊分佈問題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niches),研究地點是南美洲的厄瓜多爾 (Ecuador)。在研究生中,他挑選了我來執行這個研究計畫。說實在,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有經費,可旅遊看世界,又可得學位,何樂而不為? 如果我當時是單身的話,絕不會錯失這個大好機會。但是,我需要為太太著想。當我回絕Nelson教授時,他很不高興。 之後,他也一再地要求我重新考慮,我也一再地婉辭。 為此,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了一段時候。
1969年第一學期。 我希望靜下來好好尋找論文的題材, 只選修了論文研討。 Nelson教授除了專研爬蟲、兩棲類的生態及演化學外,也對科技社會學、科技政治學涉獵甚深。我在他的實驗室中出入頻繁,也接觸了不少他收集的文章。有一次,他看到我閱讀這方面的文章時,很高興地說,「科技的影響及衝擊將來是社會、政治、文化等的重要課題。你一定要注意。」就像Charle Krebs 教授在第一堂生態學上課時談到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啟發了我對科學哲學的興趣;Nelson 教授也因他的一句話帶引了我進入科技社會學、科技政治學的領域。 以致,十幾年後,我回台後第一次在台大動物所及東海大學開了一門「生物哲學」;出版了三本專業以外所謂「不務正業」的書籍:「科技文明的反省」、「打破科技中立的神話」及「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這都是我在生態學及演化學專業以外,因受兩位老師的啟發所得到的額外知性的禮物及發展,讓我對自己專業以外的世事有了更寬廣的視野,而不受自己狹窄專業的限制。 「一個好老師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傳道、授業、解惑(instruct),不如說是啟發 (inspire)。」對我而言,誠非虛言。
這一學期的自習、旁聽,我自覺對我的專業開始有了方向。 但我心境也開始有了變化,不時感到疲憊倦怠(listlessness)與焦慮不安(restlessness)。 年輕時,這種感覺常不定時的發生在我的身上, 我自稱為「生存的真空」(existential vacuum)。 這種「生存的真空」產生的不安感,常讓我想換個新的環境,尋求「變、變、變」。 根據生態學研究,齧齒類的族群中,有少數的比率屬於傾向向外遷徙的「基因變異群」(genetic variants)。他們經過一定的時間,在外界環境的變遷下,都想離開原來的族群,去找一個新的合適的區塊(niche);其他大多數的比率都屬於安於現狀,不想外移者。人也有類似現象,有安於現狀者;也有少數不安於現狀者。可能是個人的基因作祟吧!我想我是屬於後者。 從淡江英專、台大、師大,從文學到生物學,我不是一直都在「變」嗎? 我常想,如果我一輩子都作同樣的工作,一成不變,當躺在床上吐出最後的一口氣時,我一定會很遺憾後悔的。從小學至今,三十多年的歲月都躲在學校裡讀書,我必須要換個環境。
來美已翻騰了快五年矣,五年埋首的讀書過程中,也體驗美國60年代發生的政治大變動, 再加上演化學及生態學的啟示, 我感受到生命的壯闊和繽紛,可以海闊天空,任人遨遊。1970年5月,我通過了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也獲頒碩士學位後,心情浮動不安的情況更加劇烈,腦海中不時環繞著各種問號。 讀書、結婚、就業、退休? 隨波逐流? 難道大學只是提供職業教育,保障就業的場所嗎? 生命誠可貴,可是活著是為什麼、為誰,目的何在? 我到底要活出什麼樣的生命? 要追求什麼生命的意義?要尋求什麼生命的價值? 難道唯有在學院、研究所及正規的教育中,讀書、攻讀博士學位,我可以尋找到生命知識、價值及意義的答案嗎? 教授可以給我答案嗎? 閱讀偉大哲人大師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或是只有我自己才可回答? 這些問題值得問嗎? 矛盾複雜的掙扎似乎在我腦海裡試圖尋求一條出路。 夜闌人靜時,想起在台大時受到史懷哲的影響及對非洲的好奇。 此時,我內心一直聽到史懷哲的呼喚,揮之不去。 我曾向台大時的女友提議過,畢業後一起到非洲去,「您瘋了,您自己去」是她的回應,我也堅決地回她,「我一定會去。」 現在,有了不同生命價值觀的伴侶,我想太太一定會舉雙手贊成,支持我; 因為門諾教會設有「門諾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專門招募支援非洲的志工,所有門諾教會的會友都為他們的年輕人到第三世界國家當志工為榮。 我告訴太太我的心情,想暫時輟學,去探索生命中沒有碰觸過的角落及不同生命的經驗,去尋求生命的意義。 我聽到了非洲、史懷哲的呼喚,我要到非洲去! 我可從事教育的工作,你可以從事醫護的工作,我們可以在非洲開創生命的新經驗。 她猶豫了好一陣子,僅以沈默回答。 有一天,她握著我的雙手,凝視著我說,「Proud of you. Let us go.」 我緊緊地抱著她,強忍著盈眶的熱淚。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