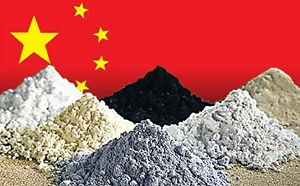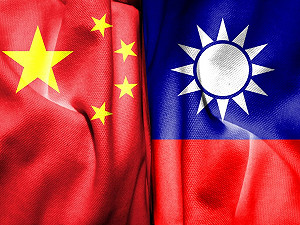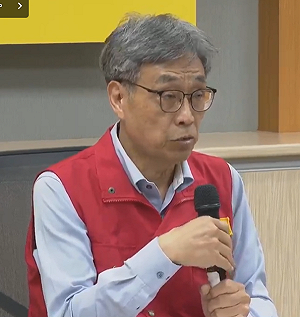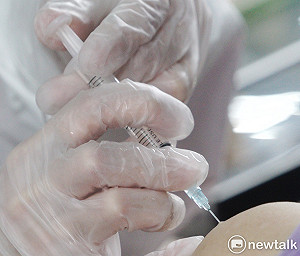國民黨主席委鄭麗文於舉選時期在(29日)吳稚暉紀念活動時表示,她帶領的國民黨,要讓全部的台灣人都能自豪、自信地說「我是中國人」,國民黨要有清楚中國認同,不要再掉入民進黨設下的陷阱。當鄭麗文講說《國民黨要有清楚的中國認同》時,我真的想問這位黨主席:共產黨統治之下,還有以前國民政府在統治中國時所講的《中國人》嗎?
一、使中國人產生斷層的主因=以黨治國
現正最夯:李四川表態參選新北市長!劉和然確定不選了、侯友宜發聲全力支持
中共的體制基因並非中國歷史本身的演化產物,而是來自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國家體系(Party-State System),這正是共產國際在20世紀輸出的核心模式。它有幾個基本特徵:1、黨高於國家:國家不是獨立機構,而是黨的工具;所有權力都要通過黨組織的運作。2、政治合法性來自革命,而非民意或法治:黨自認為是歷史的代表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此權力不是被授權,而是被「歷史使命」賦與正當化。3、持續的鬥爭哲學:即便在和平時期,也必須不斷「鬥爭」以維護政權的安全。這使得這個體制具有高度的防禦性與排他性。
這些結構就共同形成了「以黨治國」的根本邏輯:國家為黨服務,社會服從政治,政治服從意識形態。
二、中共建國後的社會(1949–至今)
中共建國之後,國家與社會完全合一,一切組織都被納入黨的體系(此即黨政軍一體)。
在這種政治體系之下,思想被統一化,從「思想改造」到今日的「政治學習」,政治就成為精神生活的核心。於是整個社會行為就被導向至《集體服從》,個人行為以「政治正確」為最高準則。
在這種社會體制之下, 人的性格就有如下的特色:1、外表順從、內心戒懼;2、習慣觀察「上意」行事(政治的敏感度極高);3、公共責任感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保身文化」與「沉默策略」;4、在情感上對國家既有依附又有不信任。這種人格在政治心理學中,常被稱為「權威順從型人格」,以即是一種被制度長期馴化後的集體心理模式。
三、「集體主義」取代了「個體責任」
在民國時期,人們仍被鼓勵作為「獨立的公民」思考。但在中共體制下,人被定義為「集體的一部分」, 最終要服從於「黨」、「人民」、「國家」這些被抽象化的整體。其結果就導致:1、道德判斷變得相對化,「只要是黨的決定,就是對的」;2、個人行為傾向於服從上級而非內在原則;3、社會中形成「責任消散」的現象——人人參與,但沒有人負責。這使得共產黨下的中國人整體性格變得更務實、謹慎、現實主義化,但同時也更缺乏信任與道德勇氣。
經過七十多年,「以黨治國」的政治文化逐漸滲入社會心理,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怕牽連、怕被利用);知識分子普遍失語,害怕言論出事;年輕世代走上功利化、犬儒化,也就是別談理想,談錢最安全。
四、全世界的癌症=共產中國
在以黨治國之下,權力極具封閉性,共產體制的核心在於權力集中與不透明。只要權力不透過制度分立來制衡,政治就會以「控制」為主,而非「共存」。共產黨的意識形具有態壟斷性, 中共仍將意識形態作為合法性的基礎(「黨領導一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意味著任何多元思想或制度競爭都被視為威脅,這與現代國際政治的「共存共榮」之開放性根本相反。 在黨國體制下,「政權安全」永遠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這種邏輯使得外交、經濟乃至教育政策,都是首先服務於黨的穩定,而非社會整體福祉。這就形成中國的對外政策的特色:
1、在政治層面上,中國的外交模式本質上屬於現實主義外交(Realist Diplomacy),亦即以國家利益、主權安全與權力平衡為最高指導原則。這種模式在與其他大國互動時(例如美國、俄羅斯、歐盟)能形成某種「互相制衡的穩定」。例如:中俄之間在戰略上合作,並非真正的盟友,而是出於共同抗衡美國的需要。中美之間即使有激烈競爭,仍維持一定層面的溝通,因為雙方都知道全面對抗的代價過高。結果,這是基於實力與利益的穩定,而非信任的穩定。
2、在經濟層面,相互依存只是帶來暫時的穩定。中國與許多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及歐洲國家)在經濟上高度互賴。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亞洲、非洲、拉美多國建立了經貿連結。這樣的經濟依存確實能維持一段時間的穩定關係,因為雙方都有利益要顧及。但問題在於:一旦經濟利益失衡(如債務問題、貿易逆差過大),關係就會惡化;中國的投資往往附帶政治條件,引發對方國內的不滿或警惕。結果,這是交易型的穩定,而非制度化的穩定。
3、在價值與制度層面,與諸多國家缺乏共識而造成潛在不穩定。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價值觀與多數西方國家不同,缺乏共同的「規範語言」(normative language)。例如民主、人權、法治等概念在國際社會中仍是衡量關係的關鍵。但中國拒絕這些普世語言,主張「各國制度平等」、「不干涉內政」,這雖可避免衝突,但也讓關係難以深化。結果就是中國與他國的關係多停留在「合作而不信任」的層次。
傳統中國的「天下觀」是一種文化性、秩序性結構:中國自居為文明中心,以文化感召周邊。「王道」意味著以德化人,而非征服他人,雖然事實上常常成為侵略他人的大義名分。但至少傳統的王道思想(源於儒家)主張以「德」服人,講究仁政、和諧與秩序。它是一種帶有道德正當性的政治理念,強調「禮義」、「仁德」與「天下為公」;在外交層面上,體現為「懷柔遠人」、「不以力服人」。但共產中國的意識形態則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套思想強調階級鬥爭、革命與權力鬥爭,講究「敵我」區分。即使後來在實踐中更趨務實(例如鄧小平以後),其核心仍是「現實利益」與「權力均勢」,而非道德感或天下秩序觀。
近年中國官方在外交修辭中有意重提「天下觀」與「王道思想」的元素,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等,但這種話語更多是文化包裝,意在塑造文明自信與話語權,而非真正回歸儒家式的王道精神。共產中國的外交行為,不具備傳統中國「王道」的德性與秩序意識,而是以現實主義與權力邏輯為主軸。它或許借用了「王道」的語言,但實質上更接近「霸道的現代化版本」——只不過披上了文化與合作的外衣而已。
五、這就是鄭麗文口中的中國人嗎?
鄭麗文曾說她為什麼脫離民進黨?其實一聽也知道那只是藉口吧!她應該知道民進黨至少沒有以政治力量強迫人們接受黨國教育吧。但是,她要讓台灣人自豪講出自己是中國人,她可曾了解到現代的中國人跟古代的華人已經產生斷層,,難道妳還要台灣人過著比國民黨更嚴厲的黨國統治嗎?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