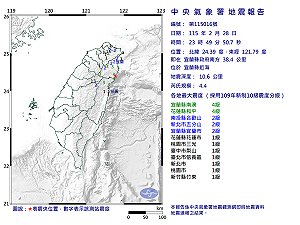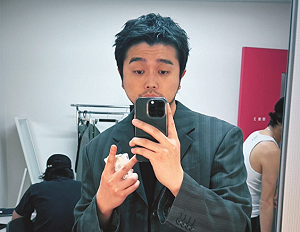藍委拋出將總統選舉改為兩輪決選制的修法倡議,這裡的修法是指修改《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將我國總統選制改為兩輪絕對多數制,引發社會各界熱議。有網友一針見血的評論;「笑死 ! 藍白合就好了,還要修憲?」、「難道要改到國民黨當選為止喔」。
平心而論,按照兩輪的制度設計,小黨很容易在第一輪就被邊緣化,也就是被藍綠支持者「棄保」掉。尤其現在藍白合氣氛濃厚,如果沒有談好條件,柯文哲跟黃國昌恐怕只能繼續騎車謝票,看不到入場券。另一方面,羅智強自己也說,不靠民眾黨力量,下架不了賴清德;反過來講,民眾黨沒有國民黨也一樣難。所以這個提案,到底是想合作還是在卡住對方?真是耐人尋味啊。
這裡要釐清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現行憲法是否已經明確選擇了「相對多數決」?若答案是肯定的,則任何改採「絕對多數決」(不論是兩輪制或排序複決)的修法,都涉及憲法層級的制度扭轉,難以僅以法律修正逕行。以現在的國會結構,修憲案成案不易,除了必須立委1/4提案,3/4出席,出席3/4通過,修憲案複決門檻必須高達公民數50%。藍委若推動修憲必然不可能成功,最後還是只能強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法,建立「改革」的形象而已。
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 用語本身就是相對多數的技術表述
主張修改法律即可修改總統選制的論者認為,在兩輪決選制中獲勝的當選人,不論是在一輪選舉中即以過半數當選,或是在第二輪選舉中得票贏過對手而當選,也都是「得票最多」的候選人,仍符合《憲法》「以得票最多的一組為當選」的規定,因此藍營不用再推動修憲。
當前熱搜:川普下令「史詩怒火行動」轟伊朗 國會炸鍋:未經授權開戰?
然而,《憲法》條文的規定是否有這樣的文義解釋空間?事實上,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看,《憲法》規定由得票「最多」而非「較多」的候選人當選,即預設選舉中可能會有3組或以上的候選人存在,並由得票數排名第一的候選人當選。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明文規定「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選舉法學與立法技術上,這是典型的相對多數表述:只要名次第一即當選,未要求獲得超過有效票數半數。若立法者要採絕對多數,慣常做法是直書「過半數」、「逾二分之一」,或設置「未過半則進入下一輪」的條件句。換言之,文字既「只指名次、不問比例」,其規範意旨便是「相對多數即當選」。將此種用語硬解釋為可容納「絕對多數」的彈性條款,等於抹去選制語彙在立法技術中的既定分工,於文本語義上站不住腳。
若從憲法體系來解釋,憲法增修條文在需採「絕對多數」之處,向來明白書寫。例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第十二條等處,一旦涉及「特別多數」或「過半門檻」,文義即清楚標示。這種起草技術的穩定性,構成了解釋的體系脈絡:同一法典體系中,對不同決定規則以不同語句明確區分,是為可預期性與法的安定性服務。若在總統選制上忽然改採「得票最多」,但又暗含「需過半或另行決選」的看不見條件,等同破壞體系的一致表述。
兩輪制的合憲性問題不可迴避
若承認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確立相對多數,那麼改採兩輪決選制(其結果是要求當選者須在第二輪達到「過半」)即屬「從相對多數改為絕對多數」的規則更迭,原則上涉及憲法層級的制度變更。不可以單純只修《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或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來導入兩輪制,這將與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的技術規則發生衝突,構成違憲樣態。
從程序正當性與法治國原則出發,當憲法層級明確改寫決定規則,才能由選舉法完善第二輪的間隔、入圍門檻、經費上限、辯論義務、爭訟機制等細節。如此不但尊重憲法位階,亦可避免以法律偷渡重大制度工程的風險。若在未修憲的情況下逕以法律導入兩輪制,最終極可能由憲法法庭以「牴觸憲增第二條第一款」為由宣告違憲或限期失效。這將把國家投入高成本的制度過水一遍,卻又回到原點,對選務安定和社會信任傷害更大。
眾所周知,憲法法庭長期在重大制度爭議上欠缺即時性與可預測性,社會自然會質疑其作為「憲制守門人」的能力與意志。憲法法庭應明確釋示規則位階與程序要件,避免立法部門以低位階法律承載高位階變更,並以程序性判準維持選務安定。這種制度怠惰最終會反噬司法的權威,憲法法庭若不自救,沒有人能替它挽回憲政信任。因而,導入兩輪制並非「法律細節調整」,而是「憲法級制度變更」,正當路徑是修憲在先、法律配套在後,藍白故意挑起爭端,綠營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