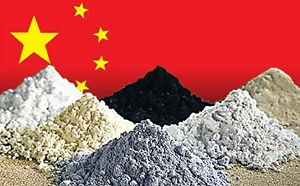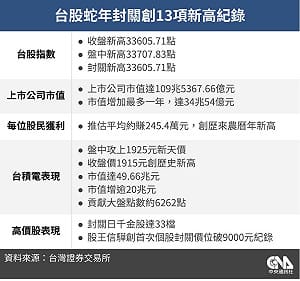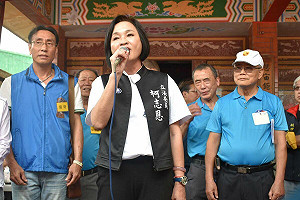美國前總統川普重返政壇,其「2.0時代」的關稅政策如重磅炸彈般,引爆全球股市,重擊國際貿易體系,並對全球製造業供應鏈帶來強烈衝擊。在川普口中的「解放日」,彷彿意味著全球化時代的終結。他再次以極具破壞力的反全球化手段,揮舞關稅大棒,狠狠針對以代工、製造業為主的國際貿易夥伴,透過美國的「有形之手」干預市場機制,試圖以政府力量重塑產業格局。
關稅2.0是豪賭?抗議民眾走上街頭
這場政策風暴不僅為全球經濟帶來重大下行風險,更可能反噬美國自身,引發通膨惡化、經濟衰退,甚至步入蕭條深淵。
台灣時間4月3日凌晨4點,川普重磅宣布對全球180個國家實施「對等關稅」,震撼全球政經格局。這不是一次常規的貿易政策調整,而是一記重拳,直接砸向過去30年以全球分工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隨後,中國貨櫃暫停出貨,越南工廠也陸續停止或取消對美出口,國際供應鏈陷入混亂。
這場「關稅革命」的背後,會是保護主義的回歸?還是全球化模式的根本動搖?
當前熱搜:傳為檢察總長提名舖路!總統府准法務部政次徐錫祥辭職 調最高檢主任檢察官
中國、歐盟、英國、加拿大等主要經濟體立即表態,揚言報復或要求協商。而在美國本土民間團體也發起名為「把手拿開(Hands Off)」的抗議活動,在全美50州舉行1200場遊行,數以萬計的抗議者走上街頭,表達對川普及其顧問馬斯克解散聯邦機構、加徵關稅等一連串舉措的不滿。這場貿易與民意的雙重對撞,為川普2.0時代拉開戲劇性的序幕。
美國曾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如今倒行逆施?
全球化,不是口號,而是一個深耕數十年的經濟體系。從1990年代開始,美國企業主導了全球產業鏈的布局,透過外包、代工與技術輸出,大幅降低成本,享受了長達30年的低通膨紅利與穩定經濟成長。國際貨幣基金(IMF)定義全球化為:貿易往來、資本流動、人口移動與知識傳播四大支柱,美國無疑在這四個面向都是最大贏家。
據數字統計與世貿組織總幹事伊維拉發表的「美國是貿易大贏家」指出,2023年美國的服務出口額超過1兆美元,占全球總額13%,2024年再成長8%;美國與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有服務貿易順差,2024年順差總額近3000億美元,包括金融、專利、娛樂、高科技等高附加價值項目。其中,光是智慧財產權的授權費與版稅收入就超過1440億美元,遠超其他國家,可說是在高附加值服務領域近乎壟斷,支撐起410萬個高薪崗位,平均時薪較製造業高出25%。數據會說話,美國真正的強項早已不在製造,而在服務。
然而,川普卻選擇對抗全球分工下的製造業,重啟貿易保護主義,聲稱唯有讓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才能恢復工作機會與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樣的論述表面上有其「愛國主義」號召,事實卻是政治人物以民粹言論包裝,刻意轉化為民怨出口。
關稅能帶來製造回流?現實恐是產業斷鏈
川普的邏輯顯得簡單又直接,卻少了通盤謹慎思維:若企業想享受零關稅,就必須在美國本土生產。然而,這無視了全球分工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整合生態體系。
美國人穿的Nike球鞋、用的iPhone、開的Ford汽車,雖然都是美國品牌,卻幾乎都在境外製造。這不只是為了成本考量而省錢,更因為全球供應鏈中的專業分工無可取代。若單純以關稅「懲罰」海外製造,結果可能不是工廠回流,而是成本飆漲、消費者買單,甚至讓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再次被削弱,亦可能引發國際拒買高價、抵制美國貨的風險,也可能使得出口商減少對單一美國市場的依賴,轉向布局其他國際市場。
更何況,美國已不再是典型的製造導向經濟體。當前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創新、品牌、科技、資本與智財權。川普指望透過提高關稅讓工廠回流,就像是頭痛醫腳,對症卻不對病。
再者,即便是製造業回流,缺乏足夠的誘因、政策補助,企業又如何負擔美國高勞力等生產成本?高關稅與高產製成本都是壓力,提高採購與售價是必然的路。然而可預見的是能抵抗的成本壓力的企業短暫戰鬥活下來;無法長期負荷成本、接不到訂單、失去競爭力的企業就面臨縮小規模、生存危機,最終如同多位經濟學家憂心整體經濟將走向衰退。
川普式邏輯:關稅換回製造?錯置的保護主義
當全球主要經濟體準備迎接AI、數位轉型與綠能革命之際,川普卻選擇用20世紀的工具應對21世紀的問題。他以為透過政府看得見的手,進行政策干預、設限與懲罰,就能扭轉美國製造業的頹勢,卻忽略了現代經濟運作的關鍵早已從生產轉移至創新與服務。
川普反全球化的思維,其代價不僅是國際緊張升溫,更可能帶來全球經濟的下行壓力,尤其是供應鏈中斷、投資信心動搖與企業成本劇增的多重衝擊下,最終受害者或許不是他國,而正是美國自己。
雖然全球化為多數人帶來消費便利與經濟成長的同時,也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但真正該改革的是全球化的「制度設計」,而不是貿易本身。若一味訴諸關稅壁壘與民族主義,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推動世界走向更加封閉、分裂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