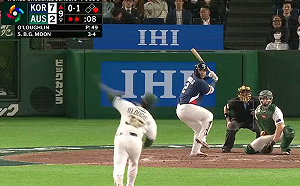翻到那一頁筆記的時候,我總會訝異它那麼短。升上高三準備學測的暑假,我把四冊社會科課本裡的內容整理成一本讓自己能夠安心的寶典,那一年,所有與記憶相關的事,我一律信奉寫下來才能算數。後來,我上了大學,開始當起高中社會科家教,有學生家長問我能不能把整本筆記拿去翻印。送回我手上時,每一頁右下角多了影印店輕輕用鉛筆寫上去的頁碼,我才知道總共有一百多頁。
戰後臺灣史的部分只有三頁。我會深吸一口氣,盡量假裝一視同仁地用「你知道單一選區兩票制是什麼嗎」、「你知道行星風帶為什麼會隨季節移動嗎」的語氣問出「你知道二二八事件跟白色恐怖是不一樣的嗎」。那是人聲鼎沸的車站旁星巴克,那是高級住宅區一樓的會議室,那是打通了大安區電梯大樓兩層自成一戶的家,桌上還放著媽媽舀給我的雞湯,加了整顆的大鮑魚煨煮。他們的回應總是口徑一致,老師,這個會考嗎?陽光斜斜地曬進來,一切都被拉長了一點又一點。我每一次都像在哄我自己一樣的回答,這個會考。
全站首選:卓榮泰私人包機可用松指部? 顧立雄:可以、那是軍民合用
我其實沒有印象自己曾在高中的任何考卷回答過這一題。考卷上的答案,往往會在填答過後,被記憶自動作廢,會發芽的疑惑通常是沒有答案的。例如,是誰允許這樣的事發生?我們怎麼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
◆
我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感覺,是因為看了影集《一把青》。2015 年,我緊追著每週的更新,跟著女學生與飛行員經歷國共內戰,一路從瀋陽退到臺灣。在所有顛沛流離中,只有一個段落讓我不得其門而入。那是一場撤退來臺灣以後的審判,飛官自陳與共產黨無關,下屬作證說他沒有接觸過共產黨人,老長官擔保他沒有向共產黨投誠,最後飛官仍然被強押著在寫好的自白書上蓋了手印。他一面掙扎,一面大叫「我不是共產黨」,但是只有如此具結,才能保他平安回家。他一直喊,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共產黨彷彿是一種能夠自圓其說的悖論,沒有人希望這裡出現共產黨,這裡也沒有人是共產黨,但最後,還是要有人當共產黨。我覺得一定是漏掉了某些事由,整件事才看起來像一團迷霧,我因此去了書店,想找到影集的原著小說看看。我注意到與原著小說一起擺放在鋪面的新書推薦,那是 2015 年,那本書是剛出版的《無法送達的遺書》。
全站首選:經典賽韓國7:2擊敗澳洲晉級爆控分爭議 網友不解:就為噁心台灣?
書裡的人全部被判處死刑,因而有遺書。遺書內容有的簡短,有的綿延,不捨把話說完。我看了三篇,因為哭到鼻涕流到嘴裡而倉皇逃離書店。死之前的憂慮、死之時的戛然、死之後的清算,都隨信紙被扣留在檔案局,徒留一片空白給家屬。直到政治受難者的家屬調閱檔案,偶然才發現他們最後有留下一些話,卻連同生命一起被黨國沒收。
當集體的苦難被細細分辨成為一個人的、那個人的生命,以及在意他的人的生命,你會很想知道為什麼可以?苦難之所以令人陌生,是因為個人對個人的暴力是需要練習的,我們很難在一個大好的日子,心無罣礙到只需要思考等一下喝奶茶還是鮮奶茶好的情況,突然用滅火器打破路人的頭,所以我們也無需為此提防;而國家對個人的暴力,國家可以訓練出一群習慣施展暴力的人,是奠基在長遠以來如何約束個人對個人的暴力,積累轉化而成的承諾。社群或說社會的價值,在於我們享有個人生命能夠安然存在的共識,有人狠狠破壞這個規則,卻不用付出代價,這種事是怎麼發生的?
上了大學,我才知道這件事是由〈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所組成。國民黨政府有憑有據的,鋪排了一個完整的系統殺人。
◆
我後來發現,不經意的死沒有那麼簡單。舉凡美劇,主角在情緒失控下用磚頭、花盆、煙灰缸之類的重物狠狠砸了別人的頭,看見對方倒在一片血泊裡,就以為自己殺了人,衝回家一邊洗澡一邊哭,十分鐘過後,當那個人搖搖晃晃地爬起來,施暴的人頭髮可能都還沒吹乾,屢試不爽。好想一開始就穿過螢幕把水龍頭關掉,叫他聽我的,先不要洗了。
人要死,必須精心安排。那個流程是這樣的——第一步,〈戒嚴令〉在戰爭時期得以發布,接戰地域內,刑法名列的某些罪行,得由軍事機關審判,包含內亂罪與外患罪。第二步是〈懲治叛亂條例〉加重刑罰,內亂罪、外患罪得處死刑,沒有實際行動但執法人員認定你有在盤算的陰謀犯、預備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最後是〈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具體而言是你知匪不報可以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破獲匪諜案件,無論是檢舉人、承辦人員都會由國庫支付獎金。
上述最初的問題是,國民黨政府在沒有交戰的臺灣,實施了 38 年的戒嚴。所以才有接下來的問題,不是軍人的一般民眾也得接受軍法審判。它與司法審判的差別在於允許刑求逼供,再以自白作為證據,沒有辯護律師,也不得公開審判。因此狠心不只是個人選擇,是這個制度,渴望每一個人被屈打成招,並且排除任何能夠說明情況的人。
你知道他們不好,與你知道他們處心積慮的謀劃如何對每個人最壞,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
每當歷史科家教的進度上到戰後臺灣的部分,我總有那麼多話想要說。課本上的條目,如何展開成為一個人的生命——軍法審判允許長期扣押的意思是,柯旗化第一次被捕,先是在高雄的拘留所關押一個月,又被移送到台北的保安司令部,抵達台北兩個月以後才進行了第一次審問。被迫離家時是夏天,真正前去服刑已是隔年一月,這半年的監禁,不是刑期,沒有任何理由與可見的盡頭。沒有在課本上的內容是,那兩個月,他被關在保安司令部的單人牢房,牢房只有九十分公分寬、兩百四十公分深,他必須睡在僅隔了一層木板的排泄處之上,從通風管裡聽取其他獄友的聲音。
儘管我有那麼多話想說,但是我們總有安靜下來的時候。那時候我會害怕與學生對上眼。我害怕我們對於這一段話的感受,直到我話語的極限,依然沒有接點。那既是他的問題,也是我的問題。我們無法共同定義這是一個故事、一段知識,還是一個不會成立的題目?這一次,他們不需要問我,也知道這些內容不會出現在考卷上。他們還是會認真聽完,然後問我要把什麼寫成筆記?
高三的我,從歷史課本上對照著擷取下來的重點,那一頁筆記上,其實根本沒有寫到白色恐怖這四個字。現在的我,也沒有把一個時代的傷痕,摘錄成一句筆記的方法。我仍然相信寫下來的東西算數,但是有時候,寫下來的東西也不能作數。太多苦難的總和竟然會等於,一次、兩次、一個、兩個學生乖巧而困惑的表情。
◆
我即將從歷史系畢業的那個學期,我非常喜歡的作家/學者湯舒雯應邀演講。那是一堂開給大一新生的必修課,大學國文一,她來談給「後白色恐怖世代」的同學聽,我們該應該站在什麼樣的位置,來理解關於白色恐怖的記憶與再現。那是可以報名入場的演講,我做了很多筆記,幾乎想把她投影片上的文字隔空複製貼上到我的 Word 檔,筆記最後卻草草收場。文件內沒有留下虎頭蛇尾的理由,但我一打開筆記的檔案就想起來了,我之所以不敢也不想留下痕跡,是因為我哭了。我覺得那樣好丟臉,我聽她分享自己遇上政治受難者的情景聽到哭出來。我羞於記錄自己廉價的煽情。
後來,我找到湯舒雯寫下這一件事的公開臉書貼文,事情始末與她的口述沒有太大的差別。文章是這樣的,她去到一場講座談白色恐怖的文學救贖意涵,遇上一位聽眾,他是政治受難者,他坐在台下默默地、不斷地擦去眼淚。結束後,她鼓起勇氣去找長輩握手,她向他道謝,她無從謝起,可是她想要道謝,兩人都哭得無法自拔。最後長輩的伴侶遠遠地回頭,用嘴型向她說,再見與謝謝,謝謝妳。她反覆在文章裡寫,她為了聽講座時的哭泣感到丟臉,可是她停不下來,那些事她早就已經知道了,可是她停不下來。
演講那年,距離她與長輩在街頭的握手,剛好十年。十年間,人一定有過千百次心冷卻下來,決定不再為苦難流淚的念頭,但她仍然慎重地講了這個故事,於是像我這樣的人聽見,我同樣忍不住流下更難為情的眼淚,讓之後的我下定決心,再說一次,再說一次。
直到下一個人聽見。
作者【張嘉真】
1999 年生,高雄人,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目前就讀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曾獲馭墨三城高中聯合文學獎、台積電青年文學獎、台大文學獎。曾出版短篇小說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三采文化)。
【被雷打到的瞬間】
配合著「519 白色恐怖記憶日」,新台灣和平基金會邀請了朱宥勳偕同台灣新生代作家一起談談各自的「白色恐怖」經驗。到底,這些現代的台灣青年,是在甚麼樣「被雷打到的瞬間」,開始覺得這一切都不對勁?
這群新生代作家,生在解嚴前夕與民主化的初端。不同於在戒嚴中成長的人,他們多了一些直接,少了顧忌,也因為網路時代,只要有好奇心,白色恐怖的故事都足以讓人對過去低迴、憤慨與行動……。
本篇發表於「被雷打到的瞬間」專欄。將永久鏈結加入書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