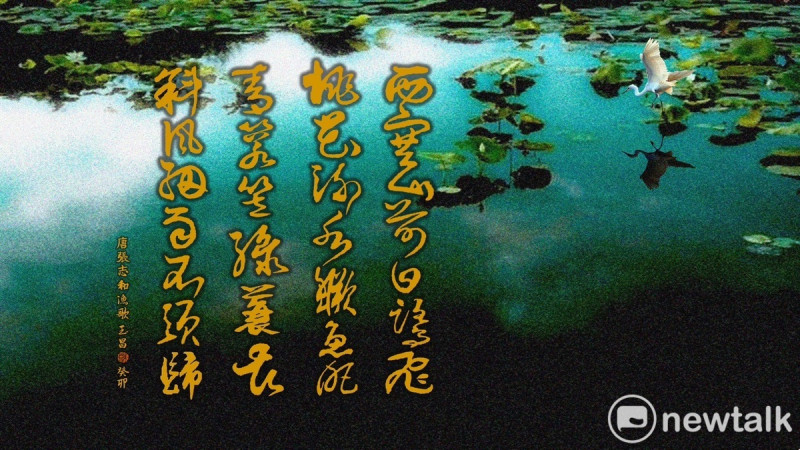宋代以來,研究者將〈漁歌〉焦點集中在「其一」的地點之爭,依史料所載,作品是張志和受邀於顏真卿湖州刺史任上一次聚會的即興之作,那麼,席間完成的五首作品,內容又觸及五個不同時空修道角色,理當是腹中有墨或腦內「印象」盤整之作。若非聚會之作,就有可能是在不同時間創作的作品,若真如此,待考證處勢必再添膠著。不可否認,作品描述地點對還原歷史現場極其重要,但因此失焦創作本意,抑辜負了原創核心?過於執著地點而忽略作家傳達的內核精神便顯顧此失彼,對受教的讀者更是一種損失。所以應該回歸作品的中心思想。
鶯脰湖登仙
小舟佇立在粼粼的湖心之上,舟上人緩緩朝著水面鋪下一捲席墊,隨即跨舟端坐席上,只見他身體沉墜時舉臂指天,以從容姿態向岸邊注視的道友灑脫揮別。
全站首選:全球軍力人數榜 ! 「它」203萬居首、美只排第三、「這國」預備役竟達500萬...
一路見證「預知死亡」過程的顏真卿,頃刻間,陷入張志和選擇以「水解」得道的思緒中,因著湖面傳來的鷺鳥叫聲清醒過來,他望向湖心那艘款款蕩漾的小船,從上空飛越而過的幾隻白鷺鷥感知,好友已然羽化登仙。他深知道家修道最重「道法自然」,能超越死亡的訣竅就是「齊生死」。生跟死其實一個樣,只是在自然中轉化作不同的存在形式罷了。
他帶著起伏心情執筆〈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在停停寫寫間不斷回顧,張志和實踐「無為」之心,通往成道之路,早已具體釋放在那次曲水流觴,即興風雅作〈漁歌〉的聚會上,聚者,無論自己、陸羽、徐士衡,還是李成矩,其作皆不如張志和貼近屈原〈漁父〉「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精髓,張志和的五詩五「不」,都不被外事外物侷限束縛,盡是順應時勢,從心所欲而行。
顏真卿讚嘆張志和的〈漁歌〉「淈其泥而揚其波」,詩詩相扣,既讓泥水溼身,也和天地混濁在一塊兒,詩裡體現的不須「歸」,是圓滿生命不「憂」、不「窮」、不「寒」的自由,那是老子闡揚「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的怡然自得;也是莊子「至樂無樂,至譽無譽」的清靜無為,足與「仙」齊又何須羨仙!
現正最夯:WBC美國隊史上最大爆冷輸義大利!與台灣一起上數學課 墨義戰控分就能把美淘汰
【詩詞新譯】
細究張志和快意暢寫的〈漁歌〉組詩,在抒情寫景之外,富含著「以人為始」的深層「道意」,五首詩皆以「道」為本,從「現象」中論「道」,依附《道德經》基礎,藉由遠離世俗紛爭的不同時代人物,點出一系列逍遙於江湖的隱士典範。最耀眼手法,莫過呈現作品「靜動」、「有無」、「體用」的內核效驗,尤其跳脫唐一代詩作百年俗成的格律、音韻章法,將「七絕」幻化成「詞」,裂解第三句作三三句式,形成不同音律變化的七七三三七字五句排列的單調歌詞。詩人未曾料想,他隨興唱和道友的一組詩風,竟演變為後世文學歸類上的五闋詞作。
〈漁歌〉其一
范蠡 /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德經》第九章
范蠡師承老子門下玄元十子之一的計然(辛文子),習得計然所精通的戰略與經濟思想本領,助越王句踐復國後毫不眷戀權位,功成身退離開越國,其後,依《吳越春秋》記載,他「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足跡或以傳說,或載入地方志,遍及浙、魯、蘇、鄂、皖等地,尤以太湖南岸湖州轄內縣市鄉鎮(吳興、南潯、長興、德清)為最多。自古相傳范蠡常出沒苕溪,在輕風吹柳綠,細雨點桃紅的暮春時分,最喜泛舟垂釣於水上,經數日才返。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臨水那片淡濛濛深鎖蒼鬱的丘陵前,一群白鷺鷥正輪番飛舞嬉戲著,水岸邊桃林紛落的花瓣兒漂浮在波動的水面上,似化作水下無數肥碩鱖豚爭相大快朵頤的盤盤珍餚。瞧,頭戴笠帽、身披蓑衣的范蠡先生(漁父),已全然忘情溶入這幅春雨微風的景緻裡而不能自拔。
道家思想核心,牽涉萬物生成本原與存在本體,以及人生價值,範疇含括「道」與「現象」兩種層面下所觸及的「有無」、「動靜」和「體用」觀。詞作中,山、花、水流、笠帽、蓑衣盡是肉眼能見的「現象」,仰天上鷺鳥徜徉,俯水下魚兒肥碩,觀風雨中漁父佇足,又焉知鷺鷥因何橫飛?魚群是肥或瘦?漁父思歸不歸?倘若以己心度萬物之心,盡落「執念」則有違「道」心。
山沉「靜」,飛鳥「動」,山不動鳥動,靜動之間存在著矛盾對立的決定意識,意識主導內容決定形式,想在動中之靜的形上思維,做到符合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就須追求動靜相養,戒躁主靜的自然規律。桃花流水清晰「有」可見,難辨水底魚肥瘦,任憑想像俱為「無」之狀態。本句闡明宇宙事物皆由「有」和「無」構成,但兩者同作矛盾對立卻又相輔相成,「有」作為事物存在的條件,惟有與「無」結合,才能發揮應有功能,有和無相資相生,少了「有」就無所謂無,沒有「無」也就無所謂有。看見桃花流水或想像水底魚兒肥瘦,就是從現象發覺道的過程。
斗笠雨披為物,其本質謂之「體」,供人穿戴,動靜間可無畏風雨謂之「用」。在道家「體用觀」流變中,自唐前期經學家崔憬提出「天地圓蓋方軫為體為器,以萬物資始資生為用為道。動物以形軀為體為器,以靈識為用為道。植物以枝幹為器為體,以生性為道為用。」(《周易集解•繫辭》卷十四)之後,「體」形成實際的形質,「用」成為形質所有的作用,雖偏於「唯物」色彩,卻貼切反映出人處在本真自我中的經驗和感受。
一生致力求道的張志和,引范蠡漁隱之道,從「現象」觀察「靜動」、「有無」與「體用」關係,藉此論述「道」的真諦。
千年爭一回
「西塞山」一說在浙江湖州,另一說在湖北黃石。雖然南宋學者王楙早在八百年前已有詳實考證,且在著作《野客叢書》卷二十九裡說得明白,「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按《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溪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因作品在文學史上握有「詩」轉折為「詞」的重要脈絡,迄今,地點依然維持各有擁護的爭議性。
「鱖魚」又稱桂魚。「箬笠」即斗笠,是用竹葉或竹篾編製而成的寬邊帽子,可遮雨防曬。「蓑衣」係用草或棕編製的雨衣。「斜風」微風。「不須」不一定要。「歸」本指返回,此處抑指回朝堂。
宋代以來,研究者將〈漁歌〉焦點集中在「其一」的地點之爭,依史料所載,作品是張志和受邀於顏真卿湖州刺史任上一次聚會的即興之作,那麼,席間完成的五首作品,內容又觸及五個不同時空修道角色,理當是腹中有墨或腦內「印象」盤整之作。若非聚會之作,就有可能是在不同時間創作的作品,若真如此,待考證處勢必再添膠著。不可否認,作品描述地點對還原歷史現場極其重要,但因此失焦創作本意,抑辜負了原創核心?過於執著地點而忽略作家傳達的內核精神便顯顧此失彼,對受教的讀者更是一種損失。所以應該回歸作品的中心思想。
羽化非失足
開啟黃老之術質變為道教教義而成書於六朝以前的《老子想爾注》,把初始道教領入深層探索,視死後復生思想為一種獨特的神仙方術,藉此追求靈魂、肉體不死境界,其中《道德經》通行本第七章闡述的「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句裡「私」字,被擴及解釋為「屍」字,引注者(道教創始者張道陵或其孫兒張魯)直接更改句義為「以其無屍,故能成其屍。」自此,儒、道、釋等諸種信仰本已糾纏的龐雜體系,又添一條修道人以「自殺」求仙的路徑且影響甚鉅。六朝起,無懼自沉、火焚、兵殺、煉丹吞丹、服屍解藥的風氣,便成修仙者盲目求取永生的方式。
張志和因酒後置席水上表演助興,不慎落水而死,多見於持中立研究的文獻中,不過,從他散佚的主要著述名稱《玄真子》及《大易》可顯端倪,兩部作品必是他狂熱修道結晶,再對照《續仙傳》卷上「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運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這段敘述仔細推敲,當可明白為何目睹者無人伸手援救的疑惑,因為在場者皆尊重,張志和是以水解儀式淨化生命,完成升仙的目的。
【詩人簡介】
張志和,本名龜齡,字子同,自號煙波釣徒,道號玄真子。唐代東陽金華人。幼年受精曉道家思想父親薰陶而崇奉道流,終成著名道士。十六歲遊太學,後以明經擢第,曾獻策肅宗得賞識,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並賜名「志和」,遂改龜齡為志和。榮寵之際開罪朝堂,遭貶南浦尉,經量移他郡,又遇赦返京,因看破宦海,泯滅仕念,趁親喪辭官歸返本貫。肅宗賜奴、婢各一稱漁童、樵青,偕奴婢隱居於太湖流域,扁舟垂綸,以修道爲宗。大曆九年冬,與顏真卿諸道友遊平望,於鶯脰湖水解成仙。著有《玄真子》十二卷,《大易》十五卷,多散逸,今存詞五首、詩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