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聰明睿智的人,也不知其深度,對勤奮用功的人,也不知其真諦,我的思想在世上找不到接受者,如同海水只能在自己體內老去。----法稱(古印度詩人)
2.
這時候,我不得不佩服嚴向冬的本領,他勇健的腿力自不待言了。而他的眼力同樣不凡。的確,我在國中時期,不埋頭讀書準備高中聯考,卻非常熱衷於鍛鍊體魄,伏地挺身啦、拉伸鋼條擴胸器啦、像折甘蔗似的正反握折彈簧棒啦、舉重啦、投擲標槍啦、推鉛球啦、小腿綁上小沙袋,在村外的溪埔練跑啦等等,所有想得到的方式都做了嚐試。經過這種克難式的自我鍛煉,終於練出成果來了。在營養普遍不良的鄉下,我們班上有三十餘名同學,就以我的胸肌最為發達,最能展現出少年人罕見的光耀。然而,當兵退伍以後,我不得不投入生活中的大洪流,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我在少年時期練就的體格,一點一滴的流失,如山坡的土塊逐漸地崩塌,到現在,只剩下形式猶在的骨架而已。而嚴向冬在這短暫見面中,竟然看出我曾經努力健身的前史了,就這點來說,誰能不佩服他敏銳的洞察力嗎?
現正最夯:鯉魚潭9歲童翻船溺斃掀 傅崐萁怒批中央對花蓮「卸責切割」
我們倆終於並肩走著,這樣就不需為誰先誰後而尷尬了。來到寬闊的街路時,剛好遇上了紅燈。這時候,他指著對面一棟超高大樓,不無感慨地說:「三十餘年前,我搬到這一帶的時候,放眼望去,那裡幾乎都是美麗的水田,四周連一棵高大的樹木也沒有。我兩個孩子都喜歡到那裡玩耍,他們說每次有風吹來,那大片水田便泛起小小的波紋,甚是好看令人感動,回家之後,他們都會興奮地告訴我們夫妻,以聽完他們的敘述,我們也像是身臨其境一樣。」
「您的意思是,與現今相比,那裡已失去當初的景象了嗎?」我好奇地問。
「嗯,原先大片的美麗水田全變了樣,已經被拔地而起的大樓給取代了。雖然,滄海桑田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實,說我老頑固也沒關係,直到現在,我依然不大習慣,也不大接受這種變化。不怕你笑話,除非有什麼急事要辦,否則我根本不到那裡去的。」
全站首選:香港男陳屍北市五星級飯店!遺言盼:結清房費 母現身相驗
「哎呀,想不到您是個懷舊的人。」我開玩笑地說,並話鋒一轉,「我還以為您是反商的激進派,最後恐怕要把那些建商臭罵一頓,才能化解心中的怒火呢。」
「譚社長,您說對了一半。」
「咦?」
「在這些我熟悉的地貌改變之後,我的確有著深深的失落感,恨死了那些吃骨頭不吐渣的壞建商。他們透過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勾結官員),收買大片水田和併購貧戶產權,還惡劣地炒作土地,操縱和抬高房價,讓許多人根本買不起,只好統統退到郊外去。當初,我若不是向銀行貸款,硬著頭皮買下那間四樓公寓的話,早就像蒲公英一樣,隨風飄往哪座公墓了。」
「哈,您真是幽默,」我也打趣地說,「看來,您是把整個時代的重負全壓在自己的肩上了。」
「我才沒那麼偉大呢。不過,它的確是我切身的感受,不怕您取笑就是。」
號誌燈由紅轉綠了,我們不能像兩支懷舊的木樁,一直杵在原地不動。於是,我們再次並肩往前走去,約莫過了五分鐘左右,來到了一條較小的街道,他略顯興奮地對我說,「社長,我們往前直走十公尺左右,然後往右邊小巷拐進去,就快到我的工作室了。」
事實上,我的心情也跟著歡快起來。我抬頭看向天空,豔陽的熱度比剛出站的時候,明顯升高了許多。按照我的理解,它像是要用這熱度來考驗市民們的耐性,也像是在證明在其底下走動的人影,都能達到自由和保全,而不受其毀壞的。我又想,有了這種期待做支撐,那麼在造訪者和受訪者心中的那片樹林,就不致於貿然枯萎了。人之所以對未來抱著希望,大概就是從這個基礎出發的。
快到巷口的左前方,有個店家的門板,貼著奇特的廣告,令人我十分好奇。我猶疑了一下,因為就快抵達目的地了。不過,最後我依然止不住好奇,還是問了嚴向冬,他在當地居住幾十年了,對於周遭的環境和居民的變遷,應該比誰都了解。
「噢,您是指那家國術館嗎?」他恍然大悟地說。
「那裡是國術館?」
「是啊,」他解釋著說,「據說,老闆曾於一九七○年代中期,到過日本打職業摔跤,藝名叫做南國英雄。大約二十年前左右,不知什麼緣故,回到自己的故鄉,開設英雄國術館,做些跌打損傷的治療,兼做整骨和經絡調整。」
我重又看著那張醒目的海報:體格壯碩的南國英雄雙手抱拳與著名摔跤手安東尼.豬木合照,他們二人都露出自信而燦爛的笑容,彷彿所有膽怯的人,接受這微笑的照拂,就能變得勇敢和面對挑戰。這種海報的確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以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激勵每個年輕人將自己鍛煉成肌肉精壯的猛男。
「我記得,開業之初,還有在地的青年到那裡學打拳,但是好景不常,隨著各種武術道館的興起,英雄國術館的生意就漸漸冷清了。」嚴向冬補充說道。
「或許,這就是時代的變化,各行各業起起落落,誰也無法阻擋它。」我忽然想起似地說,「說到日本職業摔跤,那是我小時候愛看的電視節目。當時,在只有三台的時代,每到轉播的時間,我村裡的所有少年們都守在我家的電視機前,提心吊膽地看著黑白電視裡兩個猛男的生死鬥。說起來,它倒不失為一段美好而新奇的回憶。只不過,我四十歲以後,知道職業摔角原來是套招的表演,從此就失去了興趣……」
「套招?」嚴向冬詫異地說,「難道……在擂台上把對手打得頭破血流,逼得對手逃命似地躲進擂台底下,拿出傷人的小鐵棍予以反擊,也是配合演出的嗎?」
「嗯,應該說,這是那個年代最受日本觀眾歡迎的戲碼。」
「問題是,您說這是『表演』出來的,那麼觀眾不就成了受騙的傻瓜嗎?」
「不,一開始,觀眾就明白。他們花錢觀看,是為了消除壓力,獲得些娛樂,這是經過充分訓練的武鬥表演,即使出現流血的場面,亦是依照劇本的安排,不致於要人命。真鬧出人命的話,摔跤選手可要吃官司,被選手家屬控告過失殺人罪。這樣一來,摔跤公司等於失去兩名選手的演出,經營方面一定會更困難。為了長期有效地營運,就需要選手們彼此之間的套招表演了。」
「社長,您對日本職業摔跤研究得這麼透徹,真是讓我長見識了。」嚴向冬接著說,「話說回來,商業性的演出我還能接受,但政治上的『表演』,我絲毫不能苟同。」
「我了解您的意思,做人不能沒有原則。不過,有些情況很複雜,很難用幾句話,就把它說得通透。」
一拐進巷子,嚴向冬立刻對我說,他們家就位於巷子盡頭那棟公寓四樓。我順著他的手勢看去,果真,在樓下入口處,有一扇紅漆斑駁的鐵門敞開著。按理說,這是很尋常的光景,在尚未被地產開發商挖掘翻遍的地方,或多或少還能看見這種時代的殘景。不過,我還看到了另一個奇特的光景,巷子右邊有一道青色的鐵皮圍牆,高度大約兩公尺半,牆內正在整地準備興建大型公寓,不時傳來物體碰撞的響聲;在巷子半途的左側,有一間小型宮廟,前面擺著偌大的香爐,爐內有幾道青煙升騰著;另外,幾名女信徒或義工正忙著炊煮素食菜料,將它們端上簡易的桌子上,看樣子,這天好像是廟會的慶典。
我心想,這光景與我小時候所見的沒有不同,甚至讓我有似曾相識之感,它是一種對相似場景的喚回。不過,這次我不發問了。如果我當場向他探問,一定讓他備感尷尬的,因為我們從大香爐經過的時候,他既沒有主動向宮主,或者類似廟祝的男子打聲招呼,而那幾個女信徒也沒有抬頭正視著他。這些動作也算是一種表明,表示他們彼此保留沉默以對的距離:你拜你的神明,我走我的巷弄,誰都不要干涉對方的自由。一個再尋常不過的現象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度裡,哪怕是有黑道背景的神棍,說他是神尊的化身啦,他通曉神明的語言啦,如何要拯救世間疾苦等狂言,只要有人相信,自願地掏錢捐獻,尤其,在《宗教法》尚未拍板定案之前,他就不構成詐欺的罪嫌。進一步地說,不但不會遭到稅捐機關的強制管收,他們還能一如往常地繼續擴大宮廟的營業規模;又例如,哪怕是為赤魷黨的殘虐行為搖旗吶喊、開著宣傳車噪音擾民的黨徒們,他們的狂熱行為無不受到法律上的保障。與此同時,他們老謀深算,知道人民有信仰和結社的自由,並以此展開行動,換句話說,他們深諳民主制度的脆弱性,比任何人更早地找到法律的漏洞,進而在漏洞中自由進出。(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文化隨筆三部曲《日輪帶我去旅行》、《我的枯山水》、《燃燒的愛情樹》(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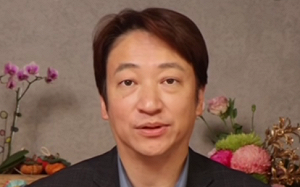





![[影]年假尾聲曬萌犬片!賴清德分享蔡英文帶「樂樂、鳳梨妹」作客官邸](https://images.newtalk.tw/resize_action2/300/album/news/1021/699b1786a6f50.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