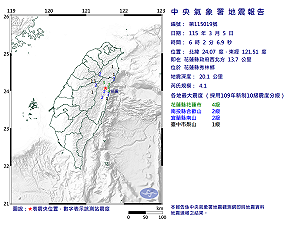許多人死在天安門廣場,也有人永遠活在那裡
「六四」屠殺中,死人最多的城市是北京,其次是成都。然而,三十年後,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的北京和成都,沒有多少人記得那些逝去的生命。「六四」是中國最大的禁忌,中共當局恨不得在日曆上刪去這個特殊的日子。「六四」發生時,還在英國治下的香港沒有死一個人,卻意外地成為一座以「六四」為主題的活的紀念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關於六四的記憶和研究都彙聚到香港。我也遇到過很多香港人將「六四」像種子一樣種植在心中,仿佛「六四」屠殺中死去的孩子是他們親生的孩子。
全站首選:行政院加開穩定物價臨時會報 持續油價雙緩漲機制、關鍵原物料稅負減徵延至9月底
陳潤芝就是其中之一。三十年前,陳潤芝作為亞洲電視記者赴北京天安門採訪學生運動,無意中成為屠殺的見證者。三十年之後,她和前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前無線電視記者謝彩雲、前亞洲電視攝影師勞家輝、前星島晚報記者梁慧珉、前路透攝影記者曾顯華等三十名曾直接採訪「六四」的記者,一起拍攝了一部名為《我是記者》的短片,各自講述「我的六四故事」。片中有記者憶述當年槍聲響起的場景,不禁失聲痛哭。
三十年前,陳潤芝跟一班香港記者在槍林彈雨中逃離北京。不料,去機場的道路被民眾設置的一堆自行車堵塞,司機打開車門二話不說衝出去,把擋在前面的一架自行車抬起,大力扔到老遠。周圍的市民被突然而來的大動作惹怒,像螞蟻圍大象般圍過來,將車隊團團堵死。遠處就是十幾輛坦克,戒嚴令下,槍彈掃射過來是絶對有可能的。一位男同事急中生智,立即衝下車,舉起記者證說:「我們是香港記者,趕着送新聞。」奇跡出現了,群眾像摩西過紅海般向兩邊挪開:「讓開,讓開,讓香港記者走,讓香港記者走。」就這樣,他們渡過紅海,直奔機場。三十年後,這驚心動魄的一幕仍然歷歷在目。
當陳潤芝發電郵給我,告知她要爲撰寫一本紀念六四屠殺三十週年的書採訪我時,我也收到她十年前寫的書《六四二0》。這是六四屠殺二十週年時,她自費赴美國採訪寫成的一本訪談錄,她與書中的六四參與者和流亡者一起哀哭切齒,讓我想起另一位也是被六四改變一生軌跡的香港女記者蔡淑芳。
現正最夯:首批滯留中東我國旅客275人返台!民眾盼儘早了解有無返國機位
六四流亡者蘇曉康在爲蔡淑芳的回憶錄《廣場活碑》所寫的序言中評論説:「她茫然若失在四點鐘的廣場上,以後便一次次地驚叫、哭醒在香港的深夜裡。……她化為每年六四維園燭海裡的一點燭淚。她陪整個民族受難。」六四屠殺之後鋪天蓋地的遺忘和謊言,讓説真話的記者成為「時代的敵人」或「不合時宜的人」,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綁架中國,精英整體投降,西方輸誠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許只是杯水車薪。但六四把她淬礪成一個‘革命者’——她已經忘我,她不再是一個私人的蔡淑芳。俗話說,時間改變一切;不屈不撓地跟歲月搏鬥,乃是她的回應。她把自己變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是的,蔡淑芳、陳潤芝以及每一個作為見證者和記憶者的香港記者,在精神上從未離開過天安門廣場,一直站立在那裡記錄廢墟中的真相。
我懷著敬意接受了陳潤芝的採訪,在華府郊區的刺骨的寒風中,她穿著兒子的一件「加拿大鵝」牌的羽絨服如期而至。我們差不多談了一整天。幾個月後,陳潤芝採訪王丹、張伯笠、王超華、蘇曉康、滕彪和我的訪談錄《六四三0》出版問世了。
三十年無祭,但三十年不能沒有反思
陳潤芝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三十年過去,記憶如斯清晰,就是因為生命確曾有一刻懸於一線!經歷過八九民運,流亡海外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創傷:跟父母分離、家庭破碎、家人遭嚴重車禍致殘。心靈上,他們多年來經歷不同階段的反省。」今天,中共的統治依舊蠻橫暴虐,蔣彥永醫生呼籲的六四正名依然是水月鏡花,蔣醫生本人再度因此失去自由。天安門母親不能去親人死難的現場和墓地悼念,中共為了監控天安門母親之一的張先玲,居然在她兒子遇難的學校門口安裝一台攝像頭,這是專屬於張先玲的攝像頭。儘管三十年無祭,但三十年之後,六四的參與者們不能沒有個體化的反思。然而,很多六四參與者確實沒有反思,他們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那樣重複地控訴共產黨的兇惡,以及渲染自身的悲情或勇敢,誰有耐心傾聽呢?
深切的反思,乃是為下一次民主運動所做的最好準備。陳潤芝在採訪多名當事人時,都會提出此一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有沒有覺得當初某些事情做錯了?先後兩次下獄的王丹認為,絶食這一步行得太早,亦沒想到參加的學生這麼多。他以「三分功,七分過」評價自己在學運中表現,對未能堅決促成學生撤退,感到十分後悔,他説:「最後導致運動的失敗,和同學的傷亡,我因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第二次坐牢、我至今不放棄,在我看來,都是為了彌補自己的過錯,為了承擔這個責任。」
張伯笠承認自己存在激進情緒,導致決策失誤,他如是説:「作為一個決策者不僅要考慮到良好的動機和理想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考慮到所利用的手段。而我們的腦海裏殘存着為了目的的美好和純潔不惜用鮮血和生命去換取這樣理念。」
王超華在八九那一年已三十七歲,是社科院的研究生,是學生領袖中最年長的,曾試圖力挽狂瀾,哭求知名學者一起勸學生停止絶食,撤離廣場不果,與柴玲等人多次交鋒。三十年來,她始終堅持這樣的看法:「學生有錯,政府有罪。」眾所周知,決定開槍,權在政府,而非手無寸鐵的學生。
八九時已經四十歲的蘇曉康,經歷過文革,父親是中共高官,二十六歲開始做記者,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深知中共政權專制本質。胡耀邦一死,他就立定與運動保持距離。戒嚴令一出,他立即躱起來,展開百日逃亡。三十年後,他反而後悔沒更早介入,像劉曉波一樣,以行動取信於學生,說服他們及早撤出廣場。
在從事政治活動時,政治人物尤其是領袖最重要的品質乃是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説的「責任倫理」。韋伯提出「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這種二分法,以便疏解政治活動家的困境。他認為,信念倫理是一股一往無前的勇氣所驅使的道德感,但政治家不能單憑信念,只能腳踏實地地衡量一切行動所帶來的各種後果,於是他所能秉持的,只能是「責任倫理」。換言之,既要有「熱情」,也要有「責任感」和「判斷力」。
韋伯進一步論述説,「熱情是獻身於一項事業,不成功,便成仁」,而「責任就是在將政治當作一項志業時,重要的行動指南」,「判斷力就是沉靜地面對現實的能力,也就是對事對人的距離」。韋伯批判完全由熱情驅動的「信念倫理」,人們自以為是在追求「善」這個目的,但「在許多情形下,‘善’的目的與人們對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險的手段以及產生惡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幾率的容忍分不開」。類似的反省,從劉曉波九十年初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開始,在本書中若干受訪者的敘述中,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共識」。
君子和而不同:中國民主還是中國解體?
六四是一場「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運動。所謂「先天不足」,是指運動之前的思想準備工作不足,儘管八十年代的中國經歷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但基本上只是囫圇吞棗式地翻譯和傳播西方兩百年來的各種現代思想文化,遠遠談不到創造性地「本土轉化」的地步。就連精英知識分子階層都缺乏核心思想和核心觀念,又怎麽可能要求年輕學生具備深刻的思想批判力呢?
所謂「後天失調」,是指運動過程中,以方勵之為代表的知識精英、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體制內改革派以及廣場上的學生領袖這三者之間沒有基本的聯繫和協調,難以形成一種主導運動發展的合力,反倒各行其是,甚至彼此紛爭和內耗,使得以鄧小平為首的頑固派輕而易舉地各個擊破、穩操勝券。
在六四運動中,無論是知識精英、體制內改革派還是一線的學生領袖,都未能為未來中國提出吸引人心的願景,他們只是停滯在「反腐敗、反官倒」這樣一種低級的訴求以及「民主中國」這一模糊的目標上。五四時代空泛的「民主」和「科學」的概念被拿過來使用,甚至國際歌、中國對越戰爭時期的軍方歌曲「血染的風采」也成為學生的文化資源。
那麽,三十年後的今天,受訪者們又有怎樣的新思維呢?陳潤芝是香港人,她眼睜睜地看著九七之後香港淪陷,迎來「再殖民」的厄運。因此,她特別詢問受訪者如何看待香港近年來失敗的民主抗爭,以及香港與中國之關係。
受訪者的看法各不相同。王丹認為,香港、台灣與中國是「命運共同體」,對於港獨倡議,他堅決反對,認為是「完全情緒化的反應」,但「要包容年輕人相對激進的思想」。張伯笠不曾談及統獨問題,對香港的未來相當悲觀,但又認為台灣的民主模式能給予中國參照作用。王超華也不曾談及統獨問題,她流亡美國之後,多次以學者身份到訪香港,但在二零一一年被拒入境,她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灣是反面示範作用。蘇曉康對民運策略以至香港及台灣獨立問題,採取務實態度,「這兩個地方的獨立,在政治上都是他們的權利,現實的問題是你獨立得了嗎?」滕彪則認為,香港「雨傘運動之後加速了本土意識,港獨獨力量興起,要求本土化的聲音越來越強,這是完全應該支持的,這是身份認同問題」,「香港獨立在可見的未來是實現不了的。但是主張獨立的人有權利講,是香港人的選擇和權利」。最後,我的觀點是支持香港、台灣以及更多地方的獨立運動,以解構中國為目標,只要中國是大一統的格局,表面上的民主是毫無意義的。
有意思的是,從本書中的第一個訪談對象王丹到最後一個訪談對象我本人,對於港獨、台獨和其他「獨」的立場,正好呈現出從反對、默許到支持的這種逐漸變化的「階梯」。這肯定不是作者有意識的安排,也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自有其內在邏輯。受訪者之間確實存在著思想觀念的重大差異與分歧。我是獨立價值最堅定和熱切的倡導者,我認為六四未能形成解構邪惡中國的思想積澱,是六四最大的失敗。六四本應當成為獨立思想的酵母,但六四屠殺之後中國轉向傳統文化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知識人也固守反共不反中或反共不反華的定見。
在我看來,獨派才是真正的熱愛自由的人群。從價值上而言,獨立不僅是消極意義上的個人權利,更是積極意義上對上帝所賦予人的自由的實踐,正如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義無反顧地支持與讚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訴求,不惜被國人駡作叛國者。其次,從現實而言,不能因為香港等地暫時無法實現獨立,就否定未來在某一歷史契機實現獨立的可能性。在蘇聯解體之前,在其鐵桶一般的統治下,誰能相信波羅的海三國和中亞若干穆斯林加盟共和國能夠迅速走向獨立呢?我們不能守株待兔般等待那個歷史時刻到來,我們可以從現在就從事解構大一統思想觀念的工作。大一統的中國不可能實現民主化,唯有解構中國成為「諸夏」,人民才能得自由。
寫作六四,是為了制止還在繼續的殺戮
陳潤芝剛剛從電視臺退休,還沒有來得及享受退休生活的安逸與寧靜,就匆匆背包上路,遠赴美國開始新書《六四三0》的採訪和寫作。她如此執著於採訪和寫作六四題材,并將這個「吃力不討好」、「自由投入而幾乎無回報」的工作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僅僅因為她是六四親歷者,對此有切膚之痛;更因為她意識到,六四並不是一頁已經翻過去的歷史,如果使用歷史學家唐德剛的比喻,中國以及世界都未走出六四這段驚濤駭浪的「三峽」。也就是説,六四不是過去時,六四是現在進行時,今天中國社會的全面沉淪,離不開六四屠殺帶來的精神震盪,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六四屠殺的負面遺產中。
在中共統治中國的七十年中,六四不是中共所做過的最為惡劣的事情,中共發動的造成人員傷亡更多的政治運動數不勝數。如果要描繪一張中共政權的殺人年表,一九八九肯定不是醒目的最高峰。但是,跟將數千萬饑腸轆轆的農民拘押在家中、不准外出逃荒以至於餓死和人相食來,六四是在全世界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野戰軍屠殺本國民眾,其震撼力唯有納粹大屠殺可相提並論。
陳潤芝在序言中強調説:「六四屠殺只是極權殘暴的最惡劣展示,之後一直以不同方式展示其專橫,從沒停止。」中共發現開槍殺人是維持政權的最佳方式,從此再無底線和顧忌。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共在新疆建立關押數百萬維吾爾人的集中營,其背後的權力邏輯就是六四鎮壓的延伸。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刊登了英國倫敦學院大學政治系教授、專攻人權與大規模暴行(mass atrocities)犯罪研究的克洛寧福曼(Kate Cronin-Furman)的文章,作者認為,中共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迫害雖然還不到「種族滅絕」,但已構成《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中的「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亦即「有組織」(systematic)及「廣泛地」(widespread)對平民謀殺、強迫失蹤、性侵、強迫遷徙、虐待或基於種族、政治、民族、文化、宗教、性別等的迫害。維吾爾族人更指控,中共政府對他們進行「文化滅絕」(Cultural genocide),包括強迫兒童離開原生家庭,禁止使用母語,禁止舉辦文化活動,並摧毀學校、宗教場所等。或許可以説,沒有昔日的六四就沒有今天新疆的集中營。在發生過六四屠殺的中國,沒有人是安全的。
這就是本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寫作六四,乃至為了制止正在發生的暴行,乃是為了顛覆作惡多端的暴政。這是一項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其中。中共掌握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警察等暴力機器,但正如聖經所説,那殺死身體不能殺死靈魂的,你不要怕它,作為基督徒的陳潤芝和同樣作為基督徒的我,秉持相同的信念,在同一個廣袤的戰場上奮戰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