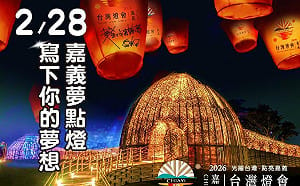依自由時報11月18日A2版「國家檔案館啟用 賴:實踐轉型正義 成就更好的台灣」報導指出,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將於十一月廿二日開館,總統賴清德昨主持開幕典禮致詞表示,國家檔案館除了展現政府保護國家紀錄、保存國人記憶的決心,也展現政府落實政治檔案開放的堅定態度,更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實踐,盼國家檔案館的成立,能夠成就更好的台灣。
賴清德強調,國家檔案館負責徵集典藏各級政府重要檔案、民間私人團體的珍貴文書以及國外典藏的台灣相關檔案,這些檔案是全民共同記憶,也是民主的重要基石。在管理與運用檔案上,國家檔案館應以「最大開放、最小限制」為原則,公開運用檔案,唯有國家把檔案公開給人民,讓國家行為接受人民檢視,才能實現開放政府與資訊公開透明的目標。
查陳昭如教授2020年9月28日在「大法官與轉型正義:從九份解釋談起」研討會發表「檔案的能與不能」一文指出,台灣過去的大法官會議不僅通常欠缺公開的審理程序,許多相關文件也不公開。在這種過程資訊近乎缺無的情況下,就不難理解為何人們會特別希望取得會議紀錄來了解其內部過程,尤其是為了轉型正義的目的而希望藉此了解大法官的角色。追求轉型正義是否能作為公開內部會議紀錄的理由?要評斷大法官是否為威權體制的運作與合理化提供「法律扶助」,是否必須仰賴內部會議紀錄,或者由大法官行使權力做成的解釋就可資論斷?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該文為陳教授對司法院釋字第二六一和第二七二號解釋檔案分析報告所作之回應。這兩號解釋在台灣憲政人權史上得到的評價迴然相異。釋字第二六一號被認為是敲下了萬年國會的喪鐘,但釋字第二七二號則認為是對解嚴後救濟戒嚴時期司法人權的侵犯設下防火牆。
目前大法官會議解釋已走入歷史,憲法訴訟法於民國111年1月4日起施行,目前演進為憲法法庭審判,不過人們仍然想從大法官釋憲檔案中尋找威權體制運作嚴重侵害人權的線索,尤其是對於威權時期的大法官解釋,人們希望可以如同在政治檔案中看到軍法審判的判決書上蔣中正大筆一揮的紅字批示,找到「冒煙的槍」(smoking gun,亦即鐵證)。
依2014年11月出版,蘇瑞鏘著《白色恐怖在台灣》第343頁刊載,徐會之中將原來處5年有期徒刑,蔣中正紅字批示「應即槍決可也」。不過,我們似乎在這批大法官檔案中(按即釋字第二六一號及第二七二號解釋)找不到「冒煙的槍」。
平心而論,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家,有關政治檔案(包括大法官解釋)的開放是歷史真相的基礎,這有助於對轉型正義的實踐,我們期盼國家檔案館本著「最大開放、最小限制」為原則,發揮最有效的功能,來加強鞏固台灣民主。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