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南某科大發生師生爭議。某助理教授因不滿學生遲到,關門、拉窗簾,並口出「卑劣的東西」辱罵學生,數名學生被拒於課堂之外,甚至揚言若無公開道歉與補償,將提告捍衛受教權。事件曝光後,輿論多數支持老師,認為學生不知好歹,網路留言更以「應給遲到的人教訓」為主調。然而,這起事件並不應只是單純的「遲到問題」,更該是一場關於教育制度、師生倫理與人格尊嚴的深層討論。
首先,學生遲到確實不足取。課堂是一個公共場域,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學習,也是對其他學生與教師的尊重。若是人人遲到,秩序崩壞,整體教學品質將受影響。正因如此,學校與教師有責任在學期初訂立明確規範,告訴學生遲到的後果:扣分、記錄或補交作業。制度化規則可減少日後爭議,也能避免老師臨場情緒失控。
然而,老師以羞辱方式維護紀律,無論如何都不可接受。拒絕學生進入教室聽課,甚至口出侮辱言語,則是已超越管教範疇,侵害人格尊嚴。換言之,教育不應以羞辱為手段,否則不但破壞師生信任,也背離高等教育追求的理性與專業。
當前大學的師生關係已不同於傳統師道尊嚴的模式。隨著個人主體性與公民意識的抬頭,師生關係更像定型契約:學生繳納學費獲取知識,老師提供專業教學並領取薪資。權威應建立在專業與尊重上,而非特權與羞辱。尊師重道必須基於平等互敬,而非單向壓制。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換成老師遲到,學生是否也能「鎖門、罵老師卑劣」?答案很顯然是不行。那麼,當規則未制度化、僅靠情緒維護時,師生關係容易淪為權力不對等。因此,唯有透過清楚規範與正當程序,才能避免衝突升級為對立。
借鏡於國際經驗,許多高教體系已建立成熟制度。美國大學通常在教學大綱(syllabus)明訂出缺席、遲到規則,學生開學即知悉,爭議可透過申訴程序提出。日本大學強調自律與責任,老師通常不在課堂羞辱學生,而以成績反映缺席的後果。歐洲部分大學甚至將出席與否完全交給學生自主,教師只提供完整課程的教授。綜觀而言,核心理念一致:師生是契約關係,而非父權式壓制,權威來自專業與人格,而非情緒與怒罵。
對照台灣現況,問題不在於遲到該不該懲罰,而在缺乏制度化的公平規範。當制度缺席,師生衝突容易升級為情緒對立,甚至成為社會輿論的謾罵。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培養理性對話、懂得尊重的人。學生遲到應承擔後果,但老師以羞辱方式處理,傳遞給學生的卻是錯誤示範:權力凌駕於尊嚴之上。
因此,這場爭議不應簡化為「遲到對或錯」,而該是「如何在彼此尊重下維護公平正義」的教育省思。遲到不應該,羞辱人更不應該。唯有在制度化與尊重並行的完整框架下,教育才能真正培養負責任、懂得尊重的公民。
最後,要再提醒的是,教育從來不只是管規矩,更是教會每個人如何在規矩中守護人性與尊嚴,並發展自我而能公益利他。老師與學生,都應如此。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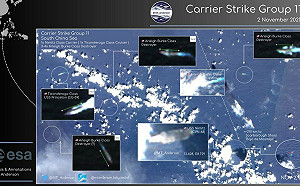

![11/29-11/30 [流量政治學第二屆營隊] 免費報名參加](https://images.newtalk.tw/resize_action2/300/album/project/1/69033cad7782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