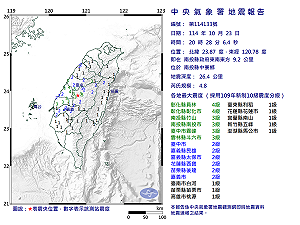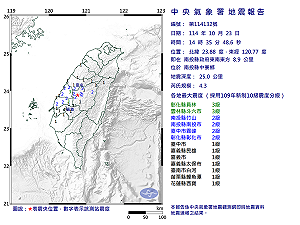既來之,則安之。身在非洲的土地上,我的心情好像穩定多了,也不再像在美國時的那樣急躁。心想我們可以好好利用這兩個星期的機會,來熟習肯亞的環境。
有這樣的想法,我們就開始安排我們的日程。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跳上了往城中心的私人轎車叫Matatu。車資只合美金6分錢。在英國殖民下所建設的奈羅比市可以說是當時非洲最風光 的大城市之一。 市容及建築物十分別緻,街道兩旁綠葉成蔭,店家比比皆是。肯亞又是東非野生動物國家公園最多的地方;奈羅比外圍就是野生國家公園,因此觀光事業發達。城裡的希爾頓旅館是遊客及活動聚集的地方。我們在旅館四周圍散步,很難相信 身處非洲。我們特別到了販賣當地的蔬菜水果等的傳統市場Westlands Market閒逛,學習到了很多新奇的蔬果。穿梭在人群中,感受到現實生命的躍動。
第一個星期日,我們經推薦到奈羅比浸信教堂做禮拜。 信眾大都是英國白人。 第一次在非洲白人的保守教會聽道,我聽到一些讓我不安的聖經章節的詮釋。當我出來時,我開玩地向太太說,「我們來非洲不是來聽道,而是來行道的。」 我們第一次經驗到,做禮拜進出教堂,竟然沒有人與我們打招呼。可見這個教堂信眾的態度。
Sam Yoder教授有兩位女兒,Phyllis和ElaineYoder都嫁給醫師。Phyllis 和夫婿曾在越戰期間到南越服務,並收養了兩個孤兒。我在招待所時得知Elaine,夫婿Roger Unzicker及兩個幼子全家正在Tanzania(坦桑尼亞) Moshi鎮,等待到Lake Victoria (維多利亞湖)東岸的Musoma小村莊服務。 Sam教授過世後,遺孀Ethel Yoder 也跟他們一起來到坦桑尼亞。 他們很高興知道我們在奈羅比等著,歡迎我們去找他們。
剛好Hershey主任也要到Moshi探望他們, 歡迎我們一起搭他的車前往。Moshi 是在坦桑尼亞東北端(在非洲最高山吉力馬札羅山(Mount Kilimanjaro)的山麓),從肯亞越境至坦桑尼亞,我又碰到簽證的問題。 當時東非聯邦剛解散,但肯亞移民局還負責坦桑尼亞及烏干達的簽證事宜。 首先,我必須到「再入境」窗口,填了表後,馬上就得到肯亞再入境證明。 當他們把我的護照移到坦桑尼亞入境簽證的窗口時,我看到辦事員在抽屜中找來找去,抬起頭來問了一下隔壁的辦事員後告訴我,「你的護照必須送去坦桑尼亞外交部批准才可發給你。」 「送坦桑尼亞批准!」我大叫一聲,「要多久啊!」「兩到三個月,」他說。
辦簽證時,我心裡就毛毛的,因為坦桑尼亞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國正在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Zambia)蓋一條坦贊鐵路(TanZam Railrosd),因此被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奉為宗主國。 我的心情壞極了,拿了中華民國護照,來到非洲還要受這種窩囊氣,太沒有尊嚴了。 經過我 一再地央求,並把太太搬出來,讓我們一起成行,終於打動了辦事員的慈悲心,他拿著護照到裡面去問上司,出來時給了我一些希望,要我下午再來一次。 我在兩點上班時就準時來排隊。等到我時,他看著我說,「有兩個中國,坦桑尼亞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你是來自那個中國? Socialist?」我轉頭避開他的眼神,嘴巴跟著咕噥一番,「soso...cialist」, 不斷的點頭。 他又回到裡面向上司報告, 十分鐘後,奇蹟似地,他把護照交給我,「多次的,」他還說。 我轉過頭向他說,「肯亞政府的不結盟政策(non-alignment policy)太棒了!」我感謝他後,拔腿就走!
Moshi 離奈羅比南方約100公里處。由於是兩國邊界的大鎮,又在非洲最高山吉力馬札羅山的山麓,遊客很多。我們往南經過的地方,都是一片紅土矮叢,車子一過,灰土濛濛。附近的Massai族(馬賽族)都集中在Moshi 的附近吸引觀光客,我們急著到Unzicker家,雖對馬賽人十分好奇,可惜也沒有機會多停留瞭解。
我們至少兩年沒有看到Roger 和Elaine Unzicker了,也很高興看到Ethel Yoder來到非洲。在哥森時,我可以說是他們的一家人,能一起在非洲團聚,反映了我們對生命超越國界、超越文化的共同態度。 所以我看到他們倍感溫馨。 Roger 是一位很有愛心的醫師,志願與太太Elaine帶了兩個稚齡的孩子,來到維多利亞湖東岸偏僻荒野的內陸行醫,令我欽佩感動。在我離開非洲前,我和太太帶著兩歲多的兒子林西濤,專程跑到偏遠的Musoma向他們說再見。 途中發生了一件神秘又奇蹟的故事,改變了我的生命,深深領悟到生命的謙卑和奧秘。這個故事容後再慢慢道來。 1974年Roger一家離開非洲後,住在哥森,默默行善。但不幸,二十多年前,Roger在一次割除腦瘤的手術時,缺氧過世。 Sam Yoder 一家人,都自然流露出的無私、勇敢的大愛,對我影響很大。至今,我努力謙卑,學習是非,拒絕自私,厭惡貪婪,都是他們留給我的資產。
對我學生態的人而言,非洲是生態的聖地。Roger也對非洲野生動物及生態景觀非常熱衷。 第二天他就載著我們到附近Arusha國家公園去看Ngurdoto 火山口。 Ngurdoto 火山口直徑最寬3.6公里,深100公尺,火山底部是一片濕地,四周都被森林包圍著。 出奇綠油油的四周,往下看如同綠野仙洞一樣。看完後,我感到非常慶幸,來到非洲才一個星期,就看到如此難以相信的生態奇景。
回到奈羅比第二天,Roger突然電告說他要去Ngorongoro Crater(N. 火山口),問我想不想去。 哇,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怎能不去呢。印大時,生態課裡,Ngorongoro Crater 一再地被提起,是世界最令人嘆為觀止的野生動物及生態體系奇景之一。雖然路途十分遙遠,但我們毫不遲疑,和太太馬上就動身,好像恐怕以後再也看不到似的。 首先,我們要從奈羅比搭公車至Moshi,再往西到Arusha後,與Roger會合,再驅車到Ngrongoro Crater。
這是我們第一次搭公車到坦桑尼亞,車況像台灣五零年代的巴士一樣,路況是坑坑洞洞。 一路下來,只有我們三、四個乘客,偶而會有幾個人上上下下。在快到Moshi前,上來了一個Massai的年輕女孩子,穿著馬賽傳統的赭紅長衫、耳環。她坐下到我們的前座,不斷轉身看著我們。 不久她轉過身來,看了一回,開始從我的頭髮到臉上,輕柔地觸摸著,然後轉向我的太太,也一樣從她的頭髮到臉上,輕柔地觸摸著。 我們不動地看著她好奇且露出驚喜的美麗表情,彼此對著微笑。看著她真誠、驚奇的眼神,流露出一股自然的神色,實在太美了!當時我口裡含著口香糖,從袋子裡掏出一包給她。現在我真感到後悔。我應該站起來清柔地擁抱她。
Moshi附近是Massai族的傳統牧游的地區,一路也可看到Massai族人趕著牛群。馬賽族是東非一個非常獨特迷人的族群,其文化傳統也非常古老。 女人的頸上掛滿成串的串珠,手臂也掛滿圈環,耳珠的大耳環,十分賞心悅目;男人身材高而修長,穿著赭紅長衫,右腳翹在左腳跟後,以右手握著長矛支撐著身體,站在無際大草原中,遠遠對著陽光的輪廓,難得一見的美景。
到了Roger家時,前後已五個多小時了。這一趟真是不虛此行。我們在Roger家待了一個星期,一共去了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和Lake Manyera國家公園,三個連在一起,但有不同的野生動物及生態多樣性的國家公園。當時,這些國家公園的管理不是很嚴格的,我們可以直接駕車到處漫遊。一般人很難想像,Serengei 地區內一百五十萬頭的牛羚(Wildebeests),二十萬的斑馬(Zebras)及三十五萬的瞪羚(Gazelles)跨越1200英里非洲土地大遷徙的雄偉、壯闊景觀。如今,在「發現」電視台(Discovery Channel) 看到大遷徙的景觀就已令人嘆為觀止;一旦置身在那廣闊無際的大草原中,令人驚心動魄,其震撼感受,難以描述。瞭望這些非洲野生動物的原始棲息地,人類演化的搖籃(Olduvai Gorge),我心中充滿激動、謙卑、感恩。
我想到,達爾文22歲時即冒險隨「獵犬號」(Beagle)航遊世界五年,收集、觀察各地動植物生物變遷。在Galápagos Islands島上的觀察給他解釋生物演化機制「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啟示,可惜獵犬號沒有停留在東非,否則,達爾文會更早洞悉到「自然選擇」的機制。
我想到,莎士比亞說,「自然就是我的書」(Nature is my book)。 科技越發達,自然宇宙更奧秘,未知越多,人類的無知愈多。 我所知的生態知識,已微乎其微,只是滄海一粟,只能謙卑地敬畏自然,驚嘆其奧秘。
我想到,David Attenoborough畢生以相機拍攝自然的奧秘,令人驚嘆,呼籲人們敬畏自然。 今年86歲高齡的他,憂心地球未來之餘,感嘆地說, ”We are a plague on the Earth.”「人類是地球的瘟疫」。人類以現在破壞自然的速率下去,誠非虛言。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