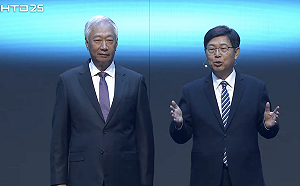美國1960年代,對我而言,是一個豐富,撼動人心的十年。 我有幸恭逢其盛。
1963年,給美國帶來希望的甘乃迪總統遇刺身亡;1968年3月,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及甘乃迪的弟弟羅伯特‧甘乃迪相繼被槍殺。 爭民權、反越戰聲浪此起彼落,如野火般在美國各地延燒。 繼承甘乃迪總統的約翰•強森總統甚至迫於排山倒海而來的反越戰的示威活動,宣布放棄尋求總統連任。
二次大戰後,美國充滿希望的年代就在如此令人沮喪的事件一一衝擊下,敲醒無慮安逸生活的睡夢,年輕學生及30歲上下的美國人開始覺醒,質疑上一代的價值觀,無法解決當下政治社會的現實,終於站出來群起抗議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問題。他們要求結束對黑人不公不義的待遇、結束兩敗俱傷的越戰、解放婦女,提倡兩性平權。 他們關心環境生態的問題,展開環保生態運動,要求立法保護;他們關懷少數族裔的的人權,並鼓勵少數族裔爭取文化權利的自覺。
不滿、思變的心態,年輕人以反傳統的行為表達。1967年在舊金山,有兩萬人參加了嬉皮集會。1969年,50萬年輕人湧入了The 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 (現通稱為 Woodstock Festival) 放縱自己,展現自我,追求不受拘束的自由。他們開始反抗,留著長髮,穿著奇裝異服,並透過音樂來盡情表達對生命、社會的不滿。
1967年夏天,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我來到印大。 經過一段助教教學的經驗,修習課程的考驗,及與同學交往的認識,我逐漸對自己建立了信心。 我自忖,如果好好地用功的話,博士學位的獲得,並非難事,指日可待。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政治社會的巨變,各種運動如火如荼的掃遍了全國的校園。 我發現自己也無法置身度外。我毫不諱言, 基於相同的價值與理念,我很興奮地捲入了這場風暴。 我當然支持黑人民權、環保生態,及反越戰運動。 在台灣,228的殺戮、白色恐怖,我的家族就有受害者;台灣人的文化語言、人權、就業、福利等不是遭受類似歧視嗎? 我學的是生態學,還有不參與保護環境生態的理由嗎? 受哥森學院的薰陶,能不反對戰爭嗎? 各種活動中,我參與最多的是環境生態保護運動和反越戰運動。 校園內主辦的反越戰集會,代表亞洲的聲音很多次是由我負責上台。 1970年4月20日第一次世界地球日的宣告,達到了運動的高潮。 印大校園舉辦的地球日,就是由我們生態研究生負責舉辦的。 1965年到1969年間,哥森學院的教育,印大生態學的薰陶,及社會運動的熱烈參與,把我從一個只知追求博士學位的書呆子變成一個積極實踐的行動者。
60年代,政治、社會及文化的變動不僅發生在美國,社會主義左派的思潮也席捲西歐各國。1968年,在東方,毛澤東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這反思的風潮下,我們一些台灣留學生,組織讀書會,研討分析美國政治社會的各種運動的本質,咸認這些運動不僅是政治、社會,也是文化的反省運動,並質疑資本主義下的文化本質、經濟發展的目的、進步的意義等。平時,我們一起研讀討論各種社會主義的書籍(如Paul Sweezy的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也關切第三世界被西方國家剝削的問題,並以台灣為例。讀書會的成員中,我最佩服的一位朋友是葉新雲。 他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的高材生,受當時馮滬祥台大哲學系政治事件之害,也出國唸書, 來到印大讀哲學。 每次他在讀書會中的報告條理清晰,說服力強,令人印象深刻。在芝加哥大學的林孝信也是當時受人尊敬的一位運動者。
這些運動的參與讓我認知到關懷社會正義公平的必要性,走出象牙塔的正當性,訓練我學習到忠於自我、勇於表達理念的自信心,更進一步深化了我對民主政治的信仰。 我很幸運地在美國各種社會、環保、民權及反越戰運動的熾烈發展時期恭逢其盛,此影響了我回台後,對台灣各種政治社會的不公不義的反感,並埋下了我積極參與改革的決心。特別在生態環保的議題上,我投入了我二十年的艱辛歲月,也改變了我的生命。
這段時間,我個人的生命也像美國的社會產生了重大的變動。我結婚了!
1968年夏天,Kathleen Yoder 從哥森學院畢業後在Bloomington醫院找到了一份護理的工作,我們又開始來往。到了1969的春天,我們彼此存著一種淡淡的情愛,週末相聚彼此都感受到情投意合的喜悅。 有一長假,我們一起回到她賓州的家鄉,探望獨居的母親。 從高速公路下來,一路上經過都是遼闊的農場,景觀之美,令我稱奇。 他家的小鎮Allensville,處在俗稱大谷(Kishacoquillas Valley)半山腰上。 老母親獨居在一間古老的兩樓房子,被十幾公頃的果園林地包圍著,整個環境如入仙境。 她所吃的食物都是來自果樹菜園,山上流下來的溪水直入家中水管,可以隨時安全飲用。Kathleen 就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全在自然的擁抱滋潤中成長。在回途的路上,我告訴她,看到她成長的環境讓我想起美國詩人 Walter Whitman 的一首詩,”Now I see the secret of making the best person: it is to grow in the open air, and eat and sleep with the earth.” (現在我知道了,養成最好人的秘密: 就是在野外開放的地方長大,和大地一起吃飯、睡覺。)看著她樸實滿足的笑臉,濃密憐惜疼愛之情油然而生。
我雖在學業與結婚間有些掙扎,但愛情的力量顯然消弭了我的恐懼。愛,就是她不嫌我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我們雖然是異國聯姻,來自不同的文化、種族,但我毫不懷疑她會是一位好太太、好母親。 不同的文化,難不倒彼此的溝通;不同的種族基因的結合才會產生混種的優勢(hybrid vigor)。 這是遺傳和生命演化的道理。當我們告訴她母親結婚的消息,她衷心地祝福我們,只希望我們的婚禮一定要在Allensville舉辦。
那年暑假我獲得了美國科學基金會的獎學金從6到9月要到Costa Rica及 Panama的雨林去接受三個月「熱帶研究組織」(Organization for Tropical Studies)主辦的的熱帶生態學訓練。按照行程,我在8月30日從Costa Rica回到美國,結婚的日子就決定在9月5日,地點就在賓州Allensville母親的家鄉舉行。 8月30日下機後,匆匆忙忙地趕到她的家鄉,買了新人該有的一雙新鞋,穿上從台灣帶來的西裝,就步入教堂了。美國結婚的風俗是由女方主辦,我想協助,也幫不上忙,一切都由她全部處理,我只要作個現成的新郎,出席即可。 我們就在當地教堂裡以傳統正式的儀式結婚,除了我的室友Jerry Bontrager做我的男儐相(best man)及一些哥森的同學參加外,所有的來賓都是女方的親戚朋友,男方只有我一個人。 結婚儀式後就在她家後院花園裡舉辦歡迎餐會。她的母親為了點綴出東方的氣氛,還在會場裝飾了很多的小燈籠。並作了一些東方的餐點,場面十分溫馨。 餐後,我們揮別送行的客人後,就駕車往西,以三天的時間,一邊度蜜月,一邊趕回 Bloomington。
結婚是生命的大事。從一切可預料的情況,我將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博士論文的研究;她將繼續在Bloomington醫院工作,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兩三年,沐浴在新婚規律安定的生活,直到我獲得博士學位後,再來面對一個生命的新選擇。 可是,生命的變數卻不是我們可以預料掌握。1970年在我結婚回到學校後不久,生命神秘的力量就一步一步地把我們推向非洲的道路上。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