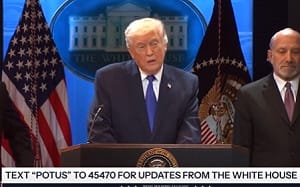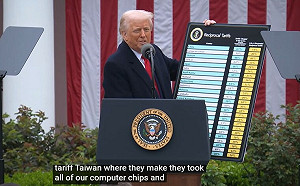台灣第一部談論面對當代灰色地帶戰爭(grey zone)的攻擊的《零日攻擊》在播出後,便成為這種輿論戰的典型受害者。它不僅在劇情中揭示中國可能發動的資訊戰,現實中也遭遇了與劇情如出一轍的帶狀攻擊。這種攻擊,比帶狀皰疹更致命,因為它不僅消耗個體,更扼殺了整個文化社群的公共討論空間,透過零日攻擊,我們所見識的是一場真實存在的潛意識戰爭,它沒有煙硝,不費一發子彈,卻從根本上攻擊台灣的民主基礎以及人民的鑑賞水準。
前言
「皮蛇若長一圈,你就會上西天。」—— 台灣民俗對於「皮蛇」的警告
帶狀皰疹是一種痛苦而纏綿的疾病,作為一種與免疫力相關的疾病,它的特徵不是一擊致命,而是長時間反覆發作,讓身體在持續折磨中逐漸崩潰。
但我們知道帶狀皰疹很可怕,卻不知道資訊戰中的「帶狀攻擊」攻擊更可怕,它不追求立即摧毀,而是透過低強度、高頻率、跨平台的持續性攻擊,讓目標逐步失去聲音與抵抗力。
台灣第一部談論面對當代灰色地帶戰爭(grey zone)的攻擊的《零日攻擊》在播出後,便成為這種輿論戰的典型受害者。它不僅在劇情中揭示中國可能發動的資訊戰,現實中也遭遇了與劇情如出一轍的帶狀攻擊。這種攻擊,比帶狀皰疹更致命,因為它不僅消耗個體,更扼殺了整個文化社群的公共討論空間,透過零日攻擊,我們所見識的是一場真實存在的潛意識戰爭,它沒有煙硝,不費一發子彈,卻從根本上攻擊台灣的民主基礎以及人民的鑑賞水準。

在外語圈,它被視為一記警鐘,許多評論者與觀眾認為這部作品真誠揭露了台灣人長年面對戰爭威脅的焦慮。英國《衛報》稱它是「直面焦慮的響亮一槍」,澳洲 ABC 新聞報導強調它因赤裸呈現可能的戰爭場景而備受關注。甚至有國際觀眾在 Reddit 上討論,認為這部劇「讓台灣的處境更容易與烏克蘭的現實對照」。
現正最夯:最高法院擋關稅! 川普反手加徵10% 台灣半導體壓力升溫
然而,在華語圈,卻上演了另一種劇本。從台灣的特定政客到中國的官媒,再到社群平台的大量帳號,短時間內湧現了「浪費公帑」「荒謬」「自嗨」「徵兵廣告」等高度重複的批評,宛如事先寫好的腳本。這種劇烈落差,顯示了語言環境的不同,更揭露了中國政府如何系統性地操弄輿論,企圖把一部文化作品轉化為政治攻擊的戰場
但這是如何開始的?
一.你的輿論不是你的輿論
「謊言重覆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覆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
讓我們先從原則開始。
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俄羅斯謊言水龍頭戰術》(Paul & Matthews, 2016, The Russian “Firehose of Falsehood” Propaganda Model),他們從俄羅斯攻擊烏克蘭的手段指出,現代資訊戰的核心並非「說服你相信」,而是「用持續訊息洪流干擾你判斷」。真假不重要,數量與重複才是關鍵。這正是「帶狀攻擊」的精髓。
其特徵可以歸納為三點:
低強度重複:
批評者不需要深度分析或嚴謹論證,只要持續丟出簡單標籤,如「大內宣」「恐嚇」「浪費公帑」。這些話語雖淺薄,卻因高頻率出現而產生心理暗示效果。
跨平台傳播:
從中國官媒到親中政黨,再到社交媒體帳號與網紅,形成「迴音室效應」(Echo Chamber))。每個平台重複同樣的話術,觀眾很難不被環繞。
心理與文化消耗:
當觀眾與評論者長期暴露於這種負面氛圍時,會產生心理疲勞與懷疑,甚至選擇沉默。久而久之,整個公共討論空間便逐步萎縮。
這意味著,台灣人以為自己正在參與一場自由的輿論討論,但實際上,我們的輿論場早已被系統化的帶狀攻擊滲透、引導與框限。

而從《零日攻擊》發布前到播出初期,輿論攻勢有明顯的時序集中現象。首先在正式上線前數日,攻擊聲浪就已預熱。7 月下旬預告片曝光後,部分媒體與人士便開始了他們的作戰。7 月 31 日,國民黨立委王鴻薇即在臉書發文,稱此劇「製造對立、抹紅異議人士,被包裹政治目的」,質疑主要投資者中華電信為何不公開投資額,指控民進黨「利用國家機器行政治目的」。
她甚至嘲諷出資的曹興誠是「大罷免大失敗領銜人」,將影集內容定義為選舉操作。也就是說,尚未正式播出,在野陣營已先行給本劇扣上「認知作戰」「大內宣」的帽子。隔日(7 月 30 日)中國國防部便緊接著表態開罵,如前所述,時機上「恰巧跟上」島內攻擊聲調。
《放言》媒體引述台灣政治工作者周軒評論,影集還沒上映,王鴻薇就和中方媒體同步抹黑,難免讓人懷疑是預先安排、心照不宣的配合。
而在正式播出後 24~72 小時內,負評更是以不正常的方式呈現爆發式湧現。2025 年 8 月 2 日晚間首集在台灣公視首播,不到數小時,PTT 上相關討論串已數度爆版。台劇板與八卦板同時討論熱烈。PTT 台劇板有不少正面評價覺得題材新穎緊湊,但在八卦板(Gossiping)卻幾乎被負面言論洗版。
該板 8 月 2 日上午的討論串中,在短短幾十分鐘內就湧入大量帳號留言,其中相當比例語句類似、緊抓相同論點,如強調「共軍飛彈飛過頭頂大家早習以為常,這劇還洗腦年輕人說不是侵略」「臉書上還造謠 YouTube 封鎖預告,蠢爆」等,也有留言一再使用戲謔語氣稱其為「娛樂大片」「替代役自慰神劇」「莒光園地必看片」等。
在首播 48 小時內,關於《零日攻擊》的負面文章密集出現在各類新聞專欄與社群,形成一波明顯的首映負評潮。這種同步湧現的節奏,與一般觀眾自發口碑發酵有所不同,更像是預先佈署的議題攻勢。
此後隨著每週新集數播出,負評輿論雖持續但熱度遞減,與內容走向高度相關,甚至有組織地「逢劇必批」,特別是每當劇情涉及對中共滲透、第五縱隊等敏感情節,加倍遭到特定人士公開炮轟。例如第 5 集播出後(8 月 30 日),親國民黨外國人方恩格立即發文揶揄劇情邏輯混亂並再度飆罵為「爛片」,中天新聞網當晚即刻發布〈美國人看不下去了!批《零日攻擊》荒誕爛片…〉的新聞,詳載其批評要點,與其他協同媒體讓其作為「美國代表」排兵佈陣。
而第 6 集《金紙》播出期間又爆發「抹黑羅景壬事件」,即導演羅景壬被人指控曾領勞動部補助而遭影射拿雙邊預算,他憤而提告加重誹謗的新聞,引來新一輪話題。第 7 集《海倫仙渡師》後,「逆風的烏鴉」此類粉專在 9 月中發文列數據試圖證明此劇熱度大跌、口碑崩盤,再次稱其為「民脂民膏砸出的糞作」。


可見從首映起的一週內,到連載中段,每隔幾天就有節點式的負評高峰,往往由熟悉的幾個帳號/媒體引領,再引發跟風轉載與評論。這種有規律的負面聲量起落,背後可能存在協調運作,包括提前備妥論點、按進度推動議題,以及運用社群與媒體交叉放大等手法。尤有甚者,異常的帳號活動也存在於這波輿論戰中,YouTube 上出現未授權上傳的劇集片源,其留言區聚集了許多新帳號,用流利中文刷負評,彷彿中國戰狼式「水軍刷屏」。
負評本身不是問題,因為無論是電影還是影集甚是 ACG,我們都會有正面負面的評價,問題在於負評的觀點是否多元,亦或千遍一律彷彿中央廚房端出來的量產大糞,而其數量與同質性如何讓其幾乎不像是活人用大腦想出的內容而像是機器傳播或者協同攻擊的第一波產物,或者諾羅病毒傳播到人身上後的嘔吐物。
讓我們對比一些因為語言差異而相對較沒那麼扁平的外語評價。
二.外國的觀點比較多元,還是華語輿論圈生病了?
在生產國的中華民國台灣,《零日攻擊》常被幾個不斷重複的單一標籤吞沒,進而造成輿論污染,然而,只要把視野移到海外,你會看到一張更複雜、更立體的國際輿論圖景。其橫跨歐洲、美洲、澳洲與日本,媒體各自帶著不同的關懷進場:
有的把它視為文化警鐘,有的把它放入社會系統與公共安全的討論,有的直接把它納入戰略與政策對話。這些差異,恰恰展現外語輿論場的健康與多元。

英國方面,最早可追溯到〈一記警鐘般的台灣戰爭想像〉(Taiwan war drama trailer rings alarm,《衛報》,2024 年 8 月 4 日)。報導把焦點放在「如何透過戲劇把恐懼具體化」,導演的談話被放在敘事的最前面:如果不把恐懼具象,社會就無從展開真誠的對話。它不去問作品「站在哪一邊」,而是問這部作品如何讓社會開始說話。同一篇裡,觀眾回應被視為公共感受的溫度計,強調「這像是我們不願承認、卻真實存在的陰影」。重視公共對話的《衛報》強調:「這不是內政,也不只是娛樂,而是一場社會心理學的演習。」
到了播出前後的重點節點,國際通訊社多次以不同角度切入。〈台灣《零日》電視劇製作方以中國入侵恐懼為背景〉(Makers of Taiwan’s “Zero Day” TV series set around invasion fear backlash China,路透社,2024 年 12 月 23 日)先從台灣影視產業風氣切入,創作者明知觸碰北京禁忌,仍決定拍攝;不少人選擇匿名,表明產業面臨的市場懲罰與政治風險。到了半年後,〈新電視劇想像中國入侵,給台灣觀眾當頭棒喝〉(New TV show imagines China invasion, gives Taiwan viewers wake-up call,《路透社》,2025 年 7 月 28 日)換位到觀眾側,強調這不只是娛樂,而是「讓社會演練最壞情境」的文化機制,報導清楚表達出普羅觀眾把劇作當作公共討論入口的心理狀態。
《路透社》兩篇一前一後,形成了「製作風險」與「社會反應」的對照,先說敢拍的代價,再說敢看的意義。

澳洲媒體則以系統思維見長。〈零日攻擊:電視劇想像中國侵略的後果〉(Zero Day Attack TV series envisions fallout of imagined invasion,澳洲 ABC News,2025 年 8 月 10 日)同樣不是在爭論政治立場,而是把劇中情節拆解成一串社會系統的連鎖故障:通訊中斷如何擾亂交通與醫療、金融體系如何觸發民眾擠兌、假訊息如何在焦慮中放大破壞力。ABC 的評論立體的呈現作品本質。這種方式與這波中國觀點主導的華語輿論圈裡常見的「一句話定生死」迥然不同:前者關注機制與韌性,後者困在標籤與立場。
美國主流報紙把它放入更廣的文化現象觀察。〈在銀幕和遊戲中,台灣上演了一場中國入侵〉(On screens and in games, Taiwan acts out a Chinese invasion,《華盛頓郵報》,2025 年 8 月 23 日)則指出,台灣社會不只在電視上排演戰爭,也在電玩、兵棋推演與模擬訓練中反覆排演。這篇報導把《零日攻擊》視為「文化上的國安演習」的一環,並放入更大的地緣政治敘事內。這種觀察不是稱讚或撻伐,而是體現文化如何讓社會練習面對現實。
從政策與戰略視角介入的,則是〈電視能幫助人們準備入侵嗎?〉(Can TV Help Prepare for Invasion?,《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25 年 8 月 29 日)。作者把《零日攻擊》放進「edutainment(寓教於樂)」與「公共韌性建設」的討論框架,戲劇當然不能增強火砲口徑,卻能在心理預演與社會動員上強化集體免疫力。文中比較其他民主社會在冷戰、反恐期間的文化產品,主張這種作品能把抽象風險翻譯成大眾可理解的情境,進而促使民間組織、地方政府與學校在非軍事層面強化準備。這完全跳脫華語圈「是不是宣傳」的窄化,轉而問「能不能讓社會更有準備」。
拉美視角帶來另一種觀點。〈零日攻擊:台灣的文化里程碑〉(Zero Day Attack: A cultural milestone for Taiwan,《資訊網》(Infobae),2025 年 8 月 2 日)指出:把侵略情境拍成主流劇集,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坐標的移動。報導連結到台灣延長兵役、全民防衛課程等政策現實,視這部劇為社會情緒與政策變化之間的體現。這個角度尤其可貴:它並不鎖定台海議題的中心,但仍能以風險社會的共同語言讀懂台灣。
在東北亞,日文輿論把它直接對接到「台灣有事」的國安討論。〈「台灣有事」的戲劇化預演〉(〈ドラマ化された「台湾有事」〉,《世界日報》(世界日報日語版),2025 年 8 月 18 日)強調這是台灣第一部正面處理「台灣有事」的主流影集;而〈灰色地帶作戰的實景化敘事〉(〈グレーゾーン作戦の“実景”化,〉《日本實業論壇》(實業之日本フォーラム),2025 年 8 月 27 日)則引述專家峯村健司,指出劇中從資訊操弄到社會癱瘓的連結高度貼近中國現實統一戰線/混合戰的手法。日本文本的關懷很務實:它不是評論藝術優劣,而是問戰術與社會影響是否真實。

同一時間,華府的政策圈把它當成公共外交與國際認知的一部分。〈「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在華府舉辦《零日攻擊》放映會,引發對台灣安全與韌性的對話〉(GTI Hosts Film Screening of Zero Day Attack in Washington, Sparking Conversations on Taiwan Security and Resilience,2025 年 9 月 4 日)記錄了在華府舉辦的座談會,與會者把《零日攻擊》視為提升國際理解與內部對話能力的文化媒介:虛構不等於虛假,戲劇可以是把抽象威脅轉化為公共語言的工具。這種語境下,影集已越出娛樂領域,進入了跨部門的風險溝通與盟友社群建設。
條列來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外媒觀點的「多元觀點」:
— 英國報紙從文化對話啟動切入;
— 路透社以製作風險/社會反饋雙篇對照;
— 澳洲公共媒體以系統韌性做情境推演;
— 美國全國性報紙把它放進文化—戰略交叉的觀察;
— 政策雜誌進一步提出公民防衛教育的命題;
— 拉美媒體凸顯創作自由與反自我審查;
— 日本文本直連台灣有事/灰色地帶作戰的安全辯論;
— 華府智庫則把它收束為國際認知與公民韌性的討論場。
這些差異並非偶然,而是資訊生態與新聞傳統的結果,比起扁平的褒貶,他們的媒體專注開展影視評論的立體空間。
— 它是怎麼被拍出來的?(產業與風險)
— 社會為什麼需要這樣的故事?(公共心理)
— 如果情節變現實,系統會如何崩裂?(基礎設施與韌性)
— 文化如何幫社會演練最壞情境?(文化戰/國安演習)
— 戲劇能否成為公共教育資產?(edutainment/政策傳播)
— 這對國際理解與聯盟政治有什麼影響?(公共外交)
而正是這些層次,使外國媒體的評論彼此不同、彼此補充,形成一個真正多元的討論場——即便有人保留、有人質疑,也不是用單一標籤抹平一切,相反地,它們把爭議拆解為可被辯論的延伸議題,讓讀者自己形成判斷。
那麼,這是否表示華語圈評論能力較為低下?或許也並非如此。
因為根本上,如同戰爭時躲在掩體後雙手抱頭的人不見得不會用槍一樣,這不是知識的問題,而是槍林彈雨下的勇氣問題。
不過在回到台灣本土前,我們可以前進日本一下,因為目前根據官方資訊,海外合法觀賞零日攻擊的管道,其實只有日本亞馬遜,而外媒們多半是親自前往台灣或者與官方取得線上合法觀賞途徑,所以比起觀看途徑不明的外語觀眾或者海外中國人,我們不如來看看日本觀眾的看法。
三.機器人和假外語人滾蛋吧,看看日本觀眾怎麼看
《零日攻擊》在華語圈所遭遇的負評潮,早在播出前就展現出協同操作的跡象,並非自然形成的口碑,而是一種「工廠化生產」的資訊攻擊。
這類攻擊有幾個明顯特徵。首先,語言高度重複:社群平台充斥「大內宣」「恐嚇片」「浪費公帑」等標籤,幾乎無分析、無舉例,只是大量複製貼上,符合蘭德所謂「謊言水龍頭」的低內容、高頻率特徵。
其次是跨平台同步:從 PTT 到 YouTube,從台灣在野政黨到中國官媒,言論步調驚人一致。當國民黨立委批評影集的同時,中國國防部也緊接跟進,形成「雙聲道操作」的戰術態勢。

更進階的是「假外語人」
自稱國際觀眾、語句格式化、內容空洞,意在製造「全球都在笑台灣」的錯覺,打擊本地觀眾信心,讓真正的觀眾選擇沉默。
這些帳號多為新註冊、評論集中於單一主題,與機器人或水軍配合,短時間內湧現負評,壓制正面聲音,讓留言區成為心理戰的第一線,而他們的目的是吸引原本就討厭本劇集但可能從未收看的觀眾,以機器帶動真人,或者以真人帶動真人的方式佔領討論區。
總結來看,這就是典型的「帶狀攻擊」:低強度、高頻率、跨平台操作,再加上假國際視角,最終讓真實觀眾噤聲、輿論空間被污染。
因此,當我們回顧《零日攻擊》在華語圈的遭遇,可以說它不僅僅是影視作品的爭議,而是一場活生生的「輿論戰實驗」。這種帶狀攻擊的威脅,比帶狀皰疹還要致命,因為它並非只攻擊個體,而是針對整個社會的認知免疫系統。它讓專家不敢評論,讓觀眾懶得辯駁覺得疲憊,最終讓公共空間被廉價口號占滿。
如果說華語圈的評論場域被「帶狀攻擊」與「假外語人」充斥,那麼日本觀眾的反應則提供了一個對照組。因為目前在外語市場中,日本是唯一合法能透過日本亞馬遜( Amazon Prime Video Japan) 收看《零日攻擊》的國家。這讓日本觀眾成為極為珍貴的樣本:他們相對不受華語圈的資訊攻擊左右,而是憑著自身的文化語境與觀影經驗,給出多元且細膩的評價。
讓我們先看看日本知名媒體的評論:

除了剛剛提到的《日本實業論壇》、《世界日報》外,
《JBpress》在專欄中以《「與中國的戰爭早就已經開始了」—— 正在 Prime Video 上播出的台灣影集《零日攻擊》,完成度實在令人驚艷。》(〈「中国との戦争はとっくに始まっている」プライムビデオで公開中の台湾ドラマ『零日攻撃』の完成度がとにかくすごい〉.2025 年 8 月 17 日) 為題,乾脆地把這部劇視為「現實的延伸」,標題就直言「與中國的戰爭早就開始了」。文章大幅肯定其完成度,並把它納入「東亞深層取材」的脈絡,顯示日本評論者不只是談影視,而是直接連接戰略格局。
《毎日新聞》在 2025 年 8 的報導〈描繪中國入侵的非典型台灣影集《零日攻擊》,製作團隊的想法是什麼?〉(中国による侵攻描く異例の台湾ドラマ「零日攻撃」)。
2025 年 8 月 10 日,把重點放在創作者的聲音。它引述劇組成員的說法:「這不是宣傳,而是要讓觀眾面對現實威脅」。報導同時指出,台灣的文化人往往要冒著市場與政治的雙重風險才能完成這樣的創作。這是日本媒體對「自由與表達」框架的熟悉切口。
《文春線上》同樣在 8 月 8 月的新聞〈如果台灣有事成真會怎樣?高橋一生也參與演出,大膽挑戰禁忌題材的影集《零日攻擊 ZERO DAY ATTACK》〉〈もしも台湾有事が現実になったら?高橋一生も出演、大胆にタブーに挑戦したドラマ『零日攻撃 ZERO DAY ATTACK』.2025 年 8 月 23 日〉,則把焦點拉回到卡司與題材禁忌。報導強調「高橋一生」與「水川麻美」的跨國參演,並藉由訪談台灣演員楊大正、連俞涵凸顯「這樣的題材本身就是一種挑戰」的概念。換言之,文春把它當成娛樂圈內少見的「禁忌突破」。


文化導向的 CINRA.NET 則在 2025 年 8 月發表〈描繪中國軍事侵略的台灣影集《零日攻擊》,為何會誕生?「這對日本來說不是別人的事」〉(〈中国の軍事侵攻を描く台湾ドラマ『零日攻撃』、なぜ生まれた〉2025 年 8 月 22 日),則向團隊追問:為什麼台灣會誕生這樣一部作品?這樣的作品與日本又有何關係?它探索台灣社會的現實壓力,以及這部影集如何把日常與國安議題連接起來。這樣的框架屬於文化新聞的典型,即去追問「生成的條件」,而不是單純判斷好壞。
至於非專業媒體的一般日本人呢?
在日本的 Note 平台,有觀眾在第 5 集後寫道:「這一集同樣是資訊密度極高的劇情,中國與台灣的戰爭逼近,緊張感逼人」(「今回もまた、手の込んだ情報量の多いドラマ展開です。中国との戦争が目前にせまり、緊張状態が続く台湾」;渡瀬水葉,Note,第5話レビュー)。這樣的文字不僅顯示觀眾對劇情的專注,也表達出他們會直接把影像文本連結到當前地緣政治緊張的敏感度。另有第 8 集的心得則談到跨境家庭與校園霸凌橋段,強調這些情節「極具說服力」(「説得力があった」;渡瀬水葉,Note,第 8 話レビュー),顯示觀眾感受到戰爭如何滲入日常生活與親密關係。
在 Filmarks,日本最大的影視評分社群,數據更直觀地揭示了輿論狀態。該劇目前的平均分數約為 ★3.5(Filmarks,劇集頁面),呈現「兩極化」分布。支持者強調:「這部劇不是拍戰爭本身,而是揭露有事下的社會恐慌、資訊戰與輿論操弄」(「戦争そのものではなく、有事の社会的パニックや情報戦、世論操作を浮き彫りにした」;Filmarks,用戶評價),甚至有人感嘆「這樣的企劃在日本幾乎無法通過」(「日本ではこの企画は通しにくい」;Filmarks,用戶評價),顯示對台灣影視敢於處理嚴肅題材的敬意。另一方面,批評者則直言「節奏拖沓」(「テンポが悪い」;Filmarks,用戶評價),認為節奏掌握尚待加強。可見日本觀眾的正反意見雖然矛盾,但都集中在敘事與技術層面,而非空洞的政治標籤。
此外,在 X(Twitter) 上,部分觀眾將劇情轉化為寓言式的解讀。例如有人提問:「連公務員都只是為了私利行動,那麼國家究竟是什麼?」(「公務員も含め皆が自分の利得で動く、国家とは何か?」);也有人認為第 7 集「像是日本《世界奇妙物語》的風格與台灣寓言的融合」(「世にも奇妙な物語タッチ×台湾ローカルな寓話」)。這顯示出日本觀眾願意將作品放入自身文化框架重新閱讀,而非僅停留在表層批評。
即使是在匿名論壇 5ch,也有人展現出自律氛圍。有網友提醒:「Amazon 的早期評論很多只看了一集就打分」(「Amazon の早期レビューは1話だけ見て評価しているケースが多い」),呼籲大家「應該完整看完再下結論」(「全話見終えてから判断すべき」)。這樣的討論雖然瑣碎,卻透露出一種「共同體責任感」:即便分數不高,觀眾仍願意彼此勸誡不要草率。
綜合來看,日本媒體與觀眾的反應具備三個關鍵特徵:
1.多層次性:評論不只停留在喜歡或不喜歡,而是從劇情細節到社會寓意進行全方位分析。
2.兩極化但有根據:支持與批評都有立足點,爭論的核心是戲劇手法與現實意涵,而不是意識形態標籤。
3.文化對話的自覺:觀眾能把台灣的經驗轉化成反思日本社會的鏡子,讓作品超越國界,進入更廣泛的公共議程。
這與華語圈「帶狀攻擊」的空洞喊話形成絕對反差:前者是機器人和假外語人用來毀滅討論環境而製造的噪音,後者是真實觀眾透過文化文本進行的有益於多元觀點交流的對話。正因如此,當我們說「機器人和假外語人滾蛋吧」,不是單純的情緒發洩,而是一種文化戰線的宣言:
唯有真實觀眾的多元聲音,才能守住影視作品的公共價值,抵抗資訊戰對輿論空間的污染。

四.面對恐懼與嘲諷,專家和粉絲該怎麼辦?
如果你能讀到這邊的第四段,就算你不是喜歡《零日攻擊》或者 L.U.C 的粉絲,甚至根本不認識 Lizard 那我想你也不會是機器人或者假外語人,畢竟這字數已經超越了八千字,所以你能讀完你的認知能力以及教育水準應該有一定程度以上,就算是個反對方也是一個有一定程度的反對方。
所以讓我們進入這篇文章含金量最高篇幅最短的最終段落。
前面我們先從國內輿論泥巴攻勢再到外語媒體多元觀點,接著到了我們的亞洲好朋友日本,現在我們要回到本土,來探討一下對《零日攻擊》的帶狀攻擊在台灣如此有效的原因。
首先,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會知道,如果希望《零日攻擊》不淪為二元式的扁平討論,而是要像前面國際外媒或者日本那樣展開立體的討論空間,我們首先需要跳脫政治紛爭,透過影視的類型分析或者具體的文本描繪來展開討論其內容與延伸議題,而且不急於馬上褒貶。
在台灣,最擅長做這件事的人,就是影評。
以下為了減少紛爭,模糊焦點,我就不特別一一點名了,但若平常有在觀看影評的人,絕對會發現許多平常就有在熱烈活動的影評對於《零日攻擊》其實是三緘其口的,無論是寫文字可以寫的深情款款、義正嚴詞,還是拍影片可以說的趣味橫生、充滿智慧的那些你經常甚至等等你划手機或者看YT會滑到的影評……
他們多半對《零日攻擊》噤聲。
我當然也不點名這次有談《零日攻擊》的影評或相關媒體,畢竟如果這樣做的話,他們原本默默實踐他們身為影視評論產出者的義務或者責任又會被歪曲成為特定政黨的側翼了,這是我們國內現在輿論環境對文化生產最有病的氛圍,那就是我們的許多國民一邊說「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的同時,卻任由政治強姦藝術,讓藝術不再能想像與詮釋我們所生存的現實,最終需求帶動供給,讓市場上不再有這樣的「純粹藝術」,而只剩下「閹割藝術」。
這不是一朝一夕在台灣發生的事情,藝術本身都是如此,遑論對於藝術的評論?
那我想要具體的談什麼呢?

我要談的是促成這種環境,要談的是影評噤聲後,「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妖魔鬼怪取代各方正神坐到神壇上開壇弘法、扭曲教義的根本原因,除了最一開始前述來自中國中央廚房以及國內特定政黨或者意識型態,也有影評這個「職業」的當代處境。
在社群媒體時代,影評這個「身分」早已非傳統報章雜誌專屬,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正如 2023 年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付費文章《從爛番茄五十美事件淺談當代影評人的處境》所寫的,傳統意義上以影評為業即可生存的「專業影評人」早已在當代消聲匿跡,而這與我們網路科技進步大有關係:
這些本來該成為「專業影評人」的人們,如果不是躺在墳地(比如羅傑.埃伯特(Roger Ebert)、寶琳.凱爾(Pauline Kael))此時可能正在教學,上班,或者跑 Ubereat,事實上,如果我們說「專業」意味著此人以此維生,我們在當代幾乎沒有所謂「專業」影評人,他們往往還有其他更能營利的身分,比如前述的教授,上班族,外送師,作家,娛樂記者,或者當代一點,youtuber 或是 titoker。
其實專業影評人消失不是這幾年的事情,隨著網路文化興起,人人都能在社群網站發表自己對電影的評語,影評就沒那麼神祕與稀奇了,而在網路上發表自己對某部片的好壞評價,往往就是成為影評的第一步(所以爛番茄粗暴評分長期被學者或者電影人批評,怎麼可以把不同類型片放在一起,不同群體的人分數拿來平均,甚至只分成影評跟觀眾就覺得分類夠準確了?但批評又如何呢?爛番茄就是可以拿到資金繼續使用,因為很多人看,這意味著很多人贊同這樣的作法。)如果他走的更遠,遠離人群就是一件很可能的結果,畢竟電影裡所有的元素,你都可以深入要求到極限為止。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這不過是一家之言,那麼,讓我們看看《放映週報》這個台灣的有公信力的國家的媒體的那篇《「老派」影評的浪漫:訪柏林影展策展人潔西卡江》吧,為《綜藝》、《視與聽》、《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電影評論》這些有頭有臉的媒體撰稿的潔西卡江(Jessica Kiang),作為柏林影展策展團隊成員的這位資深影評人,對於影評人作為一項全職工作怎麼說呢?
「除了報紙媒體,基本上沒有什麼固定的讓你寫作的影評「正職」,在(英語)報紙的正職影評工作,全世界只剩下大約 10 個了。而這些崗位的數量還在不斷減少。」
當多數影評人都必須以此為副職,那些能讓他們以此獲利的工作自然不該付出太大的成本,或者反過來說,必須獲取他們認為足夠值得的利益他們才能全心投入。
而無論是身為前者還是後者,都沒多少人,特別是那些已在此領域有成就的人,願意為了《零日攻擊》這樣駛入台灣影視禁區的作品冒險,特別是他們必須承受軍事等級的網路攻擊持續的在他們談到《零日攻擊》的臉書粉專或者 YT 頻道上的惡意留言的精神負擔以及實際流量的可能損失的時候了。
他們可能光是寫文就必須承擔巨大壓力,更別說發出後等通知甚至是看私訊了,如同那些喜歡《零日攻擊》的粉絲,在對作品發出具體稱讚前,往往也必須擔憂是否會被人嘲笑一樣,除非該討論區已有大量支持者留言,抑或是經營者有秩序且決斷的管理惡意留言與異常留言,那麼這種狀況實在是難以避免。
因為有別於自由且觀點各異的個體,成群且統一的網軍將會順著「#零日攻擊」的標記一路找到他們,如同所有上架《零日攻擊》的平台的官方粉專一樣,那本身就是毀滅影視討論立體空間的惡意襲擊。

而如果影評們或所謂影視 KOL 今天是靠網路品牌生存時,與《零日攻擊》牽扯上任何關係,都可能對他們的粉絲造成巨大割裂,特別是在網軍或者偏激的真人帳號刻意留言引戰下,留言區馬上就被有意分割成兩派互動,而引戰者可能隨時都可以脫出這個用來引戰的並非他本人所持有的隨手可拋棄的非唯一帳號,將戰場交由兩派真人互鬥。
就像地頭蛇照三餐替你的店鋪「裝修」,三天兩頭一次,一開始你的客人就算同情你而繼續光顧,但到後面他好一點是為了自身安危帶著歉意逃跑,糟一點就會覺得你難道沒半點問題也開始懷疑你。
更別說在台灣社會,由於過往威權統治的後遺症,還有轉型正義的做半套,大部分時刻我們的影視產品的主要功能,就是像中國的那些當代影視產品一樣,負責替觀眾提供一種現實的逃逸路徑,而電影也好影集也罷,都是看完後不久即忘掉最好別帶到現實的東西,又或者是建構在虛構語境來操作來遊戲的東西,比起那些疏理歷史脈絡,解構權力關係以及社會現象的作品,我們更喜歡那些快義恩仇,刺激我們大腦分泌多巴鞍,甚而透過溫情主義賺我們熱淚不問是非只求和解的作品。
追根究柢,我們或許該過問自己,什麼時候「國家安全」被染上了政治色彩?而我們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潛意識與歷史傷痕抑或是經濟關係,也漸漸遠離此類放在我們眼前的現實問題?
那些口口聲聲說《零日攻擊》有色彩的人,手頭的油漆桶從未乾涸,正如他們從未放下他們手中的槌子,讓他們覺得會惹怒中國的作品,通通變得扁平一樣。
鄉愿者,德之賊也。而無論是政府還是百姓,我們對於勇於捍衛多元討論空間,讓惡意破壞者付出代價的決心,以及對於偉大藝術的追求與執著,遠遠無法超過我們對於中國的恐懼,還有那塊看得到但可能根本吃不到的中國市場的渴求。
我們欺騙自己帶狀攻擊是出於一般個體的自由言論,正如我們欺騙自己身為影評有「民主社會有不表態的自由」,這些自我欺騙終將會讓我們付出代價,因為我們自我欺騙這只是「遠離一部有爭議的影集與風波」實際上卻是向我們的敵人俯首稱臣在還沒戰敗被關進他們的網路長城前就自我禁錮。
而這一切終將讓我們的靈魂窒息,在血紅的皮蛇纏繞我們的腰際,使我們的肉體壞死前。
作者:Lizard,現經營海底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