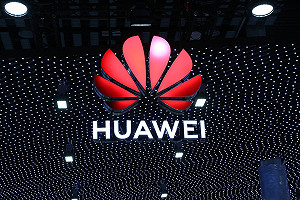王滬寧是要做和平使者, 還是統一加速師?「一國兩制」在香港搞砸難道與他無關嗎?對台灣來說,他目前所扮演的其實是一個虎姑婆的角色。
《虎姑婆》,是早期流傳在臺灣的民間故事, 敘述山上的老虎精化身為老太婆,在夜裡拐騙小孩並吞食裹腹。
「咦,姑婆,你在吃什麽啊?」「沒有啦,快睡吧。我在編新的《一國兩制》。」
去年初台灣的大選顯示 ,國民黨人除了號召與對岸貿易互惠之外,缺乏兩岸關係的論述。 他們不能像民進黨那樣,有鮮明的本土意識和台灣主體性論述。但面對中共的文攻武嚇,他們又不得不避開統一議題。
事實上,台灣的主流民意不可能接受統一。去年大選期間,前總統馬英九在接受外媒訪問時,只說了一句「要相信習近平」,就令國民黨大驚失色。民進黨明確地要抗中保台,國民黨只能主張綏靖,要和平保台。
2024 年台灣大選結果,民進黨繼續執政。國民黨在立院席次略微領先 ,加上民眾黨的八席不分區立委,形成在野聯盟,就可在立院造成霸凌局面。
去年 12 月下旬,國民黨、民衆黨立委聯手,三讀通過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憲法訴訟法》、《財政收支劃分法》,果真引發了憲政危機。

傅崐萁率立委前往中國拜見王滬寧
尤其是他們大砍國防預算,危及台灣的安全防衛, 引起民眾普遍恐慌。 這是目前爆出罷免潮的肇因。
追溯起來,藍白在野聯盟去年的一連串舉動,和大選後國民黨黨團總召傅崐萁率領 16 名立委到北京拜見王滬寧顯然是有關連的。
是聼命配合嗎?黨團宣稱會見的目的是要拓展兩岸貿易,招商引資。但返台後有必要大砍國防預算嗎?
從憲政危機的幅度來看,全面大比例的裁撤政府經費,連消防影劇部門都不放過,在野聯盟的意圖似乎是要使新任政府運作困難,功能癱瘓。
但這樣做是否就能保證在下屆大選達到政黨輪換的目的,是值得懷疑的。政策滯礙難行引起的民怨,會讓在野黨加分嗎?

一國兩制替代方案──「化整為零」、「誘拉基層」
王滬寧是中共政協主席,也是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習近平)。他在會見時依舊重談一中原則、九二共識的老調,但已不提一國兩制,因為一國兩制已在香港搞砸了。
有傳聞說,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正在擬定針對台灣的另一套「一國兩制」。這也不出奇。2023 年 9 月 11 日,中共曾宣佈《堅持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一看便知是出自王滬寧的手筆。
習近平是希望王滬寧能創造一國兩制的替代方案,從而更快的解決台灣。
2023 年 12 月初,在對台工作會議上,王就指示各部門應通過「化整為零」、「誘拉基層」的方式(如邀請台灣基層里長到大陸訪問交流),介入 2024 年的台灣大選。
目前中共對台工作的大方針是促進兩岸交流,大方針底下的小方針是設法打擊台灣的執政黨 。中共希望動員台灣的「愛國力量」來「反獨促統」,但根據台灣民調,主張與大陸統一的台灣民眾還不到人口的十分之一。如何動員呢?
《總體方略》是一方面擺出和藹可親的面孔,另一方面又派軍機軍艦對台灣耀武揚威?一會兒來軟的,一會來硬的,好像打擺子一樣。這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嗎?
眾所週知,習近平十分器重王滬寧,走出檯面,王滬寧隨時跟在身邊。

1980 年代王滬寧「一國兩制」初登場
王滬寧是要做和平使者, 還是統一加速師?「一國兩制」在香港搞砸難道與他無關嗎?對台灣來說,他目前所扮演的其實是一個虎姑婆的角色。
為什麼是虎姑婆呢?國民黨人為什麼要去巴結虎姑婆?
筆者不妨在這裏説點歷史掌故。這要從曾經在《九十年代》寫專欄的文友嚴家其説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要改革開放,趙紫陽的領導班子找了基督教會方面的趙復三去擔任社會科學院的常務副院長。趙復三提拔了他賞識的嚴家其當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當文學研究所所長。那時候的政治氣氛寬鬆而有朝氣。
1983 年政治學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邀請海外臺籍學者參加的「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
1985 年又在廈門大學舉辦第二届「台灣之將來」討論會。
事實上,李怡曾提到,在中英談判開始不久,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就邀請了一些學者和時評家來討論當時的一個熱門話題:「國共談判,實現統一」。主持人是當時中文大學副校長,著名考古學家鄭德坤。

台灣學者翁松燃:統一不用問過台灣人?
有趣的是,當時不論左派右派,都認爲統一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那時候台灣還處於蔣家的戒嚴統治下,官方的統一口徑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所以受邀與會的中文大學翁松燃等幾位台灣學者,發言不能說沒有風險。
出生於台灣埔里的翁松燃教授,首先就提出「統一是否一定好,不統一是否一定不好」的問題,立刻對所謂「天經地義」的想法形成挑戰。
翁教授表示,統一是不是國共兩黨的問題?是否由國共談判就說了算?不需要問過台灣人?
他們幾位台灣學者指出,台灣在歷史上一直任人擺布,清廷敗於日本,拿台灣做犧牲品,國民黨敗與共產黨,就把南京政府遷來台灣,實行戒嚴。
現在中共說要統一,好像也不需問台灣人有什麼想法。作為台灣人,他們的心情會愉快嗎?
其實,同樣的問題也可以質問當時中英談判下的香港人。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有自主權嗎?
一國兩制是人類偉大構思?
在 1985 年 8 月第二屆「台灣之將來」的討論會開幕之前,復旦大學學者王邦佐、王滬寧在《政治學研究》(1985,第 2 期)上發表了談主權與治權關係的論文,那是一篇主張主權至上的「威而剛」式硬梆梆的文章。
這篇文章強調一國是兩制的立足點,主權是兩制的前提,主權與治權並非對等關係,不同制度地區的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
王姓師徒二人在復旦屬於保守派的馬列學者。 後來中共人大常委會的一位發言人,曾是中英談判中方成員的李飛,在記者會上針對香港治權所説的中央給或不給,給多少之類的話,是順著二王的同樣理路而來的。
嚴家其在《政治學研究》同期發表的討論一囯兩制與中國統一的論文,則是從理論上試圖為《一國兩制》下定義。出身台大法學院的翁教授,對他下的定義還做了些修改。
翁松燃為第二届「台灣之將來」討論會做了一篇論文:《一國兩制》芻論:概念、性質、内容、困難和前景。
那時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已生效。 鄧小平的 《一國兩制》正被京港官方媒體吹捧為人類歷史空前偉大的構思。
台灣學者翁松燃:預言一國兩制困難 一一應驗
翁松燃則指出,在中共眼裡,「一國兩制」 絕非兩個治權地區地位平等,互不管轄,各自為政。只要與單一制的原則和主權在中央的原則相違背,中共是一概不能接受的。
兩制並不平等,必須有主從關係。 翁松燃舉出了「一國兩制」概念在性質上的矛盾性、壓倒性和過渡性。
在中央極權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允許資本主義制度在部分地區共存,取決於與當權者的意願和能力,因此穩定性和可行性就很成問題。
壓倒性就是兩制之間大小輕重地位不相稱、不均衡、不平等,以致一方隨時可能被另一方壓倒或吃掉。
實行社會主義的地區若處於支配地位,實行資本主義的地區只能處於被支配地位。再說,主體制度的一方不可能向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一方過渡,因而才須設定兩種制度並存的期限,但就憑領導人鐵口直斷的一句「五十年不變」,又如何保證能夠平穩過渡?
翁教授的論文在《政治學研究》的論文集中刊登了前半部,批評「一國兩制」的矛盾與困難的後半部就付諸闕如了。這是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
不過全文完整的刊登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1985,12 月號)。那時候香港的基本法還沒開始制訂呢。翁教授所預言的「一國兩制」在性質上的困難與問題,後來不幸一一應驗。
《一國兩制》這個原先為香港回歸而設計的「宏大巨構」,為什麼要在「台灣之將來」研討會中推出呢?因為這個構想是要「垂範」台灣的。香港在京官眼裏,已是甕中之鱉,對台灣則是要請君入甕。
作者:殷惠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為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錫雍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