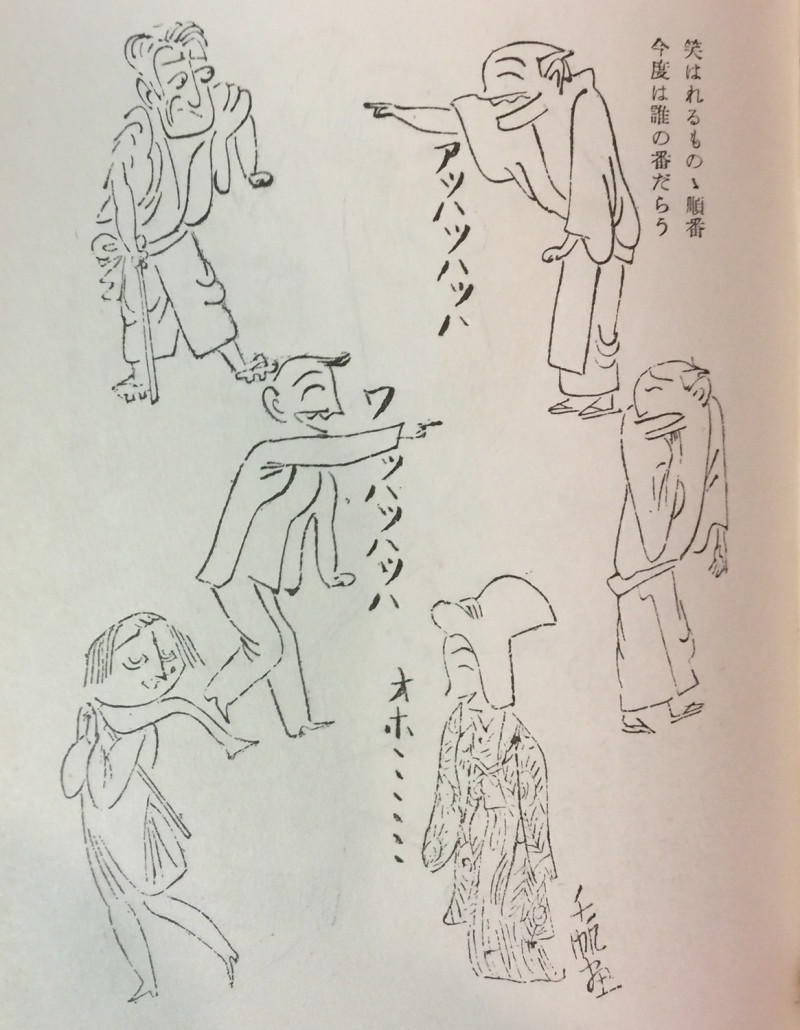引言: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進而的困境,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五章 通體照亮的漫遊者
一直同在政治甬道
「警察也來帝女花嗎?」塞林傑問道,「正因如此,這裡才成為洽商的場所嗎?」
「嗯,不排除這個因素。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難免就會發生糾紛。不過,當他們沒有把事情鬧大之前,還要察看餐廳有無警察在場,即使來的是休班的警察,他們就會收斂住暴戾的氣焰。」萬克強吞了吞口水,繼續說道,「這對雙方都是好事情,你喝你的黑咖啡,我吃我的烏骨雞湯,同屬於黑暗的愛好者,各自獨立又不相互隸屬。」
說到這裡,杰德突然插嘴說道,「萬先生,我認為後面這段說明有點問題,乍聽來,似乎在暗指現今兩岸三地的現狀。這樣一來,就跟咱們以和為貴的從商理念相違背了。」
當前熱搜:越射越少! 伊朗導彈不再是威脅了? 以色列宣佈8日重新開放領空
「老德,你一定聽錯了。誰不知道兩岸三地的問題,最容易挑起敏感的政治神經,咱們生意人盡可能避而不談。既然如此,我怎麼會在這場合上自掘墳墓呢?我的意思是,要阻止衝突事件的發生,有時候需要某種公權力的介入,不管是明的暗的,只要警察在場,它就能達到預防的效果。」
「萬先生,我沒有別的意思,完全出於好意為你和為塞先生著想。不久以後,咱們就要去考察普洱茶的市場了,在這節骨眼上,萬一因政治立場的問題,把咱們給牽扯進去,那可是得不償失呀!」
「萬先生,」臉色微紅的塞林傑問道,「如你所說,我們只是做生意投資,不牽涉敏感的政治問題。是這個意思吧?」
「那是當然。我再強調一次,我是不輕易顯露自己的政治立場,總希望以和諧代替衝突,如果哪天我在某個占優勢的場合,有人要我正式表態的話,我不但不反對,甚至會順應他們的政治訴求,支持他們高舉的意識型態呢。」萬克強說,「塞先生,雖然咱們不是共同出資者,我只發揮仲介的角色,但總是想方設法為你多拉些裙帶關係,幫助你早日取得成功,絕不可能將你置於危險的境地。」
「咦?」塞林傑詫異問道,「至少,我不是翠玉茶黨的黨員,不具該黨員的身份,到大陸做生意就不會遭到刁難吧?進一步地說,如果加入車輪黨或者認同血色太陽黨的政治旗號,就有利於開發普洱茶的市場,那麼我願意立即報名填表。」
「塞先生真是幽默,」杰德說道,「在大陸,除了兩岸統一的宏觀論述以外,其他的政治主張全是廢話空文。總歸一句,咱們到內地城市考察,你就會明白這個道理,所謂百聞不如一見,看到事實才有發言的權利。」
「哎呀,兩位的論點真是精彩!」白雲飛說話的表情,給人一種錯覺,以為他們三人是初次相識,因為真實的驚訝的確多於虛應故事。
「這哪算什麼高見,我只是實話實說罷了。白先生,讓你見笑了!」杰德用充滿世故的聲音說。
「是啊,雲飛兄,這都是普通常識,你也知道的,只是不說出來而已。不過,平常多來些腦力激盪是好事,朋友相約泡茶聊天,往往能激發出新的創意來。聽說,那些很厲害的小說作家,就是用這種方式,從說話者那裡挖掘到寫作的題材。我沒有寫作才能,就算想寫也寫不成。但是,我認為寫作如同在做生意一樣,每個環節都得仔細計算才行。」
經由萬克強的細心安排,跑單幫的杰德已升格為兩岸貿易的牽線人,他說話的音量越來越有自信了。從本質上來說,萬克強是個生意人,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比任何人深刻體會,見風使舵這顛撲不破的真理。他不守住這條生存的底線,早就從這個業界被踢除出去了。例如,他吃過幾次暗虧以後,就知道問題所在了,出售宜興古壺給大陸買家的時候,只能選用《超越宇宙大團結時報》舊報紙包裹,不小心用《自由台灣光明報》作為包材,等同於給自己增添不確定的危險。
美好而愉快的晚餐即將結束之際,四個不同業種的人:骨董商、土地代書、茶葉單幫客和旅館接班人,都在各自描繪著金色的未來。他們的笑容和聲音,似乎已說明了一切;幾個男人聚在一起吃飯聊天,竟然能談出一片大好江山來。塞林傑在心裡喊著:這不是現代版的神奇夜譚,什麼又是神奇夜譚呢?
就在這時,帝女花咖啡廳入口處傳來了叮噹的聲音,那扇吊掛裝飾性物品的門扉被推了開來。一個體型臃腫的大叔走了進來。他沒有向站在收銀台的老闆娘打招呼,而是像管制燈塔上的探照燈一樣,朝餐廳內部進行掃視著,似乎在數秒鐘內,就要尋得待見的人,一點也不想浪費時間。沒錯,時間就是金錢!這句格言對任何業種的人來說,都很適用具有正當性。
果真,他花費不到五秒鐘就找到目標了。他看見萬克強和白雲飛,立刻向他們揮揮手,並送上職業性的笑容。何謂職業性的笑容,即皮笑肉不笑,看起來很假的那種。但是,當你用高標準的道德來指責,這是多麼缺乏誠意的笑容,他們不會感到服氣的,甚至反駁你太獨斷和偏見,沒能讀出笑容背後的深意。這個大叔就是這理論的擁護者。
「噢,包桑,你來了!」萬克強向這個叫包桑的男子招手,示意他同桌陪坐一下。
杰德看見包桑來了,立刻站起來,做出讓座的動作,向同桌的三人說,「你們慢慢談,我該回到自己的座位了,不可讓我的客戶等太久。塞先生的事咱們就這麼說定。那些事情搞到以後,馬上跟我聯繫一下,咱們決定個日子出發。各位,我先失陪了。」話畢,杰德正要轉身離走,萬克強說道,「老德,有勞你費心安排了。咱們以後再聊。」杰德說了聲不客氣,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上。
就這樣,四個圍桌密商的四個男人,有一個人退出,加入一個新的成員。確切地說,包桑也是帝女花的常客,凡是這裡的常客他幾乎都認識,而且以他的職業屬性,他早就掌握住每個常客的身體特徵和習慣。所以,照理說他和杰德應該打過照面,只是彼此尚未敞開心扉而已。這有點像豬籠草與果蠅之間的關係,有時候關係對調互有勝負,很難說誰占據了上風。然而,有一點確定無疑的,杰德是來自大陸的茶葉商販,而這附近一帶則是包桑活動的地盤,在地緣社會關係網絡上,他占有絕對的主場優勢。不過,這單幫客是個識時務的行家,很能掌握進退的時刻。
「他叫做老德?」包桑向萬克強問道,可是沒等骨董商回答就自行坐下了,一副熟門熟路的樣子。這裡如同他另外搭建的鳥窩。
「嗯,有些事情需要他來幫忙,」萬克強補充說道,「在台灣,遇到雜七雜八的麻煩,總能找到有力人士解危,但是到了大陸,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大陸有十幾億人口,幅員遼闊得驚人,沒有當地的朋友帶路,做什麼事情肯定要吃虧。」
「萬桑,這位是你的朋友吧?你怎麼不介紹一下?」包桑的說法有點明知故問。
「不好意思,你不說我都忘了,都怪我剛才談得太盡興了,忘記重要的事情還沒辦妥呢。來,這位是前途看好的塞先生,是一家中型旅館的經營者。」
包桑向塞林傑微笑著,屬於皮笑肉不笑的那種。不過,塞林傑似乎不以為意,他在乎的是貸款資金趕快撥下來,才能付諸真正的行動。其餘的事情一概不予關心。
「你好,我叫包天笑,」說著,他立刻從長褲後方右邊的口袋,取出了一只皮夾,在小小的夾層找了幾回,好不容易抽出了一張名片,將它遞向塞林傑的面前。
塞林傑接過名片,仔細打量了一下,名片上的頭銜和投資很耐尋味,有土地開發啦、砂石承包啦、銀行融資業務等等。他還發現,這張名片附著濃烈的香煙味,已經發皺變得泛黃,想必放置得有些年份了。現在,他拿到這張名片,算是幸運之星,抑或是相見恨晚?
「你好,我叫塞林傑。」
「你也想跟萬桑學習做骨董生意嗎?」包天笑問道,他的嗓音低沉很特別,有點像拿著紙杯講話似的。
正游向華麗的彼岸
「我對於骨董和收藏品有點興趣,就是沒有這方面的才能,頂多買點小物件賞玩。上次,我剛好路過萬先生的洛陽閣,一時好奇到店內參觀。萬先生正巧在沖泡陳年普洱茶,招待我一起品嚐了幾杯。飲下陳年普洱餅茶,我覺得口腔立刻生津回甘,真是神奇的茶飲料!聊著聊著,萬先生知道我的困境,於是向我建議,這個時機想發點小財的話,不妨到大陸看看。譬如,定製大批普洱茶,運回台灣銷售,到時候放個風聲出去,就有買家找上門。這其中的差價利潤,可不得了。」
「沒錯。萬桑向來眼光獨到,據我所知,他所投資的項目沒有不賺錢的,簡直讓業界同行羨慕死了。僅只這一點,萬桑就應該請我喝啤酒了。」說罷,包天笑轉身過去,逕自向愛麗思點了兩瓶啤酒,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看到這種情形,白雲飛不由得向萬克強投去無奈的微笑,意思是說,誰碰到包天笑這種人,那個人就得變成啤酒贊助商。因為你必須有體恤之心,體諒他整天在外的辛勞,不論刮風下雨的日子,一直守在路口拉客招攬生意。這是平常人做不來的行當。所以,這時候他藉機索來兩瓶啤酒潤喉,不必跟他計較,不如轉念一想,把它當成社會救濟的善行,像那些財庫飽滿的寺廟,每逢初一十五日,給遊民們發放炒麵盒飯一樣。
從另外的角度來看,萬克強是最了解包天笑的人,因為萬克強在女人方面需要他居中幫忙,同時享受著某些優惠。現在,他只是請包天笑喝兩瓶啤酒充當公關費,的確是很划得來。於是,萬克強乾脆來個逆向操作,向正在收拾杯盤的愛麗思說,待會兒,給我一瓶紹興酒!愛麗思連說了兩次好,端著盛著杯盤碗碟的托盤走入廚房裡。
「來,我敬你,塞桑,」包天笑碰到或認識新朋友,喜歡用日本式的稱呼,在對方姓氏後面加上「桑」字,以表示禮貌和尊重。話音剛落,他拿起萬克強面前尚未喝完的啤酒,仰頭一飲而盡。「乾杯!」
「謝謝!乾杯!」塞林傑受到豪情的誘發,也開始變得豪氣干雲,「下次,有機會的話,歡迎包桑來我們旅館指導一下,看看業績能否直線上升。」
「沒問題。另日,我去你們旅館坐坐,順便看看陽宅風水,情況嚴重的話,還得配合宮廟的道士來祭改。」
「噢,你也會看風水嗎?」塞林傑對包天笑問道。
「事實上,我很早就拜師學藝了,還幫人家看過幾處地理風水,收取紅包謝禮,後來我轉行到有趣的事業上,將那些生財工具送給同行了。不過,別看我這樣喝酒,我可是寶刀未老,隨時都能披掛上陣呢。」說完,他打了一個響嗝,朝塞林傑的臉面噴薄而去。
與其說,塞林傑來不及閃躲這股酒氣的攻擊,不如說,他不便做出這個動作,以免得傷及包天笑的自尊心。然而,在那當下,他的確承受著酒氣的侵入,還明顯察覺到他嘴裡的怪味道,很像體內臟器敗壞溢發出來的味道。進一步地說,包天笑的外形和穿著很怪異,他的頭髮抹著重重的髮油,整個往梳前髮豎著,如倒捲般的海浪一樣,乍看去,豬肝色的臉部肌肉有點浮腫,鼻毛太長沒有剪除,悄然地從鼻孔裡探了出來。他穿著深藍色西裝上衣和粉紅襯衫,粗大的脖子繫著金黃色的領帶,儼然魔術表演的人,又像是一名過氣的老演員,失去掌聲和舞台的鼓勵。
「聽說,每個生意人和演藝人員,都非常相信風水方位,這種說法可信嗎?」塞林傑對這個話題感興趣,也把包天笑視同演員看待,因而借題探問道。
「什麼事情都可懷疑,唯獨風水地理不可不信,」說著,包天笑又倒了一杯啤酒,逕自喝了起來,如同喉嚨乾涸太久了,必須盡快拯救舌頭一樣,否則他就無法順暢地開講後續的劇目。
「你碰過有趣的事例嗎?」
「有,當然有。你想知道嗎?」
塞林傑點了點頭,用微笑代替有聲的回答。畢竟,如果他大聲回答,那聲音一定會傳進其他客人的耳裡,惹來他們在心中暗自竊笑,這小子是個傻瓜蛋,來到帝女花咖啡廳即要談生意,進行各種投資交易的協商,怎能扯到這種有孔無榫的雜事呢?基於這樣的顧忌,他探向包天笑的耳邊,低聲問道,「你能不能舉個具體的事例?說不定,以後對我的投資案很有幫助。」
包天笑清了清嗓子,像說書人一樣,開始說道。他說,由於工作和談生意的關係,他經常進出時代廣場大樓,所以,跟大樓管理員們非常熟悉。例如,哪個管理員幹不到三個月,就三不五時翹班溜出去喝酒,遭住戶檢舉被炒了魷魚,流落到地公廟附近當遊民;值深夜班的管理員,閒著發慌在崗亭裡飲酒作樂,住戶認為這是怠忽職守,向保全公司投訴,隔天以後,那個管理員也走人了。儘管如此,在大樓保全人員當中,盡職的仍然是占多數。他認識一名保全名叫嚴井天,與他同樣名字中有個「天」字。這象徵著他們與生俱來有著某種特殊的緣份,必定在現世當中以某種形式見面。
果真如此。某個晚間,他帶客人進入時廣場大樓之後,搭乘電梯來到樓下,經過樹影搖曳的中庭,快要經過崗亭的時候,他發現嚴井天的情況有點怪異,於是,不由得停下腳步,隔著玻璃窗門對嚴井天問道:
「你怎麼啦?」
「不知怎麼搞的,我的眼睛眨個不停,視力變得模糊了,我懷疑自己的兩隻眼睛,是不是快瞎掉了呢!」
「你沒去眼科診所檢查?」
「當然有。我已經看過好多次了,拿了藥水,點了藥膏,」嚴井天嘆了口氣,「坦白說,都沒有見效啊!」
「……」包天笑沉思了一下,「據我所知,台灣的眼科醫術很高明,應該可以治好你的眼疾,除非你不走運。」
聽到不走運這三個字,嚴井天莫名地緊張了起來,眨眼次數更頻繁了,血壓猛然飆升起來,把他的腦門撞得咚咚響。
「為什麼?」
「除非你碰到的是庸醫,病患們俗稱的光明終結者。」
「光明終結者?」嚴井天滿臉困惑,卻很想知道其中的原由。
「簡單講,患者上門求診,原本兩隻眼睛好好的,但是有些綜合醫院的眼科醫生,為了向健保局多申請手術費用,便慫恿患者開刀。在這種情況下,患者當然會接受開刀手術,但問題是……」
「包桑,快說!這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是,那個醫生開刀技術很差,結果手術失敗了。」說書人包天笑停頓了一下,似乎等著嚴井天提問,這樣方能突顯他演說的功力。
「……手術失敗會怎樣?」
「怎麼樣?問題可大了!等你醒來的時候,兩隻眼睛都看不見了。換句話說,那個倒楣的庸醫開刀失誤,一下子結束了你的光明。難道這樣還不夠恐怖嗎?」
嚴井天倒吸了一口冷氣,嚇得整個身體往後退,使得他坐著有滑輪的辦公椅,把那只置於崗亭角落的白鐵垃圾筒撞出了響聲。
「我才不要找那種蹩腳的醫生呢。」嚴井天嘟嚷著。
「對了,我問你,今年幾歲了?」
「我?」嚴井天吞了一下口水,提防似地問道,「怎麼啦?我的眼睛有毛病,跟我的年紀相關嗎?」
「嗯,應該有關係。說吧,相信我。」
嚴井天遲疑了一下,要不要報出自己的年齡,因為許多管理員的背景很複雜,有的是還不出債務的卡奴,有的是商場失敗的破落戶,有的是急卻找到生活避風港的更生人。更具體地說,如果這時候有不肖人士,得知大樓管理員的背景資料,而進行某種利用和操控的話,那麼自報來歷這個行為,豈不是給弱勢者的自己,帶來不確定的災難嗎?(未完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