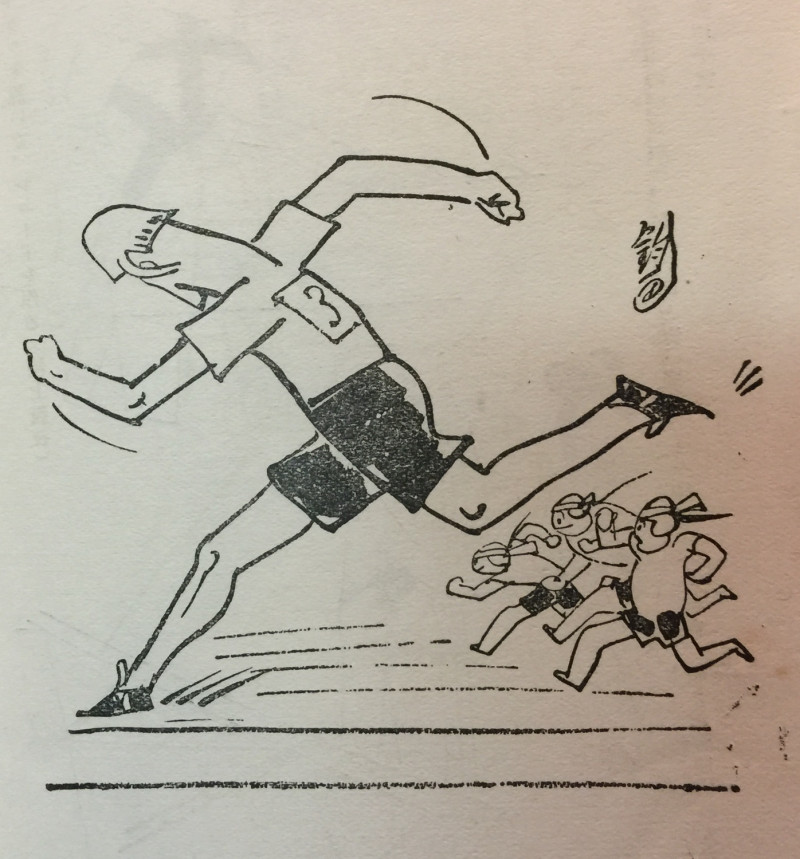引言: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四章 危險關係的發明
在那裡悲憫是一種傷害
全站首選:更新》第4架美軍F-15E戰機墜毀? 傳在伊朗上空被擊落 美軍:假訊息
畫家格雷特吳聽著賀蒙特回述他的風流韻事,忽然間,一種無以名狀的感傷情緒,如惡浪般向他撲捲過來。入獄之前,他在藝術學院裡擔任講師,曾經有過一段耀眼的青春。儘管如此,他愛情方面卻是個失敗者。他追求的女性並不欣賞謬思的畫筆,而是愛上了左派作家赫大頭。這個結果給他很大的挫折。他和赫大頭都是同時代人,共同參加極左傾向的讀書會,各自被判了五年徒刑。出獄之後,據說赫大頭得到對岸共產黨的資金奧援,繼續寫著思想僵固的政治小說,擴大自己的思想影響力,創辦雜誌鼓動社會運動。這種操作相當成功,赫大頭的名聲越來越響亮,不到幾年的工夫,赫大頭在新聞和文壇上被奉為神明,狂熱的信徒尊稱他是中國臺灣作家的良心,人道主義的代表性作家,連日本左翼陣營和有日本共產黨背景的教授們都來敲邊鼓,形成了一種變種的共產國際的思想大串連。而格雷特吳的命運就坎坷多了。剛開始,他經由情敵赫大頭的介紹,在一家畫廊擔任經理的職務,可是,這份差事沒能維持太久,特務人員就找上門了。他們採取如影隨形的跟監方式,不斷對他施加心理恐懼,目的即是要切斷他與社會關係的連結,逼迫他退回到孤獨的洞穴裡。
「老弟,你豔福不淺啊,女人主動找你上床,向你尋求慰藉,」格雷特吳坦白自己的想法,「我聽得好羨慕。對了,那個叫做貝綺娜的女人,為什麼說自己是不幸的人?」
「噢,」依照賀蒙特的個性來說,他很想立刻就說明全局,但是他覺得一時半刻,是無法說得完整的,於是先概述結論,「其實,這不是什麼新聞,媒體早就大肆報導了。有錢的台商在大陸包養女人,沒錢的台灣幹部則合租一個女人,輪流共同使用。」
當前熱搜:越射越少! 伊朗導彈不再是威脅了? 以色列宣佈8日重新開放領空
「什麼共同使用?」
賀蒙特露出神秘的微笑,認為格雷特吳終歸是單純的藝術家,不懂得兩岸探親開放以及開放投資以後,情勢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撇開經濟發展不說,臺灣男人長期在大陸經商工作,因耐不住寂寞的啃蝕,最多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包養女人解決性飢渴的問題,經濟條件稍次的臺灣幹部們,則採取合租共同的概念。
「也就是說,他們共同出錢合租一個女人來發洩積壓的性慾。而且,她們通常是工廠內的女工。下班以後,她到臺灣幹部宿舍的房間裡報到,幹部按照排定時間輪流使用,用完即迅速閃人。聽說這種互蒙其利的性交易,他們事前都經過協商和議價的,沒有半點不公平,才能長時間達成微妙的平衡。」
「……這事情超乎我的想像啊,」格雷特吳發出驚嘆的聲音,「你的意思是,貝綺娜的丈夫在大陸包養女人?」
「沒錯。」
「所以,貝綺娜不甘心,也想以牙還牙報復丈夫嗎?」
「從結論上來說,可以這樣解釋。事實上,背後還牽涉到複雜的因素,我竟然在他們的名單之中……。」
「咦?莫非是貝綺娜的丈夫向你提告?」
「當然不是,否則我這起豔遇事件就要提前結束了。按照貝綺娜的說法,當時,她丈夫自己深陷在女人堆中了,除了要求她對外借款之外,對她一概沒有興趣不關心。」
聽著賀蒙特的描述,格雷特吳回憶著昔日與瑪麗亞幽會的日子。中午時分,瑪麗亞坐在他簡陋的居所裡,有時候供他素描,有時候全身赤裸,作為藝術家筆下的人體模特兒。基於保護自己和防止監視之眼,他把臨街的玻璃窗全貼上舊報紙,但是遇到豔陽天,強烈的光線仍然會慷慨地照射進來,將暗淡的房子照得明亮起來,在那時刻,裸體著的瑪麗亞同樣沐浴在這片明亮的領域裡,使他認為眼前的瑪麗亞具有現實的和神聖的雙重特性,因為他按捺不住愛慾的時候,不由分說就扔下畫筆,擁抱著瑪麗亞進入那張簡陋的眠床上,明知在激情的燃燒中,只會讓生命蠟燭般的芯線燒得更短。
「格雷特吳,我再說個有趣的插曲。」賀蒙特補充說道,使得沉浸在昔日憂傷中的畫家,忽然醒悟了過來。
「是什麼插曲?」
「我想,不經常進出賓館開房間的人,大概聽不到這種奇妙的聲音。」
「賓館會傳出美妙的聲音?哎,老弟,別故弄玄虛了,快說出來吧。」
「你知道的,剛開始,我跟貝綺娜在床上聊了很久,而且聊得很盡量,彼此都放鬆下來。後來,我禁不住貝綺娜的愛撫和挑逗,正要翻身插進去的時候,同樓層的某個房間,傳來了輕碰板壁的聲響,而且很有節奏性。在那之後,即傳來類似女人的哀吟聲,仔細一聽,我判斷應該是女人進入高潮時的歡愉聲音。」
「這有什麼不妥嗎?」格雷特吳追問道。
「沒什麼不妥。一般而言,那聲音是一種誘惑,一種致命性的勾引,讓男人更熱衷進入那種狀態裡。可是,不知怎的,我竟然在這緊要關頭鳴金收兵了。那時候,滂沱大雨的聲響,反而失去遮蔽的力量。」
「我不信,在這種時候,男人絕不可能退場出來的。難道這不是絕佳的機會嗎?」
賀蒙特沒有即時回答,似乎在尋恰當的辭彙,以便說明當時的情境。他雖然是個詩人,但是面對經驗世界中的情感表達的時候,往往是以詞窮收場。在這時候,他似乎不得不接受新康德主義的說法:直觀的主客體區別是具有欺騙性的,需要採取行動加以揚棄。客觀世界和主觀意識不是辯證的等價物;客觀世界由源於主觀意識的行動所決定的。由於個人意識創造了世界或創造了理解世界的範疇,這樣的活動將會產生價值的創造。換句話說,他們認為意識的主要作用是判斷價值,因為這個世界實際上是個什麼樣子從來都不能被我們所了解。在道德方面也是。道德的發端非常神秘,它是被有意或憑直覺創造的行為模式,並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採納。經過代代的相傳,道德變成了自覺的強制性內容,成了慣例,努力地控制個體。在面對重大社會的問題時,個體沒有任何可替代的選擇。
「這的確絕佳的機會,」賀蒙特繼續說道,「不過,後來我還是履行承諾,滿足貝綺娜的願望。」
「每個星期三次,每次三個鐘頭?」
「嗯,那時候我的體能還不錯,終究挺過來了。正因為我守信用挺住了,才得以知道其他的祕密事件。」
「祕密事件?」也許賀蒙特吳患有坐牢創傷後遺症,一聽到與思想拑制相關的措詞,他就如受傷的禽鳥似地驚嚇起來,以為這敏感性的詞彙,隨時會向他展開攻擊,而為了證實它對人是無害的,所以他非問個歸根究底不可。
真相背後的天坑
賀蒙特說,他履行了男子漢的承諾,並為貝綺娜這個不幸的女人,努力添上些許希望的色彩。有一天,貝綺娜說有重要的事情告訴他,請他來旅館的房間。他以為這次又要撥弄雲雨,同樣準時抵達,但是情況卻與他所想的恰恰相反。他進入房間裡,貝綺娜並沒立刻寬衣解帶,或者脫得一絲不掛,而是如平常那樣,穿戴整齊坐在床沿上,一副談論正事的模樣。
「賀先生,我要向你道歉,否則我會過意不去的。」
「咦?」賀蒙特摸不著頭緒問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沒有做錯事情,為什麼要向我道歉呢?」
「我接近你是有任務的。」貝綺娜說。
「任務?」賀蒙特聲調並不拔高,聽得出驚訝的成分,但是旋即恢復平靜,「在臺灣詩壇上,我是個默默無聞的詩人,沒寫過重要的作品,像我這樣的平凡人,值得有關單位派人『觀察』嗎?」
「不瞞你說,我住在旅館這陣子,仔細讀過你的詩集,對你的思想有某種程度的了解。你那本自費出版的詩集,市面上已很難找到,我費了好大的功夫,才在板橋市的小舊書店購得。」
賀蒙特不由得喑自吃驚起來,貝綺娜真是厲害,竟然有辦法找出這部詩集來。當初,他自費花了五萬元,找了認識的小型印刷廠,印了一千本。為了賺回付出的成本,他努力四處推銷,找過親朋好友幫忙,好不容易才售出一百本左右,餘下九百冊,就堆疊在自家的公寓裡。數年以後,他家裡的空間實在放不下了,必須做出妥善的清理。他想了想,自留十本左右,當作樣書紀念,其餘的八百餘冊,只好忍痛地送到資源回收場,以公斤計重地處理掉,一種不得已對於詩集的最終解決方式。又或許,資源回收場的老闆,原本就是個大善人,他閱盡送來這裡進行最終解決的東西,舉凡各式各樣的破銅爛鐵,見識過任何形式的廢紙書冊,一眼就能看出它們有無價值,迅速判斷這些雜物的來源。想必在那個老闆的慧眼之下,他覺得把這些詩集全部送進廠剁成泥漿,未免太可惜了,不如讓它轉換管道往舊書店流通,以等待有緣的讀者。所以,這個角度設想的話,回收場老闆的最終解決方案是:將他的詩集低價賣給了舊書店,用這種方式保存詩集最後的尊嚴。
「你是在哪家舊書店購買的?」賀蒙特問道。
「洛陽閣書店。」
「洛陽閣?除了舊書之外,店裡是否有許多骨董和字畫,在玻璃櫥窗裡,擺著宜興茶壺……」
「嗯,我就是在那裡,找到你絕版的詩集。不過,我對骨董不感興趣,那種東西多半是假貨,烏七八黑看不到底的,再多的錢都填不滿。」
「你怎會知道洛陽閣呢?沒有專人介紹的話,不可能找到那裡,因為他的主力商品是骨董文物,過時泛舊的詩集不值錢。」
「說的沒錯。我是透過一個在大陸做生意的台商,聯繫上洛陽閣的老闆萬克強。我不想浪費時間,直接挑明要他找來你的詩集。」
「可是,你們並不熟識,」賀蒙特沉吟了一下,打破好奇問道,「萬克強為什麼非得接下這訂單?何況販售我的舊詩集,根本沒有賺頭。」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談到嚴肅的話題,貝綺娜仍然口氣溫和,與剛性率直的賀蒙特形成強烈的對比。事情發展到現在,她似乎不想再隱瞞事實了,繼續說道,「因為我手中握有萬克強的把柄。屬於那種不大不小的把柄……」
賀蒙特說,貝小姐,我想知道事情的經過,你再清楚說明一下,萬克強有什麼把柄落在你的手裡?他的把柄與我的詩集有什麼相關呢?」
「好吧,事情是這樣的。萬克強是個精明的生意人,眼光非常獨到,在八○年代後期,他從香港買進了不少宜興古壺,而且多半是有名家題款的作品。他知道投資這些宜興古壺,將來必定能賺到大錢,多收幾個古壺,就能多出幾疊人民幣來。後來,為了更精準掌握大陸的買方動向,他前進到大陸內地,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市場調查。結果,如你們男人所知道的……」說到這裡,貝綺娜突然打住了,像是碰觸到不愉快的往事似的,但是很快地又恢復過來了。
「萬克強在大陸嫖妓嗎?要不就是包養女人?」
「從女人的立場來看,這兩個罪名是無法寬恕的。男人成天在外面吃野味,撇下家裡的妻子不管,這種道理行得通嗎?」貝綺娜說道,「不過,這終究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要不要對丈夫的不忠寬恕,是由女人來決定的。也許,有一種恐怖的懲罰,比寬恕更具震撼效果。」
「就是你說的『把柄』嗎?」
「對。萬克強很有商業手腕,他很快就找到大陸的買家,陸陸續續售出他所珍藏的宜興古壺,所以賺了不少錢。剛開始,為了慎重起見,他總是坐飛機到大陸親自送貨,與買家當面點貨交易。後來,經過精算成本和利潤,他與買家商量,改用空運的方式寄出,這樣雙方都可節省進出貨的成本,應該是兩全其美的好辦法。不過,不知是不是萬克強缺少政治正確的敏感度,或者無意間的疏忽。」
「怎麼啦?」
「根據我得到的消息,那一次,萬克強犯了致命性的錯誤,前幾次,他都是用《超越宇宙大團結時報》舊報紙作為包材,以避免宜興古壺受到意外的碰撞或損壞。確切地說,在郵寄物品裡使用《超越宇宙大團結時報》舊報紙包裹,不但不成問題,還能受到大陸官方的首肯。但是,萬克強卻用《自由台灣光明報》的舊報紙,包裹著數只價格不菲的古壺。這個做法等於是給自己招來麻煩,而且是天大的麻煩!」
「噢,原來如此。」賀蒙特恍然大悟地說道。
「賀先生多久沒去『洛陽閣』了?」
「……大概一年多吧。」
「難怪你沒發現呢,上次我到『洛陽閣』取書的時候,恰巧看見萬克強小心翼翼地包裹宜興古壺,似乎正準備出貨。我仔細觀察了一下,堆著店內牆角的舊報紙,清一色都是《超越宇宙大團結時報》,完全看不見《自由台灣光明報》的一張半紙。顯然的,萬克強吃了苦頭,終於學會政治正確的要領了。」
「所以,萬克強就成了政治肉票嗎?」
「可以這麼說。反正,只有人掐住這一點,萬克強就不能自由呼吸了。不過,掐死他沒有太大的意義,不如充分運用他廣闊的人脈。」
「這麼說來,你向萬克強購買我的詩集,他一定以不敢高價售出吧?」
「嗯,基於這種祕密協定,萬克強原本要免買贈送給我,但是我不喜歡佔人便宜,白吃白拿別人的東西,哪怕是白吃一碗餛飩湯,都會覺得無比羞恥的。這種小氣的行為,只會貶低自己的人格。所以我自然是要付錢的,絕不讓萬克強認為,我是趁機從他身上撈到好處。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把自己的不幸,拋向已經不幸和無辜的人身上,儘管他原本就是個投機客或倒楣鬼。」(未完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