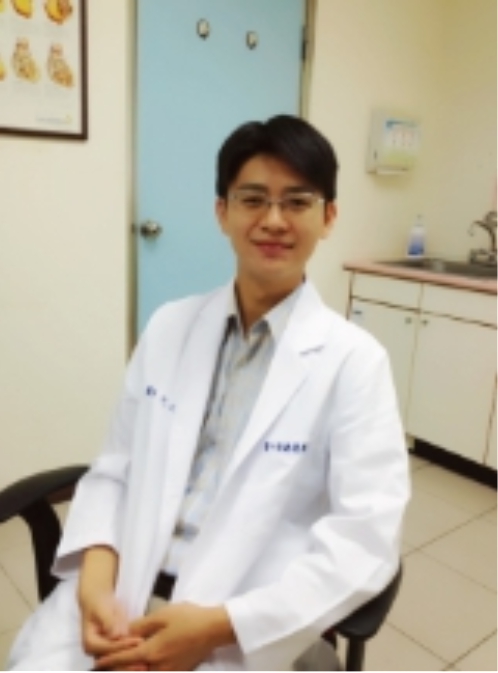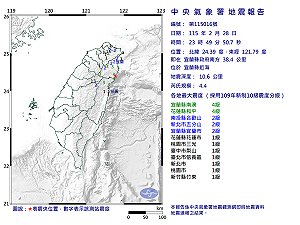接受法院委託協助精神鑑定「台鐵殺警案」鄭姓嫌犯的台中榮總嘉義分院身心科醫師沈正哲,秉持自身專業鑑定作為法官判決參考,仍遭大批網友出征留言謾罵,甚至波及院方。沈正哲稍早再發表聲明,強調自己並未說過「我是權威」、「你們要鑑定幾次都是我在鑑定」等話語,自己依照所學做出鑑定,並沒有做錯,嫌犯會被判怎樣的刑責,並非他能決定。
沈正哲表示,做出判決的是法律,如果多數民眾認為這樣的法律不合理,請提倡修改,而非只是謾罵醫師,「發生不幸的事情,我相信沒有人願意看見」,精神醫療的困境與病患的處置細節,才是更需要被關注的。
全站首選:美以聯手轟伊朗!中國外交部發聲:立即停火、恢復談判
沈正哲醫師聲明全文如下:
原先我並不想針對任何網路上的謾罵做出任何回應,因為我怎麼說,總還是會有人挑毛病來指責謾罵,但是,我不想我的家人或朋友再因為此事擔心,或者與網友爭論,所以我選擇說明一次。
首先,我想聲明的是,我從未提過「我是權威」或「你們要鑑定幾次都是我在鑑定」這樣的話語,法庭上的對話都有錄音為證,且有許多人在場,絕對能證明我並未說過這樣的話,今天家屬對於判決無法接受,可能因為情緒不滿,想找出口發洩,而向記者提出這樣的說法,但卻不是事實。我與被害者的家屬 (父親)僅在出庭時中間的數分鐘休息時間短暫說過幾句話,當時是家屬委託的律師帶著父親來向我打招呼,當下我告訴父親我知道你們很難過,請他們也要保重身體,父親告訴我嫌犯是裝病的,我回應他我會依照我的所學來做判斷,之後庭務人員告知我休息只有分鐘中,提醒我要去喝水及上洗手間,我與父親的會談便結束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對他有任何不禮貌之處,更別提嗆聲他「我是權威」或「你們要鑑定幾次都是我在鑑定」這樣的話語,在這段談話的之前或之後我與家屬都未曾再見面過。再者,只要法院安排二次鑑定,一定是安排其他醫院的醫師,絕對不會是同一人,做過許多鑑定案件的我,怎麼可能會不知道而又說出「你們要鑑定幾次都是我在鑑定」這樣的話語。
全站首選:川普下令「史詩怒火行動」轟伊朗 國會炸鍋:未經授權開戰?
去年10月份我接受法院委託接下本案鑑定,12月份我由媒體得知檢察官在開庭時對於我的鑑定提出質疑,而檢察官的理由是認為我所在的醫院不是醫學中心,所以我做的鑑定不專業,另外,檢察官認為我鑑定只用了六天就完成報告,認定我草率,看到媒體報導的當下,我內心覺得不服氣,事實上,台灣目前多數精神鑑定都不是在醫學中心完成,以嘉義為例,嘉義地區就沒有醫學中心,難道過去這麼多年在嘉義地區完成的鑑定都不專業嗎?且自我從事鑑定工作以來,做過的鑑定數量超過百件,如果今天這個案件因為我工作的醫院就認為我不專業,那過去我所做過的百件鑑定又算什麼,至於為什麼只用六天就完成鑑定報告,是因為我認為這是重大刑事案件,希望能盡快完成報告讓法院及早完成審判,於是我才每天加班完成報告,再者,過去只要我超過兩周未完成報告,法院便會來電催促要盡快完成,而如今我加班完成報告,卻被檢察官拿來作為攻擊我的理由。我並非認為專業不能接受質疑,但必須提出合理的依據,如果檢察官是依照我鑑定報告有錯誤的地方提出質疑,我願意平心靜氣說明,但今天檢察官只因我工作的醫院及完成報告的天數就認定我不專業及草率,我無法接受。
今年3月份法院傳喚我出庭作證,當天我一個人接受檢察官、法官及律師的詢問4個小時,光檢察官一個人就詢問我2個小時,而因為我上述所講原因,我的確在一開始與檢察官針鋒相對,我當下有向檢察官表示他不尊重專業,我也當庭表示既然這是個社會關注的案件,我並不反對安排其他醫師鑑定,但我無法接受他用我不專業以及草率來做為理由,尤其在媒體報導後,網友更是直接攻擊我及我的醫院。開庭的中場休息期間,檢察官向我表示歉意,說法庭上的攻防就是如此,他必須提出理由讓法官願意再指派另一家醫院做鑑定,我回應我知道他是在做他的工作,但不應該提出這樣不正確的指控。
而因為檢察官先前對我專業度的質疑,法官提問的一開始就要我說明我的學經歷,於是我說我是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後來在中正大學拿到博士學位,擔任主治醫師八年,做過上百件的鑑定案件,在資歷上絕對沒有問題,後來法官再問為什麼醫院有這麼多位精神科醫師,是由我來做鑑定,我表示也許是因為我優秀且有經驗,所以這樣複雜的案件要我來做,且做鑑定又要承受這麼大的輿論壓力,多數精神科醫師都不願意做的,而也許這就是家屬 (父親) 後來理解的「我是權威」,但即使在其他情境下,我都從未說過「我是權威」這樣的話。
擔任此案的鑑定醫師,我秉持自己所學做判斷,在鑑定業務上,我的工作是判定嫌犯是否有精神疾病,以及他的犯行是否與精神疾病相關,試問,我哪裡做錯?當網友質疑我不同情家屬,但如果我因為同情就影響我的判斷,只為了順應所謂的民意與社會期待,那其實往後的鑑定都不需要找醫師做,只需要辦網路投票即可,我想沒有精神科醫師喜歡做這樣的工作。我依照我的專業做鑑定,至於嫌犯會被判怎樣的刑責則不是我能決定的,而依照台灣的法律,因精神疾病而犯行可以減刑或免刑,如果多數民眾認為這樣的法律不合理,請提倡修改台灣的法律,而非只是謾罵醫師。
擔任精神科醫師的這幾年,我很努力地希望因為我的治療,能讓個案和他的家屬生活獲得改善,同時減輕因為個案的精神疾病對家庭及社會造成的困擾與負擔,發生不幸的事情,我相信沒有人願意看見,精神醫療的困境與病患的處置細節 (如強制住院等)才是更需要被關注的,也才真正能預防這樣的遺憾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