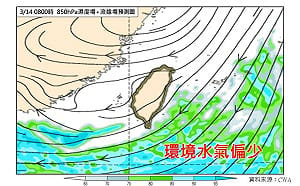鄭南榕先生:
這是一封寄到天堂到信,不知你能否收到?
當前熱搜:美軍轟炸伊朗石油樞紐「哈爾克島」川普警告:不排除打擊石油設施
你知道嗎,在你殉道十三周年之後,你的名為「自由之翼」的紀念墓園落成了。你的生命終止在一九八九年,同一年,彼岸的中國,無數學生和市民死於共產黨軍隊的屠殺。在四川成都郊區的一個小鎮上,十六歲的我在收音機前聽到急促的槍聲,由此提前完成了成年禮。我發誓將一生獻給尋求和捍衛自由的事業。不過,那時,我還不知道你的故事。
當年,小小的《自由時報》編輯部,你是創辦人和總經理,李敖是總監,陳水扁是社長,你們三個人一起在極端不自由的時代「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你離開這個世界之後,那兩個曾與你並肩作戰的人,一步步地走向當年理想的反面:或為名所累,或為權所困,可悲地淪為自由的反面。
歷史無情亦有情。學者姚人多在《鄭南榕、李敖與陳水扁的自由時代》一文中回顧説,鄭南榕的死開啟一個臺灣主體意識成為主流的年代。如今,即使你還活著,你也勢必要與李敖分道揚鑣。陳水扁則是你殉道的最大受益人,在臺灣主體意識的強大推力下,當選兩次總統。不過,如果你還在這個世界上,阿扁當選總統之日,就是你們割蓆之時。
全站首選:管仁健觀點》小草為何總是比柯傅堯更孝順?
曾經一起在不自由的時代裡共同努力的夥伴,在自由年代卻像走到了交叉路口,往不同方向各奔東西。你們三個人的“自由時代”見證了過去二十年臺灣的巨變,有點諷刺,有點唏噓。當年,因著共同的敵人,你們併肩作戰;如今,敵人的消失,使得有人“拔劍四顧心茫然”,有人甚至把持不住而釋放了自己的心魔。自由,不是一道精美的飯後甜點;自由,是一把檢驗人格高下的精準的標尺。自由,讓英雄的歸英雄,讓小丑的歸小丑。
你如春蠶吐絲,你如鳳凰涅槃
又過了十一年後的二零一三年,我從中國流亡到美國,然後從美國飛往臺灣,這才有機會到你的墓園來憑弔。
遠遠地,我就看見三米高的「自由之翼」銅雕,這是鄭南榕基金會特地請旅奧地利雕塑家林文德創作的。林文德與你同樣出生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一九四七年,曾是你主編的《自由時代》週刊的讀者。林文德本人曾是「黑名單」上的人物,作為一名美術老師,因為太喜歡跟學生分享「自由」這個「敏感」詞語,被迫辭去教職,遠赴歐洲深造。
「自由之翼」銅雕的造型,是林文德對你的詮釋——這個銅雕代表著由生命昇華成為自由的意涵。經過一年的構思與三個月的實際製造,這尊銅雕反復修改,成爲完美的成品。簡介上寫著:「筆直向天,形狀似鳥,代表自由。內部洞開,代表開放。光滑的表面,期望有順遂的未來。」
為了讓遊人親近「自由之翼」,感受其傳達出來的意像,林文德在銅雕中間,設計出一個高約兩米、寬約六十釐米的中空,讓人可以由底下穿越而過。僅容一人穿過的寬度,是希望讓人在穿過時直接碰觸到銅雕,有一種身體的接觸與心靈的互動。我走在其中,仿佛穿越時空,與你握手。有好山好水、好國好民伴你,你可安息於此。
在墓園台階盡頭,有一幅你的浮雕頭像,也是林文德的作品。浮雕上的你,有如本人一樣大小,頭上綁著「新國家運動」的布條。臉側向東方,眼睛看到的地方,正是你出生的宜蘭平原的方向。墓座上「焚而不毀」四個字,是對你的一生最凝煉的概括。
你靦腆,你單純,你是書生;你堅決,你頑強,你又是戰士。你的自我定位是:「思想家分兩種,一種是言論思想家,只能坐而言;一種是行動思想家,願意起而行。我就是一個行動思想家。」為了這片土地早日自由,你不惜向死而生,如詩人林佛兒筆下的鹽——「我們雖然粗糙,雖然卑微/但我們堅持/是一群永恆的自由顆粒/在貧瘠的土地上發光/鹽啊,鹽啊。」
詩人林超然在詩歌《鄭南榕的獨白》中,模擬你的口吻寫道:「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自由/我燃燒自己/為照亮這土地/我燃燒自己/為溫暖你們,我的兄弟/我燃燒自己/為了喚醒你們,我的同胞/你們,醒了嗎?//我立在這美麗島上,拒絕倒下。」是的,對你來說,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中丹麥王子「活著,還是死去」的追問,並不是一個問題;惟有「自由,還是不自由」才是一個問題。
從古至今,華人文化是以「活著」為旨歸的文化,從中國作家余華的小說《活著》到張藝謀的電影《活著》,都是對這種文化淋漓盡致的闡釋:只要能活著,即便沒有自由,即便當奴隸,甚至淪為一條狗,也要忍氣吞聲、苟且偷生。所謂「好死不如賴活」,所謂「甯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就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
奴才總覺得不願意做奴才的人是叛國者。你曾寫道:「在這種消極的『集體等待』心理之下,一般人民雖然滿腹牢騷,卻冷漠成性;國民黨也可以在民怨沸騰之中享盡獨裁政權的尊榮;至於最基調的『社會正義』,則在朝野一致的默契下,被判處無期徒刑。於是,臺灣人民在『等待』的歲月裡,不僅落得傷痕累累,而且久病纏身;敢於犧牲行動的仁人志士,結果還是坐失改革的大好良機。」這句話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所寫,那時,你正面對國家機器「涉嫌叛亂」的指控。「愛情誠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從蘇格拉底到索爾仁尼琴,從譚嗣同到秋瑾,你們就這樣一路走來,長歌當哭,白衣飄飄。
你知道嗎,多少次,我有這樣的想像:如果你活下來,看到今天臺灣社會在通往自由的路途上大步流星地前行,那該有多好。當然,威權時代的慣性依然在戕害著社會肌體,不公不義的事件仍舊在發生。那麽,你會繼續撰寫那些如匕首和投槍一般的文章,甚至再次率領民眾走上街頭為自由與公義而呼喊嗎?
你如南國的大榕樹,迎風而立
那個時刻,離開,是你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抉擇,你無怨無悔。這個世界上,有多少權貴“老而不死是為賊”,而你在烈火中永遠年輕。
在點燃自己的那一刻,你一定想到妻子和女兒,那是刻骨銘心的痛。對於愛,英國文學家C.S.路易士如是說:「愛,真的是一件會受傷的事。不論愛什麼,你的心勢必絞痛乃至破碎。」這才是真正的愛。如同林覺民在《與妻書》中所說,要以一己的犧牲,為天下人謀求永遠的幸福。
在你自囚期間,妻子葉菊蘭質問你説:「那我和竹梅怎麼辦?」你堅定地回答:「接下來就是你們的事了。」那個害羞的客家女孩,毅然私奔嫁給你的時候,有沒有想到你們的婚姻會是如此悲愴的結局?
多年以後,葉菊蘭回憶説:「每當有人談起鄭南榕,鄭南榕就在我心中又死一次。別人的先生死一次,鄭南榕卻死了千千萬萬次。」有一次,在鄭南榕紀念館策劃的女性白色恐怖口述《流麻溝十五號》新書座談會上,書中主角之一張常美女士,那位阿嬤跟葉菊蘭說:「你怎麼這麼憨慢,我還是要責備你,還是要罵你。你怎麼留不住你先生呢!」這句話,在葉菊蘭心裡已經藏了二十幾年,葉菊蘭心想:「對呀!我就是沒有能耐留住我先生。」每當心裡這樣想時,心就抽痛。她知道,丈夫是不會回頭的,「《出版法》的廢止,在法律上可能只是簡單一句話;但對有些人而言,卻是用身家財產或是用最可貴的生命去爭取來的言論自由。」是的,言論自由和臺灣獨立,是你願意用生命捍衛的兩大價值。
我又想,要是你能看到妻子在立法院裡的風采,你該為她深感自豪。「風猶然是昨日的風,血竟然是燒焦的血;南國的大榕樹,永遠永遠在我們心中」,葉菊蘭在立法院首次質詢,頭綁「臺灣魂」布條,再放邱垂貞蒼涼悲壯的歌聲,讓臺上的院長梁肅戎及台下老立委,渾身不自在,那股氣勢讓人們感受到什麼是「正義凜然」。
光陰如梭,你離去時年僅九歲的幼女竹梅,如今也為人妻、為人母。在爸爸離去之後,女兒曾寫下一首名為《爸爸像太陽》的詩:
爸爸
爸爸像太陽一樣
如果太陽不見了
我會哭
我會叫
但還是叫不回太陽
你生活的那個年代,離今天並不太遙遠。比鄭竹梅小一歲的張之豪在《鄭南榕與我的八十年代》一文中寫道:「同一個時刻,我在某一個角落,蹲在地上玩玩具,我的姊姊,在旁邊的角落,在想像自己是隻白天鵝地擺弄著從母親房間裡偷拿出來的絲巾。而在另一個角落,鄭竹梅,非常有可能,在跟我姊做著同一件事。」所以,張之豪説:「鄭南榕是我們,我們是鄭南榕,但是當鄭南榕點起那股烈火時,他不只是我們,他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更好,更勇敢,更理想,更無私。」
自由之翼永不折斷,即便上面有流血的傷口,也不會停止飛翔。我回首眺望自由之翼,它仿佛真的要破土而出、展翅高飛。伍佰的那首《白鴿》,似乎就是爲你而寫、爲你而唱,請允許我將《白鴿》中的這幾句歌詞轉贈給你:
沉默的大地 沉默的天空
紅色的血 繼續的流
縱然帶著永遠的傷口
至少我還擁有自由
假如你知道侯友宜在選市長,你會説什麽?
你的紀念塑像,整個臺灣只有這麼一個。老蔣不計其數的塑像,施施然地矗立在很多地方。當年,率領警察破門而入抓你的那個名叫侯友宜的刑警隊長,在陳水扁時代當上警務署長,在馬英九時代是你墓地所在地新北市副市長。有時,歷史會朝著先知做一個難看的鬼臉。不過,不必沮喪,黑暗不能永遠黑暗下去,翅膀總會攪動停滯的空氣。
台灣媒體報道,在新書《盧修一與他的時代》中,爆出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時任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長時,專抓海外異議分子,甚至用催淚彈對付盧修一。侯友宜聞訊表示,黑名單裡的彭明敏都能選總統了,若用這樣的方式,去清算當時奉公執法的同仁,這也算轉型正義嗎?有這個必要嗎?」
侯友宜自稱“奉公執法”,與艾希曼堅稱“我無罪”一樣,理直氣壯、斬釘截鐵。侯友宜認為,用對待恐怖分子的方式逼迫鄭南榕自焚並沒有錯,抓捕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黨外暴徒也沒有錯。艾希曼也認為,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一切行為包括將猶太人送入死亡集中營,都只是在履行上級的命令。但是,侯友宜與艾希曼難道真的只是兢兢業業、一塵不染的普通公務員嗎?
侯友宜在新北市長選戰中布滿大街小巷的宣傳照,早已沒有昔日刑警隊長的淩厲眼神與剛毅的容貌,而像是鄰家大叔一樣和藹可親,或許這種笑容可掬的照片能夠拉近與選民的距離。而法庭上的艾希曼也是如此,文質彬彬,有理有節,甚至有些木訥害羞,看上去一點也不像一般人想像中的“殺人魔王”。然而,一生研究極權主義的哲學家漢娜·鄂蘭指出:“艾希曼在臨終一刻,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正是在採訪對艾希曼的審判過程當中,漢娜·鄂蘭提出了最有影響力的概念之一:平庸之惡。由此,她揭示了極權主義統治的本質,甚至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質就是“把人變成官吏,變成行政體制中間的一隻單純齒輪,這種變化叫做非人類化”。
艾希曼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度過,看似渾渾噩噩,實則頗有效率。學者米爾格蘭姆在《服從的兩難困境》中指出:“艾希曼去集中營視察時也幾乎要作嘔,但坐在辦公桌前圍繞一大堆文件就沒有這種反應。同樣實際把毒氣發生器送到煤氣殺人室去的男子,以上級命令的理由可以使自己的行為正當化。”他不用親自殺戮,只需要在文件上寫寫畫畫,該承擔何種責任?如果是一個獨裁政府整體性實施的罪惡,這個罪惡從紙上的命令到具體的實施,必然經過若干層級。在這個複雜的體系內,每個人都只負責或承擔某一部分的工作或角色。這樣,一個參與實施邪惡計劃的個人,並不一定直接面臨行為結果。“這樣對整個行為負責的人就消失了,這就是近代社會的爲社會組織起來的惡的最一般的特徵。”
與漢娜·鄂蘭相似,喬治·歐威爾也對“平庸之惡”有過一番論述,他如此描述執行轟炸平民命令的、英俊瀟灑的納粹空軍飛行員:“我寫作之時,高度文明的人在頭上飛翔,想殺死我。他作為個人對我無冤無仇,我也對他毫不憎恨。他們的口頭禪只是:‘履行義務。’毫無疑問,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私生活中未曾有過殺人的念頭,是和藹可親、遵紀守法的人。即便如此,如果他們中的一個人,使炸彈正確命中目標,我像碎木片那樣被風吹走,這個人不會因此有一點點失眠的感覺。”侯友宜從未因為害死鄭南榕感到內疚、甚懺悔,他大言不慚表示,只是“救人未成功”,此種言論對受害人家屬造成了第二次傷害。
雙手沾滿鮮血的侯友宜出面選新北市長,而且被國民黨當著沒有政治包袱的“魅力型候選人”,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轉型正義的嘲諷。他不僅僅是一名粗魯無文的警察,而是一個厚黑無形的政客,他清楚地知道在台灣社會如何才能黑白通吃、藍綠並用。如果侯友宜在德國,他當然不可能“棄警從政”,而是束手就擒、乖乖蹲監獄。
如果侯友宜在德國,不是參選市長,而是進監獄。据德國媒體報道,九十六歲的前納粹軍官格勒寧(Oskar Groening),在二戰期間於奧斯威辛集中營擔任會計,被控謀殺罪,二零一七年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定讞,但格勒寧來不及入獄服刑,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在醫院過世。
格勒寧爲納粹武裝黨衛隊下士,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負責沒收及清點從集中營囚犯那裡搜刮來的財物,被稱為「奧斯威辛會計」(Bookkeeper of Auschwitz)。二零一四年九月,他被德國檢察官指控涉嫌為納粹大屠殺共犯。二零一五年七月,他被判因協助殺害至少三十萬名匈牙利猶太人的大規模謀殺罪,處四年有期徒刑。格勒寧提出上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二零一七年底做出裁決,維持原判定讞。
格勒寧在出庭時,只承認自己是在道德上有罪。法官認定,他是幫助「死亡機器」順利運轉的一員,不僅在道德上有罪,在法律上也有罪。格勒寧成為第一位因在集中營擔任普通業務而被定罪的案例。
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主席勞德(Ronald S. Lauder)在格勒寧被定罪時指出:「雖然有點遲,不過正義已經來了。」他表示:「格勒寧只是納粹死亡機器中的一顆小齒輪,但沒有眾多像他這樣的人,包含數百萬猶太人在內的大屠殺是不會發生的。」這句話準確地定位了格勒寧的歷史地位。
同樣的話可用來作為定位侯友宜:侯友宜只是國民黨暴政機器中的一顆小齒輪,但如果沒有眾多像他這樣的人,二二八屠殺和白色恐怖不可能發生,蔣介石和蔣經國不可能自己拿著槍一個個地殺人。
然而,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上遠遠落後於德國,一個本該進監獄的加害者,堂而皇之地出馬競選人口第一的中央直轄市市長。
另一方面,侯友宜的道德感也比不上格勒寧,格勒寜承認自己在道德上有罪,侯友宜卻洋洋自得地炫燿“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歷史”。
鄭南榕先生,繼承你的遺志,就是將獨裁而腐敗的國民黨送進歷史的垃圾場,包括侯友宜這樣的加害者。
這是一封遲到的信,這是身在另一時空中的後輩,想對你説的一番心裡話。我期盼著,有一天,海峽兩岸都不再有任何一個民眾被專制教育洗腦,也不再有人去慈湖、慈溪或天安門、韶山叩拜獨夫民賊的屍首、墓地和舊居。而到自由之翼的雕塑和墓地來紀念你、緬懷你、向你致敬的人,將絡繹不絕。
一名敬重你的後來者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