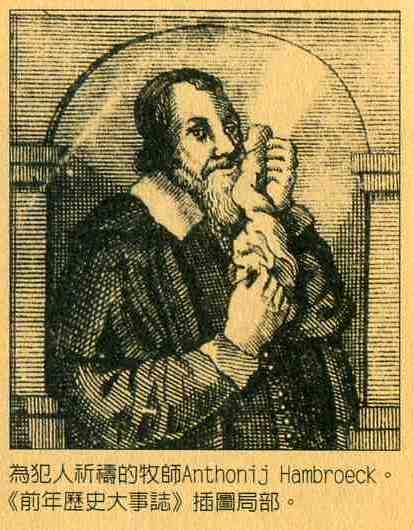作家陳芳明:《福爾摩沙三族記》是一部多元史觀的小說,但又可以當做歷史作品來閱讀。 作者陳耀昌自己則說:《福爾摩沙三族記》或許才是我對母親台灣的最大回報。這本書,如果沒有我的成長背景──出身府城老街、與陳德聚堂的淵源,也夠LKK,還來得及浸潤於台南的古蹟氛圍與寺廟文化;又正好身為醫師,懂得一些DNA及疾病鑑別診斷知識──其他人不見得寫得出來。 陳耀昌醫師這本巨著,之前曾在新頭殼〈開講無疆界〉欄目中刊載,新頭殼這次重新編排以系列推出,以饗讀者。
這天,亨布魯克家好熱鬧,因為有兩個家庭來此作客。
一位是新港社政務員優士德(Joost van Bergen van Damswijk),另一位是大目降社學校教師杜文達(Johannes Druyvendaal)。
當前熱搜:NBC:川普私下透露有意在伊朗境內部署美軍地面部隊
兩個人來到福爾摩沙都十年以上了,原住民的語言都說得很好。亨布魯克一家初到大員時,向兩人都學過西拉雅語,以及請教一些西拉雅人的習俗。
相同的是,兩個人都娶了福爾摩沙原住民的妻子。優士德夫婦生了三個女兒,杜文達夫婦則有一對男生雙胞胎。
不同的是,優士德的三個女兒,老大已經十二歲,最小的也有六歲;杜文達的雙胞胎則還未滿三歲。
當前熱搜:台中發生規模4.5地震!最大震度彰化4級 氣象署示警附近2斷層危險
兩家的兒女,都在部落出生,在部落長大。優士德的三個女兒,都長得像歐洲人,連頭髮都是紅褐色的,眼珠也帶著藍色,卻是滿口流利西拉雅語,反倒荷蘭話說得結結巴巴。杜文達的雙胞胎則長得像福爾摩沙人,目前尚在牙牙學語。
這三個家庭在一起,結果大人和大人說荷蘭話交談;小孩子們反而說起西拉雅話來,只有在對長輩說話時才用荷蘭語。
安娜摸著優士德大女兒的頭,驚訝地說:「哇,長這麼高了,還是個小美女呢!」
優士德說:「牧師和夫人,您們來到這裡,一晃也五年了。你看,現在連小彼得都會跑會跳了呢。」
亨布魯克說:「唉,真是啊,時間真快。想當年,我們一家初來到福爾摩沙,拜你們為師學西拉雅話,真謝謝你們啊!」
原來優士德一六三四年就來到福爾摩沙。他很有語言天份,來沒多久就學會了西拉雅語。於是自一六三九年開始,每年三月開的地方會議,都邀請他來當翻譯官。後來他在新港社協助甘治士傳教,但也擔任新港社及大目降社的政務員。
他和甘治士都愛上了福爾摩沙,也都愛上了福爾摩沙的女人。但是巴達維亞教會沒有批准甘治士和原住民少女的婚事,甘治士無可奈何,後來娶了巴達維亞總督史佩克斯與日本夫人生下的歐亞混血美女莎拉,但莎拉十九歲時就病死於福爾摩沙。優士德則是個自由市民,沒有這個限制,於是快快樂樂的和他喜愛的原住民女人結了婚,請尤羅伯證婚,組織家庭,在新港社定居下來,以福爾摩沙人自居。
杜文達則是在一六四四年來到福爾摩沙,在新港社及大目降社擔任教師。他的西拉雅話也說得很好,很受到原住民的敬愛。可能受了優士德的影響吧,四年前也和大目降社的原住民女性結婚,不久就生了一對可愛的雙胞胎。
杜文達則在旁稱讚亨布魯克的女兒們,「牧師,你們家的女兒才真是又漂亮又乖巧呢!」杜文達的原住民太太又接口說:「而且她們是在荷蘭出生的,西拉雅話說得這麼好,真不簡單。而彼得是在這裡出生的,荷蘭話和西拉雅話都講得那麼好,好羨慕喔。」
優士德說:「真糟糕,我那三位女兒,荷蘭話一直說不好。所以,倪但理等強調要在學校加強荷蘭語的教學是有道理的,否則我們的下一代的荷蘭語都會咬到舌頭,更不用說讀與寫了。住大員和赤崁的荷蘭家庭,平日仍然用荷蘭語交談,下一代還可以講不錯的荷蘭話,我們這些住在鄉下的可不行了。」
亨布魯克夫人說:「說的也是。所以在學校的荷蘭文教育,就很重要了。」
杜文達卻說:「可是,荷蘭政府不准我們的混血下一代回荷蘭,那他們荷蘭文說得多好又有何用,還是這裡的語言,說得好一些實際一些。」又加上一句:「我已經決定在這裡落地生根了。下一代荷蘭文能流利最好,不流利,我也不強求了。」一席話說得眾人都一陣沉默。
優士德說:「好了好了。今天來,是向牧師先生夫人報告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兩家都向公司申請發給我們土地,因為我們都已經決定在福爾摩沙定居下來了,而公司也准了,我們每人有160 morgen(註一)的土地可以來開墾耕作。我們家的土地在大目降社的南邊,杜文達家的在大目降社的西邊。」
亨布魯克夫人睜大了眼睛:「哇!160 morgen,你們成了大地主啦。這麼大的土地,你要幾天才走的完?!」
杜文達說,「是啊,我也沒想到公司會這麼慷慨。我打算請一些漢人農民來種甘蔗。這裡的土地,肥沃的很,將來把糖外銷到日本,只要不遇到荒年,大概收入不會太差。」
杜文達太太說:「可是最近常出現蝗蟲,很是恐怖,這可有些傷腦筋。」
亨布魯克說:「不用擔心。土地是永久的,蝗蟲則不可能年年都來,有土斯有財!」
亨布魯克夫人說:「政府早在幾十年前就有計畫移民整個荷蘭家庭到北美洲的新阿姆斯特丹,聽說自前年起,又准許荷蘭家庭移民好望角。但為什麼沒有到福爾摩沙來的?」
杜文達說:「不管政府怎麼決定,我自己早已經決定了,就是永遠留在這個島上,落地生根。」他指著在廚房幫忙的太太:「老實說,海倫雖然是福爾摩沙人,但是很溫柔,很善良,很肯學習,很能持家,兩個小孩也很可愛。而我的土地既廣大又肥沃,種什麼,活什麼。我對我擁有的這個家非常滿意。」
優士德也點了點頭,附和地說:「福爾摩沙的女人真的又善良,又能幹,刻苦耐勞,是好妻子,好媽媽。」
亨布魯克說,福爾摩沙人是很善良。但在這裡有一個問題是,除了要管理福爾摩沙人,還要管理漢人。如果漢人人數不多,還好處理,但如果漢人的人數比福爾摩沙人多,那可就有點複雜。
眾人高昂的談話聲突然低了下來,大家不約而同想到去年郭懷一Fayet的事。
優士德說,「唉,這是個隱憂,沒錯。但是去年Fayet聽說是受了國姓爺的煽動。因為很巧在那天下午,長官也收到一封耶穌會神父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自唐山寄到巴達維亞再轉來的信,特別向我們提出警告說,國姓爺可能會對福爾摩沙有野心。」
亨布魯克說,「聽說國姓爺的兵力高達三十萬人,而且他對韃靼人的戰爭聽說不太順利。很怕他有一天打輸了韃靼人,在唐山那邊不能繼續下去,難保不會另找出路而竄到這裡來。」
杜文達說,「我們荷蘭人的海軍,世界第一,巴達維亞也不會坐視不管的,安啦!而且,福爾摩沙人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國姓的兵雖多,有福爾摩沙人多嗎?」杜文達說得興起:「而且我們來福爾摩沙,是合法的,是有條約約定的。就好像我的160 morgen的土地,是合法的,是公司給的,誰也不能拿走。我真愛死了我那一大片長滿青色作物的土地,還有溪流池塘中的菱角、魚、蝦,連作夢都會笑。」
「牧師,這就是聖經上說的,流著牛奶與蜂蜜的土地啊!」杜文達說完,還做了一個鬼臉。眾人也跟著都笑了起來。
註一:參見2011年2月非凡新聞週刊,「『甲』:台灣的荷蘭遺跡」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