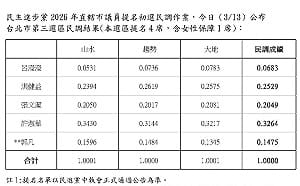忘了上次看陳昇的演唱會是什麼時候?曾經,跨年成為一種慣例,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坐在台下一起唱、一起瘋狂的年紀,但陳昇卻還是維持一年一次跨年、一年一張專輯,他像個農夫般,順著四季時序做音樂,不管這世界怎麼變,始終是那個低著頭耕耘的人,耕耘一片眾人幾乎已遺忘的音樂田。
站在Legacy裡,放眼望去清一色的白領上班族,參雜著一些熟年男女,這是陳昇新專輯「歸鄉」的演唱會,他唱了不少熟悉的歌曲,像是回到舊日的美好時光,有著久違的熟悉。
記得第一次看陳昇演唱會時,才剛出社會不久,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裡,驚訝四周都是年齡相仿的上班族,大夥一塊沈浸在音樂裡,跟著他把悲傷留給自己、想像自己是貪玩又自由的風箏、一起大喊Summer,像偷吃糖果的小孩般,享受那小小的放肆。那時唱過12點是種對規則的挑戰,誰說成人世界非要墨守成規,陳昇從不在整點時跨年,永遠依著自己的節奏,年年都唱到半夜才結束。
陳昇的跨年依舊在唱,但自己早已是個逃兵,禁不住漫漫長夜,無法再熬夜跨年,也很久不在歌曲裡找慰藉,愈來愈難有歌唱進心底裡。只是,不管外在世界如何變化,陳昇像個馬拉松選手似的,永遠以自己的速度,維持一張自己、一張新寶島康樂隊的節奏輪替著,年年都有新專輯。
音樂對陳昇來說,是一種必然,如同呼吸、飲水般,是生活的一部份,這一張張的專輯,也記錄了他的軌跡,「歸鄉」是他回到成長土地的一張專輯,就像歌裡常出現的意象,貪玩的孩子在母親的呼喚聲中回到了原鄉—彰化溪州。「我的故鄉她不美,如何形容她」,是啊?當「土地上長出了煙囪」(賣田)、「稻田上都種起了咖啡屋」(美好的哲學家),該怎麼說那當年孕育自己長大的地方?回首土地已是滿目瘡痍,歸鄉成為一條漫長的路。
當前熱搜:伊朗新最高領袖首度發聲!「不會放棄復仇」將繼續封鎖荷姆茲海峽
陳昇的歌曲始終映照著土地上尋常人物的樣貌,浪子般的七叔、眷村裡的大頭春、嫁到美利堅的校花陳老師、五十塊錢就能買到一支獨舞的甜心寶貝,許多人的故鄉裡,都曾有過這樣的人、事、情節,這些平凡的人物,在陳昇的歌聲中,立體如在你我身邊,被他唱成了一種時代的印記。
「歸鄉」像是鄉愁般,濃濃攀附在聽者的心中,忍不住在回憶裡蒐尋,那裡才是自己心裡的原鄉。「穗花」是專輯裡有著淡淡悲傷的情歌,有些戀情就像稻米與風,註定要分離;「賣田」是農業凋零後,許多家族繼承的寫實劇;「61號省道」上閃亮的檳榔西施是甜心寶貝;「美好的哲學課」唱著生活像過氣的黑膠唱片,是不重疊的同心圓。
「青春不值幾兩錢,仰頭就忘記」,陳昇這麼唱,這年頭懷舊是不必要的,過去就該讓他過去,昔日舞台上猖狂的歌者,現已端著老花眼鏡看詞譜,忍不住跟著他的歌聲想,「當年那個瘋狂的小孩,轉眼之間變成了哰叨的歌手」?「當年那個靦腆的小孩,轉眼之間成了瘋狂的革命份子」?「當年那個美麗的女孩,轉眼之間生了豬一樣的一堆小孩」?那個才是你人生的選項?

「歸鄉」像是鄉愁般,濃濃攀附在聽者的心中,忍不住在回憶裡蒐尋,那裡才是自己心裡的原鄉。「穗花」是專輯裡有著淡淡悲傷的情歌,有些戀情就像稻米與風,註定要分離;「賣田」是農業凋零後,許多家族繼承的寫實劇;「61號省道」上閃亮的檳榔西施是甜心寶貝;「美好的哲學課」唱著生活像過氣的黑膠唱片,是不重疊的回心圓。 圖:新樂團工作室 /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