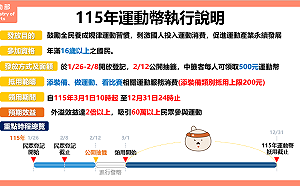去年3、4月間台灣社會在318學運的衝擊下,反政府的激情四處洋溢。一年後回顧當時運動的初衷,反省運動中的莊嚴承諾,在浪頭上奮勇爭先的學運要角、默默固守議場的志工、以及他們的夥伴們,一年來無可避免的必須檢視當初318這一系列的運動到底算不算成功?台灣如今有沒有遍地開滿太陽花?主流媒體的關注讓當時和現在的運動產生什麼變化?社運資源是否遭特定社團壟斷?當時的運動過程中有心或無意間刻畫的傷痕如今痊癒否?
《新頭殼》專訪10多名當時的運動者,描述他們一年來心境的轉變與對未來的展望。
這場運動不但來得太突然,發展得太迅速,規模也出乎意料的大,跟過去的運動經驗落差太大。初期在議場內擔任發言人的黃郁芬就說,過去運動時頂多只有「媒體聯絡人」,因此開會籌備時根本沒人想說要設「發言人」來面對媒體,而她雖然被推派為發言人,但其實不能算是決策核心。她還自嘲自己比較像是「擦屁股」的角色,因為林飛帆、陳為廷念完聲明稿後不會受訪,就必須留她下來面對媒體提問。
當前熱搜:預計政院今拍板!國民年金給付將提高並即時反應CPI 176萬人可望受惠
除了規模外,最大差異就是受媒體關注程度大大增加。黃郁芬說,當時每次開會幾乎都是以「今天某報寫了什麼,我們要怎麼解決?」為主軸,對「如何達成訴求?」反而沒那麼著重。雖然她也認為在當下很難不去理會媒體,但社會運動也不應該一直被媒體牽著走,她覺得若能從訴求延伸,設定好哪些要回應媒體,哪些不用,這場運動的走向可能就會不一樣。
重視媒體輿論大於運動訴求?
一場大規模運動要走下去,必須得到社會支持,對輿論的反應就不得不在意,特別是當媒體對於這群社運學生完全陌生,社會也普遍不信任媒體的情形下更是如此。伴隨著這樣的情緒,就出現了「乖寶寶運動」的爭議,小至「不能亂翻委員抽屜」、「330遊行後要撿垃圾」,大至「醫療通道的設置」、「全面打通立法院院區」等都成為內部爭辯焦點。
一年後看起來,一位議場核心幹部仍認為當初走「乖寶寶路線」是對的,衝進去立法院的暴民,就是因為開始撿垃圾後形象快速轉換,事實證明確實籠絡了很多中產階級。然而,佔領議場期間反對此舉的「二樓奴工」楊尚恩和高培軒仍極度不滿,他們說,當時大家都喊「警察不動,我們不動」,但都衝進議場了為什麼還要坐下來讓警力有時間部署?且就他們的觀察,明明就是警察一直偷偷地在動,結果學生還笨笨地在那邊不動。他們更質疑,如果說全面打通議場內外佔領區會讓社會輿論不支持的話,那「完全不進去議場不是更支持?」
一場成功的運動?遍地開滿太陽花?
針對這場運動最終是否已達成訴求的檢視,核心決策圈的林飛帆、黃國昌評估較樂觀,但許多參與者卻難以認同。議場核心幹部、民主鬥陣成員吳崢直言,當時4個訴求「退回服貿、先立法再審查、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兩岸監督條例」現在仍未達成,因此運動不能算是成功。
但不成功也不代表就是失敗,這場學運讓更多青年更願意關心政治、返鄉投票、參與各種公共議題等外溢效果,幾乎是受訪者中大多數人的共識,當然,國民黨在9合1大選中慘敗也常被視為是學運所直接催生的政治板塊大挪移。綠黨共同發起人李根政說,318逆轉了社會原本的認知,父母那一輩會開始重視年輕人的政治價值判斷,不再認為他們只是小屁孩。
318運動後能量延續的發展,為後續的427反核佔領忠孝西路、割闌尾行動、9合1大選等行動都挹注了可觀的能量。但公民1985行動聯盟、國會調查兵團代表王希卻認為,其實當時各個訴求後來都沒有強力擊中焦點;以推動公民憲政會議來說,討論的人和團體很多,但力量卻分散,缺乏一個比較中心的論述或推動方向;「兩岸服貿協議」當時雖然被擋下來,但相關的論述在運動之後並沒有完整地進一步去討論,社會對服貿協議還是停留在不是yes就是no的階段,相當可惜。
社運贏得更多的參與、更熱切的關注
318前後,各種社運團體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較為活躍的就有林飛帆、陳為廷與黃國昌3人的「島國前進」、以議場幹部為主幹組成的「民主鬥陣」、政治光譜較獨派的「臺左維新」及以南臺灣為據點的「基進側翼」、而學運前就組成、反服貿行動中表現突出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更朝向組織化發展,制定了由會員「逐條審查」的組織章程。
當然,團體多了參與的人也就更多了,特別是318時才投入社運的新人。議場核心幹部、黑島青成員賴品妤就說,過去運動圈參與者大部份都是法律、社科學院出身的背景,但現在也有理工科系等不同領域的人加入了。此外,社運也不再以學生為主,像「臺左維新」成員5、60人中就有一半是上班族。
318運動成功地拓展了年輕人對社會關懷的層面,從而促成許多新人的投入與參與。但吳崢倒是提醒,新血雖變多了,但很多人抱持著「有投入就會成功」的心態從事運動,他因此必須經常提醒夥伴,運動的過程中大多數時刻其實面臨的是失敗與挫折。議場糾察、黑島青成員黃燕茹則認為,參與社運的人雖變多但相對還是有限,並不是每個議題都有那麼多人投入,像年初一場反土地徵收聯盟的行動,現場的行動參與者其實都還是318前的老班底。
411「路過」中正一「首謀」洪崇晏認為,318一次爆發的能量太大,很多新團體一下獲得很多資源挹注,但其實內部成員都還沒組織好也不清楚自己定位,也不知道長久下來倒底能撐多久,他建議,從事社運的運動者應該有「暴飲暴食,不如少量多餐」的體悟。
當然,團體多也自然會產生資源排擠問題,社運人士王奕凱就譬喻,318後社運界的確呈現遍地開花的景觀,「但開的卻不是太陽花,而是豬籠草」。意指有明星加持的島國前進大量壟斷資源。對於壟斷資源的問題,島國前進發起人黃國昌也承認,話語權上確實有此現象,但他們在學運退場時就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島國前進」也刻意不去申請318募款資金結餘款的分配。
不過,學運後可以確定的正向發展是,社運議題獲得主流媒體更多的關注。「臺左維新」總召林于倫就說,以前覺得反正不會有媒體關注,可以隨心所欲,卻也可能會「盲衝」。現在社運團體作為變得更謹慎了,會更在意如何透過媒體引起關注,規劃補給線等前置作業,例如他們去蔣介石銅像噴漆前,都會先準備好聲明稿、投書媒體的文章、以及之後自首記者會的規劃等步驟。事後許多縣市表示要移除銅像,也證明運動確實有效。他也說,318讓很多人認知到「體制是可以衝撞的」,才會讓今年228銅像噴漆事件多達數十件,規模遠勝以往。
只有「前進」,卻沒有「回頭」處理的運動傷害
在運動的當下,其實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遭受程度不一的運動傷害,除了對於議場決策核心不夠民主的失望外,323行政院流血事件更是許多夥伴關係崩解的主因。當時不少行政院「首謀」在運動當下就曾打算出面自首,但一句「相忍為運動」的話仍一直流傳到現在。即便是在滿周年後的今天,仍可見臉書上偶爾蹦出運動者的抱怨、討拍文、時不時透漏一些訊息,最後卻在公開或私下的壓力下,馬上又刪了文。很顯然地,運動傷害並沒有痊癒,頂多是情緒稍微平靜下來。
對此,林飛帆受訪時一開始說,普遍情形來看,這一年很多東西是慢慢修復回來,大家誤會也慢慢解開了。不過,在記者繼續追問後,他則改口表示,有些傷害確實難以彌補,「野百合那一代很多傷痕也是持續20年,現在還有人老死不相往來」,例如當時民學聯和台大系統的鬥爭,也是現在才慢慢修補關係。
黃國昌則直言,大運動後出現分裂,是歷史的「常態」不是「變態」,在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中很難找到大規模運動後未出現矛盾或意見不一致的例證。但他會持續的質問、面對自己的初衷,當初是基於什麼理由要從事運動,若理由沒有消失,就應該想辦法找出最好的策略繼續推動改革。
李根政也覺得,318運動「神聖」的共同情境消失後,各團體本就會回到「庸俗」的常軌,這樣的「分裂」其實是相當合理的。
不過,王奕凱卻認為,當時產生的嫌隙,延續到各團體的領導幹部後,新進人員當然也會承續上一代的情緒,這不是好事。黃郁芬則明言,帆廷昌3人這一年來推動「補正公投法」的過程確實做得很好,但可惜的是,他們只想著如何「前進」,而沒有「回頭」修補同伴之間的關係。她也同意,大型運動一定有分裂,但至少可以不用落得像現在令人「無法承受」的四分五裂,雖然傷害不可能完全痊癒,但如果能全部攤開來講一定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