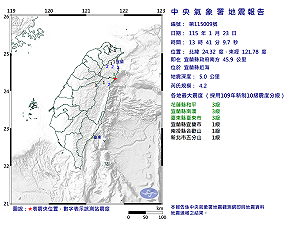西方對東方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不只受到西方人關注,東方人本身也一樣看得津津有味;原因是,透過局外人的眼光,總是能夠看到自己忽略的視角,進而多點了解自己在他人眼裡究竟是怎樣的面貌;即使不贊同他們的見解,也是另一種反觀。
當前熱搜:因應開學返校!高鐵加開12班「大學生5折優惠列車」1/27開搶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 在二戰後寫的《菊花與劍》,研究日本人的文化模式,可謂西方人對一個戰敗民族深入觀察的里程碑,美國政府想透由研究文化模式,了解日本這個令人驚嘆的民族,是如何變成今天這樣。
全站首選:黃國昌怎麼選都輸!新北最新民調攤牌 吳靜怡:藍白合一碰到他就破功
不同的是,《野心時代》是一位派駐中國的美國記者,對這個已經足以和美國分庭抗禮的大國的觀察和記錄。
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當然不是人類學家,本書也不在於找出怎樣一個文化模式,來了解中國這個龐大而令人難以全盤了解的複合民族。他是記者,所以從現象著手,將所見到的種種由野心燃放的火花給記錄下來,企圖呈現這一個世代中國人的激昂與沮喪。
從2008到2013年的駐華記者生涯,在其尾聲中,歐逸文剛好趕在習近平接棒的時刻,這段期間可以說是中國形勢從相對寬鬆轉為更形嚴苛的年代,他有許多機會去深入探訪每一個他覺得象徵這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無論是赫赫有名如韓寒、艾未未、陳光誠或胡舒立等等;或者只是一個希望藉著英語教學發財致富的升斗小民,舉辦網路紅娘因而能夠從女工翻身入住豪宅的女老闆;以及在澳門賭場中玩百家樂大賺一筆就跑路的香港人。
他們都在賭,如果說這是一個野心時代,這個野心也是透過勇於下賭注而來;時而曙光乍現,時而烏雲滿天,他們在尋找可能的機會,或許對時局有所改變,或許就魚躍龍門。即使明知機會不大,但他們的野心,或者應該說是企圖心的背後,卻由一股飢渴症候群所驅使:今天不做,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
其中曾經下過最大賭注的人,恰是由金門游泳橫渡對案向中共投誠的軍人林毅夫。擔任過世界銀行副總裁的林毅夫,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傳奇,卻讓沾上邊的台灣人覺得有點不自在。因為他背叛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而如今他效忠奉獻的中國政府卻已經大國崛起,世界都為之震動。
有趣的是,《野心時代》所描述的這些現象,同時也是另一種東西方對話。中國人從他們愛憎俱烈的美國,學到與獲得新的概念和技術,但同時也成為他們批評西方的利器。
例如,來自上海留過洋的一位年輕民族主義者,矢志對抗西方觀點。一位人權倡議者被警察找上門,警察勸告他的用詞是:「瞧你那爛車,已經開七、八年。你的朋友們已經都買朋馳了。」朋馳汽車,恰恰是西方物質主義的經典,卻成為中共用來柔性說服人權主義者的理由。
然而,書中所描述這些由野心所綻放的火花,終究都不能長久。韓寒最後選擇明哲保身,免得像艾未未一樣遭到全面監控和查稅。胡舒立的財經新聞夢想,在中國體制夾縫中愈來愈窒礙難行。陳光誠只好出走美國,劉曉波依然身繫牢獄,維權律師高智晟經歷殘酷的監獄刑求後,只好被迫宣布退出他曾經獻身的目標。林毅夫對中國經濟成長可以保八20年的預言,更是已經破功。
這本書最後出場的,是一位喜歡寫新詩的清潔工齊祥福,曾經贏得「中國超級對聯王」的稱號,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文學大師。作者這樣的安排,耐人尋味;引用歐逸文自己的話:中國生活裡有個洞,人們叫它「精神空虛」,得做些甚麼,來填補它。
如今中國經濟有急速下墜之勢。這次問題來得更嚴重而猛烈。雖然本書作者來不及探查這次可能劇烈的改變,但《野心時代》或許剛好為即將到來的巨變,提供一個出場前的鋪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