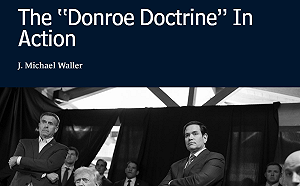1988年6月,達賴喇嘛受邀訪問史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在此期間他正式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在這個計劃中,西藏將是“一個自治、民主的政體,並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其權力結構由“一個人民選出來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法部門、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所組成。20多年來,中間道路獲得了大部分海外藏人、關心西藏問題的西方人士以及一部分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中國人的肯定,卻遭到中共當局以及持強烈民族主義理念的中國人的反對。
現正最夯:陳彥斌觀點》楊瓊瓔為何不服江啟臣?
面對此種情形,除了達賴喇嘛繼續發揮其無可替代的國際影響力,藏人流亡社區持續其民主化的實踐,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繼續關注西藏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之外,還有哪些事情可以做?觀念可以改變世界,中間道路無疑是一種優質的觀念;但首先觀念必須得以普及,並在更為寬廣的制度和文化層面贏得支持。在這一領域,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不能袖手旁觀,而是大有可為。
中間道路應當具備寬廣的闡釋空間
達賴喇嘛為中間道路描述了一個粗線條的遠景,它排除了兩種不利於西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的選項,即中間道路“不是”什麽:一是中共政權目前對西藏實施的極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治,此種統治方式是不能長久地持續下去的;二是某些激進的藏人以暴力手段爭取西藏完全的獨立,並斷絕與中國所有聯繫的策略,這種想法和做法既不現實也不符合西藏文化傳統中的非暴力價值。
那麽,中間道路究竟“是”什麽呢?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並沒有作出更加細緻的定義。在我看來,它並不是一個凝固、僵化、定型的概念,而是一個存在著寬廣的闡釋空間的、動態的觀念。
2013年,台灣的一批知識分子以“守護台灣民主平臺”的名義發佈了一份以兩岸關係為旨歸的《自由人宣言》。該宣言指出:“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說:「唯有自由人,才能簽訂契約」,我們認為,唯有當台灣與中國的憲政主義與人民主權都真正落實,人權獲得充分保障,兩岸人民都成為真正自由人的時候,才有可能在各自人民自決的前提下,開始思考是否發展聯邦、邦聯、國協、東亞區域聯盟,或其他具備憲政主義基礎的新形式。”
這份文件顯示了台灣知識分子處理兩岸議題時高瞻遠矚的視野、寬廣的胸襟和靈活的姿態。儘管台灣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擁有實質性獨立的政府、軍隊以及為少數國家承認的獨立國家的地位,比起西藏來迴旋的空間大得多,但西藏方面仍可從台灣知識分子的智慧中汲取富於刺激性的思想資源。也就是說,未來西藏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並沒有定於一尊的模式,而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沒有共產黨,才有中間道路的真正實現
近年來,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大大增強了與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和正在成長中、充滿活力、思想開明的中國民間社會的互動,這是一個相當可喜的現象。反之,越來越多的藏人認識到,中共政權不是一個值得期待的談判對象,中共政權從來只迷信槍桿子的力量。只有當中國的民主轉型來臨之後,才有實踐中間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更加直白地說,沒有共產黨,才有中間道路的真正實現。
從習近平執政以來對香港的強硬政策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中共對作為世界金融貿易中心的、在全球眾目睽睽之下的香港,尚且不肯放鬆一絲一毫,那麽,中共對西藏又怎麽可能做出讓步呢?再多藏人自焚的悲劇,也喚不醒中共統治者泯滅的良心。中共統治西藏的邏輯,完全無視藏人的心聲和基本人權,正如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1947年後的西藏》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統治西藏的模式,以及統治的每個階段該收緊或放鬆控制到什麽程度,都不真正受到西藏內部的情勢所支配,而是由共產黨領導班子所面臨的更加複雜的意識形態與權力鬥爭的議題所支配。”當下中國統治集團內鬥加劇,習近平必然採取最左、最保守、最強硬的手段,處理香港、台灣、新疆和西藏等所謂“中國內部事務”。所以,對中共政權的“惡”必須有充分的估量。如果低估了中共政權的“惡”,必將付出沉痛的代價——就如同1989年的學生那樣。
在此,我要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出一點小小的意見,我認為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不宜在公共場合表達對中共當局不切實際的期望。試圖用正面評價習近平政權的“善意”來換取其在西藏政策上“鬆綁”,實在是一種與虎謀皮之舉。其實,更有效的立場宣示是:將獨裁而腐敗的共產黨政權與中國切割開來,強調歷史上西藏與中國之間長期存在友善的關係;反之,毫不回避中共專制制度不僅荼毒中國內地人民,也造成西藏人民亙古未有之苦難的事實。換言之,批判、反對共產黨政權,既符合西藏民眾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所有中國人乃至全球民眾的根本利益。
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要讓中間道路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中國民眾當中獲得廣泛的共鳴,首先需要清除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那就是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首先,需要反思和解構中國的大一統的政治傳統。用譚嗣同的話來說,中國兩千年一以貫之的是“秦制”。在權力的橫向分配上,皇帝以天子自居,神權與政權合一,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合一;在權力的縱向分配上,對皇權所及的大部分區域採取秦朝的郡縣制,中央壟斷絕大多數權力,地方不享有自治權。此種統治方式,用美國學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國》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傳統的制度將崇高的儒家理念與嚴酷的法家手法合二為一。中華帝國採用了同樣以高尚辭藻和高壓為特點的兩面手法來對付外部威脅。這種意識形態界定的道德主義與冷酷的高壓手段的融合,在孵育它的中華帝制滅亡之後還長久地留存下來。”破除這種被共產黨繼承過來“為我所用”的政治傳統和意識形態,是推廣中間道路的前提條件之一。
其次,需要反思和解構中共從蘇聯抄襲而來的所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蘇共從沙皇手中奪取政權、並建立了疆域更為廣大的蘇聯之後,強行按照民族劃分行政區域。沒有想到,這種貌似“優待少數民族”的體制,反倒惡化了不同民族之間原有的良好關係,為蘇聯的最終解體埋下了導火線。法國學者埃萊娜•唐科斯在《分崩離析的帝國》一書中指出:“蘇聯政府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以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繼承的沙俄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胡同。”這句話也可以用來描述今天中國民族問題不斷激化的現狀。如同“皇帝的新衣”一般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從他國強行移植而來的,跟中國“在地”的環境水土不服,並且在蘇聯的實踐已經完全失敗,卻在中國成為一道不容置疑且難以摘下的“緊箍咒”。
作為中間道路推動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多元化的統治模式,共和及聯邦制度
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需要解構和清除;反之,作為中間道路推動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則需要建構和鼓吹。
在古代中國,與大一統傳統和朝貢體制相配合,有一套相對柔和的、多元的統治模式。美國學者黎安友在《尋求安全感的中國》一書中指出,傳統的中國並不視自身為一個民族國家,甚至不把它當作一個有著不同臣民的帝國,而是把它視為文明的中心。清王朝願意給周邊的所謂“蠻夷藩邦”授予特權,讓它們對生活在中國領土上的本族臣民進行管理、徵收貿易稅以及懲戒。當西藏逐步形成一個結構鬆散的神權國家的時候,滿清統治者為了籠絡西藏,甚至放棄他們原來的薩滿教信仰,轉而皈依藏傳佛教。
換言之,帝制時代的中國,中央政府對在其勢力和影響所及的範疇內的不同種族、地域和歷史文化大致都能給予一定的尊重及自治權,從而形成多元化的統治模式。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這一傳統卻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元化的極權主義的統治模式。中共政權悍然撕毀與西藏簽署的協議,破壞西藏固有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從而在西藏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未來的民主中國,在處理西藏問題的時候,需要重新發掘“前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的可以實現“現代轉化”的政治資源,使之成為中間道路的支撐點之一。
其次,讓在現代中國建立聯邦共和制度的失敗的嘗試,得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樣中間道路就有了另外一個支撐點。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之後中華民國成立,那時的仁人志士一度嘗試在中國實行聯邦共和制度。特別是20年代的聯省自治運動,差一點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中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當時的實力派人物中,無論是南方的陳炯明,還是北方的吳佩孚;在當時的知識界領袖中,無論是戊戌一代的代表人物梁啓超,還是五四一代的代表人物胡適,都曾真誠而無畏地投身於聯省自治運動之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受蘇俄驅使的國共兩黨,聯合發動北伐戰爭,以武力方式統一中國,使聯省自治的努力功敗垂成。
如今,在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中,一方面需要從當年的聯邦共和實踐中汲取教訓,另一方面需要從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聯邦制與共和制的成功經驗中取來火種。在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同時,也同步完成聯邦共和體制的建立。否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也有可能借助民主掀起法西斯狂潮。民主若與聯邦共和的觀念相配,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也就必然能夠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下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接納。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