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BP扯出CEO肥貓 黃金降落傘社會不爽
2010.08.02 | 17:02
上(7)月27日英國石油公司(BP)總裁海沃德(Tony Hayward)宣布辭職。在這之前,他所帶領的BP因海上鑽油台失事,讓好幾兆加侖的原油傾倒進墨西哥灣裡。他的危機處理也叫人不敢領教,經濟學人雜誌批評他是「會走動的災難(walking disaster)」,因為他在公開場合一再失言。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讓BP必須拿出320億美金,以支付清理海上漂油以及各種賠償,造成BP空前的虧損,但拍拍屁股走人的海沃德仍然可以領到一筆高達160萬美金(逾5000萬新台幣)的離職金,同時也可以開始支領保守估計總數將高達1,760萬美金(約5億6千多萬新台幣)的退休金。對此,美國國會議員很不爽,抱怨說這是好幾百萬美元打造的「黃金降落傘」。
剛好這幾天,台灣媒體也在報導本地「肥貓」的消息。根據證交所最新公布的去年上市櫃公司董監事酬勞,有16家公司營運出現虧損,但每位董事平均仍領百萬元以上酬金。其中友達去年虧損267億,平均每位董事仍領270萬元;萬泰銀、旺旺保兩家公司連續三年虧損,每位董事也都領150萬元以上大紅包。至於有賺錢公司董事的薪資加酬勞金就更加可觀了,宏碁電腦董事平均每人領5,887萬,聯發科5,226萬,台機電4,885萬。這麼高的數字也會讓一般民眾懷疑,這些董事們的能力和努力真的值這麼多錢嗎。
確實,去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讓人更清楚看到,有一些大公司的「肥貓」主管,平時坐領一般人難以想像的高薪,如果捅出摟子,還可以攜帶「黃金降落傘」逃生,把爛攤子丟給股東,甚至納稅人去收拾,這未免太不公平。
這樣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現象是如何發生的?它有可能解決嗎?
加拿大裔的美國經濟學家蓋布瑞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在他早年的「新工業社會」一書中,就已經看到一個「技層結構(technostructure)」的形成。這個社會經濟階層由高階管理者、科學家及律師等所組成,他們在公司決策中比股東更具有影響力,他們這個階層有自己追求的經濟目標,他們重擴張、輕利潤,有時也不免因追求和自己績效相關的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後果。
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集中化讓這個現象更為明顯,經營規模愈來愈大,讓「技層結構」的薪資與福利愈來愈豐厚,而決策影響力也愈來愈大,一旦經營出現偏差,後果也更嚴重。現在全球性大公司的主要股東已經絕少是個人,代之而起的是投資公司、各式各樣的基金及銀行等。代表這些機構執行股東權力的同樣也是來自相同階層,他們與公司管理階層有同屬「技層結構」的共同利益,所以不太會彼此為難。所以公司經營好時,大家有利可圖,可是高階主管的利益最好;公司經營搞砸了,股東、員工、客戶、債權人都倒大楣,甚至政府還要出面善後,可是往往「肥貓」們還是可以帶著「黃金降落傘」風光退場。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華爾街有些公司與高層主管的合約,引進所謂「回吐條款(clawback clauses)」,讓這些主管每年所領的績效獎金,在事後發現不如預期時,必須回吐回來。可是到目前為止似乎這些條款沒有真正執行過。
最近美國政府的金融改革方案,則要求管理高層的薪資及「黃金降落傘」必須由股東投票決定,可是它所引起的衝擊和爭議都很大。
美國是高度尊重企業自由的國家,因為金融危機許多大企業紛紛向政府求援,政府才取得介入的正當性。台灣大企業的成長背景有很明顯政府的影子。到今天,政府仍然是許多大企業的主要出資者或借貸者,因此,倘若這些公司的公司治理出問題,政府會背負較多的責任。
台灣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走上資本集中及全球化的路,因此「肥貓」與「黃金降落傘」的現象會愈來愈頻繁,而終將引發社會的緊張關係。美國的例子顯示,要同時尊重企業自由和實現社會正義,其實有一定難度。台灣應該針對此問題多加研究,找出適合台灣國情的解決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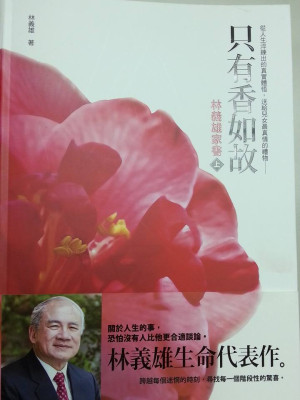









最新留言
專論》 因川普關稅而陷入困境的中國「SHEIN村」
0 分鐘前
在美國、日本等國家深受年輕人喜愛的中國電子商務網站SHEIN,因為川普政府的關稅措施,而受到沉重的打擊。在中國南部的廣東省廣州市,有一個被稱為「SHEIN村」的地區,這裡密集分佈著為SHEIN供貨的服飾工廠。隨著美國加大對中國的關稅攻勢,一些工廠因為訂單大幅減少而陷入困境。與美國的貿易戰「將傷害像我們這樣的底層工人,並使我們更加貧窮」,面臨失業威脅的移工們心情低落地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