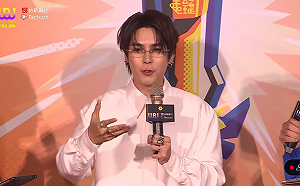我在十多年前便關注此議題,沒想到約十多年後,台灣社會這個問題還是在,且持續惡化。
2025年台灣碩博研究生正面對憂鬱、焦慮纏身的多重挑戰,每五個研究生,就有一個休學?出現被洗腦要選邊站,又害怕站錯邊,及不當壓迫指導文化和獨裁專制毒害。
而在現今不當結構性壓迫制度下,不只研究生,連教授也是被壓榨的對象,台灣研究生所面對的多重挑戰,羅列如下:
1.找不到指導教授。
2.養不起自己。
3.做不好研究。
4.修改不完論文。
5.我的位置是研究生,還是廉價勞工?
6.被迫被洗腦要選邊站,又害怕站錯邊畢不了業。
7.怕畢業找不到工作。
她是一位每天早上九點進辦公室,隨即開始規劃學生的實驗,或是帶著學生做實驗,通常會到晚上九點才下班,研究工作時間長達十二小時的新任大學教師。
由於她的專長背景與生物科技相關,所以實驗室的耗材、設備花用都十分驚人,必須倚靠國科會研究案經費的補助,才可以讓實驗室得以正常運作,所以每年通過研究案審查對他是極重要的任務,而目前台灣的大學教師評鑑制度上仍是偏重研究這一區塊,這樣的評鑑制度同時也掌握教師升等的生殺大權,因大學教師聘任不是終身職,且必須升等為教授,才能免除身陷類似八年條款的危機,在這些攸乎生存的條件前提下,她怎能不戰戰競競,如屢薄冰。
最近實驗室的學生出了一些事,造成她必須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協助學生,這是一個兩難情境,她最後決定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縱然她知道這樣的評鑑體制下,許多大部分老師的選擇可能將課程交給助教去教,而自己忙於實驗室研究或者擔任企業顧問,但這個有『教育愛』的生科系女老師還是願意選擇一個在體制下不利於自己的決定。
如果你是那個面臨兩難情境的生科系大學教授,你的決定是什麼?
目前台灣的大學教師工作包括「研究」、「教學」、「服務」、「輔導」,但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的獎勵卻多偏重於研究卓越的老師,忽略了其他三項同樣表現傑出的大學教師,這樣失衡的大學教師評鑑標準卻可以持續決定一個大學教師升等與否的現實生存問題。
多年來,台灣雖有「多元升等制度改革」,但仍未見到巨大性的全面變化。
我觀察到台灣的大學教師評鑑政策修正的迫切性,因2021年台大植物所張姓副教授在實驗室內上吊自殺,留下遺書表示主要是因為升等壓力大,而現今台灣高教界有關注到大學教授研究升等問題,雖有「多元升等」的新路徑,但實際上研究仍然是主要成績,多元只是為派系和權貴開方便小門,一般老師很難受惠,因台灣的大學教師升等,主要依據是學術論文,導致許多教師埋首研究、輕忽教學,雖然教育部102學年起推動教師以教學、服務等非學術成果升等,此類升等人數已從當年的2人,攀升至108學年的216人,6年成長108倍,此類教師難免被同儕質疑「夠格升等嗎?」,台灣的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健康風氣仍待建立,因憑教學升等不等於研究能力差,如具備教學和研究能力合一,反而研究能力更強。
台灣高教界過去出現所謂的「6年條款」、「8年條款」,在大學教師聘書內載明,助理教授如果6年或8年內無法升等為副教授就必須離職,讓年輕老師壓力非常大,矛盾的是照理說老師如果拿到副教授,就等於教職有保障,但台灣許多大學裡卻出現「萬年副教授」,不願意做研究,也不想升教授,只想輕鬆過日,又讓許多學校訂有內規,要求副教授也必須盡快升等為教授,如果長期未升等,就會在系所內被冷嘲熱諷、甚至是「集體霸凌」的壓迫。
如此的評鑑制度,在時間心力重要性的比重權衡之下,造成大部分的大學教師必須面對現實地以研究為主,對教學的態度則為應付就好的工具理性思維,這樣單一簡化的評鑑標準、僵化的升等機制以研究發表的特定期刊論文為依據,將會造成扭曲學術研究性與創造性,忽視論文的多元與品質,而大學教授最終被「異化」為生產論文的機器!淪為被研究經費奴役的一群工作者,也漸漸忘卻了大學的本質與使命–把孩子教好,做好學生的「教育」。
時間已至2025年,研究生才是台灣高教碩博班教育的主體,他們都是好孩子,需要教育愛栽培、友善對待、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曾看著孩子因結構性制度壓迫,被迫戴上笑臉孔面具,心中不忍,這真的是教育部在碩博士生教育需要修正之處!
其實,碩博研究生在學習生涯常會稱呼自己論文指導老師是「老闆」,事實上「老闆」應是你自己,找回自己學習的主體性,指導老師是協助輔助的角色。
研究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大學教授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獲得最新的知識,也是本著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精神。過去指導學生論文,我常常會和研究生說你們有得獎的潛力,老師可幫助你完成出國留學的夢想,其實是老師有得獎的能力,必能帶著學生得獎和完成第一次夢想,事實上也做到了,親自指導帶偏鄉大學生們考上全球百大碩士或其他第一志願的碩士班,而真正厲害的老師能激發孩子的潛能,就此建立無法擊敗的自信心,進而去完成助力國家社會性各大議題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N次夢想!
最後,特別是台灣碩博研究生的人性化生活品質環境,給研究生一個美好碩博士的學習回憶,當孩子進入更複雜的社會,想起這些老師愛心栽培記憶,而不是被老師罵哭,甚至不合理對待受到身心創傷,因為老師曾對我付出,內心感動又有勇氣努力向前,這不是教育最重要的事嗎?
文.張天泰(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