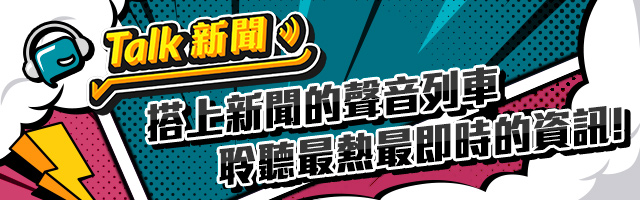前幾天,大甲鎮瀾宮媽祖9天8夜遶境進香昨天深夜起駕,有任職醫院安寧病房的護理師在臉書發文,透露她與同事將帶病患在定點等鑾轎,幫病患完成心願。她並感謝去年有賴信眾體諒,還有警方協助開道,讓阿嬤患者得以近距離看到大甲媽、安詳離世。此台灣護理師的正念義行、正心善行感動不少網友。
長老宗,亦可稱其為長老教會,源自十六世紀英格蘭宗教改革,為基督教新教的其中一個分支。
我的外婆是台灣護理師,今年76歲,已退休,成為基督徒有56年。其原生家庭並非基督教家庭,早年間由於外婆的家庭並不富裕,且生在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國中畢業後家中便不再給予她進修的機會,15歲就得開始工作,進入醫院擔任雜工。而在工作的五年間,偶會遭受到醫院內同事的刁難,且漫無目的工作讓她覺得人生了無意義,感到絕望。
外婆在20歲時,經醫院同仁傳福音,前往教會參加禮拜,半年後受洗,後積極參與周日禮拜。
22歲時,接收到有新生護校第一屆招生,只要繳學費就能就讀,便使用先前工作存下來的錢入學就讀,自此漸漸減少參加教會活動的次數,專注於念書,並以當屆第一名學生畢業,取得護理師資格,而後成功考取校護資格,工作生涯中結婚生子,在此期間也幾乎未參與教會事務,但偶爾會禱告。到2000年初期,由於發現罹患腦瘤(接受治療後便了無大礙),身體非常不適,身心備受煎熬,因此退休,而在其間受認識的牧師邀約,前往剛開幕的「六家教會」參加禮拜,後重新頻繁的參與教會事務,直至今日。
我認為教會內的氛圍十分輕鬆,感覺是非常正常的社交場所,很像是鄰里間的社交活動,實際上教徒們的談話內容也幾乎都是日常話題,不是基督徒的我在其中也感到十分自在。雖然他們有所謂的「基督徒七要」(天天讀經、常常禱告、勤赴聚會、努力奉獻、領人歸主、服務社會、為主見證),用以督促基督徒的行為,然而六家教會是鼓勵信徒「量力而為」就好,像有些人工作太辛苦,禮拜日很難早起,牧師也請他們先顧好自己身體就好,不用勉強。因此我對六家教會的教會活動有十足的正面印象,對我而言教會就是一個健康的社交環境。
除了外婆的教會生活探究,因外婆一生都是擔任台灣護理師,也讓我想探究台灣護理師的教育史;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國防醫學院、國際組織以及美援的介入,透過提供獎助學金至美國進修、專家來台交流與軟硬體設備的補助,台灣的護理體制,逐漸由德日制轉變成美式護理。美式護理在中國的發展可以從1920年協和醫學院成立的協和護士學校談起。初設立之前九年,協和護理科的入學程度是高中畢業,給予三年之訓練,修業期滿考試及格後給予「護士」文憑。1930之後,將入學程度提高至高中畢業,且要在設備完善的大學及指定之基礎學科肄業一年以上,並具備英文會話、閱讀能力者才能報考。學生如已在設備完善之大學肄業兩年半以上,修滿護理科課程後,除獲得護理科所發之「護士」證書外,尚有其原來大學所發給之「學士」證書。由於護理科之經費不與醫科成醫院經費相牽連,且設備完善,有各科的實驗室,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師資優良,實習材料齊備的狀況,不輸於歐美各國的護理學校。
協和護理系的畢業生多投入中國的軍護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係有「中國軍護之母」之稱的周美玉。周美玉,浙江人,1910年出生。1930年畢業於北平協和醫學院護理科,留校擔任協和醫院護理長。1931至37年間,參加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定縣工作,擔任該會衛生部主任兼高級職業學校校長。1933至1934年6月,曾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獎學金,至麻省理工學院進修,取得公共衛生學士學位。1947年,接任國防醫學院護理系主任。1948至49年,再度出國進修,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公共衛生碩士,以及哥倫比亞大學護理教育碩士雙學位。當時國防護理系的課程為四年半之訓練〈半年入伍,三年正科,一年實習〉,畢業後分發軍中服務。在這四年的護理學習課程,十個星期為一學期,一年共三個學期,70分為及格分數,參考書多為英文。
至於1945年之後台灣的護理界僅陳翠玉與鍾信心接受美式護理教育。戰後初期台灣醫院裡未有護理服務,護士僅進行量體溫、發藥、簡單的治療、換藥,跟醫師巡房,寫記錄,所有工作是依據醫師的指令,缺乏對病患的個人關懷,病患是由家屬自行照護。醫院環境也不佳,病人直接穿著自己的衣物躺在骯髒的床上,甚至可在病房煮食,甚至養雞鴉。每家醫院均有一位護理長負責護理服務,然而她只負責管理護士以及宿舍,醫院主管決定工時與護士的輪班以及工作的指派。1946-1947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尋求陳翠玉之協助,創辦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護理行政進修班,調訓全台各醫院護士長以上的護理主管,推行護理部的行政革新工作,著手訂定台灣護理教育制度,並籌備設立護理學校等計劃。
1948年台大醫院成立了護理部,陳翠玉擔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當時台大醫院仍保留日本制度,以每位教授為單位,各據一方,醫師高高在上,職權極大,護士在醫院內的地位仍然不清,從給醫師泡茶、奉茶,至患者的護理、伙食,包括買菜,全部包辦,彷彿是「萬能雜工」。1949年6月,陳翠玉就任護理部主任進行改革。她要求護士工作的調派與聘用,需經護理部決定後。為維護護士們的健康,改為英美式的「白班(日班)、小夜班和大夜班」三班制。設置護士長、護理督導、書記。向世界衛生組織要求派各科護理顧問來台。爭取獎學金名額,送護士長以上的護理人員出國進修。
1950年代台灣護理專業化的過程當中,美援、美國醫藥援華會、中華醫學理事會、世界衛生組織扮演重要的援助角色。美國醫藥援華會撥配各項援華醫事經費與各國內醫療團體,如國軍醫院、衛生單位、醫學院、護士學校。同時募集醫學專業圖書、期刊、解剖學及病理學幻燈片與百科全書,補充醫學院圖書不足的窘境。為迅速提升各校師資力量以提高醫學教育質量與水平,ABMAC以資助各校中青教師出國進修為主要活動方式。1950年代ABMAC仍延續對護理教育的關懷,如捐助經費購買圖書、選送人員出國進修,1960年代,則補助國防醫學院興建宿舍。
WHO與台灣護理界發展,最顯著者為1952年起,由WHO西太平洋區派遣護理顧問至台大護校,協助該校的教學。當台大護理系成立後,WHO這五位顧問仍繼續留任,而WHO也贈與台大護理系獎助學金,保送一些已於高級護理職業學校或護理專科畢業,有優良工作表現,且有教學興趣與潛能的護士,赴美進修,攻讀學位。
在美援的部份,根據1953年美援總署來台考察之報告「美援衛生計畫(U.S. Aid Health Program)」,護士教育之重要性名列第二,僅次於醫事教育。其因在於台灣的醫事教育支離破碎教學方法與課程被認為不及格,而與此相關的護理教育,因過往並未大力培植,因此要求台灣方面必須展開為期四年的完整護理人員訓練計畫。除了選派人員出國進修研習外,較大工程之興建,大宗圖書、儀器、設備之購置均有賴美援資助,其補助機關包含台灣大學醫學院、國防醫學院,台灣省衛生處及其所屬機關、公立醫院護理人員,高雄醫學院、台南護校、台北護專等。
國際衛生援助機構是美式護理得以進入台灣的背後推手。由於日治時期的護理訓練是以培養醫師助手為主,課程內容都是以疾病為主,醫院是訓練護士場所,師資以醫院醫師為主,而不是具備護理資歷的專業人員。戰後,遠赴日本、美國、加拿大學習護理,並於學成後投入台灣護理教育,對於台灣護理專業,以及護理人員的專業認同,均有極大的影響。
20世紀初,部分來台的女宣教士具有護理人員資格,「姑娘」是當時台灣社會對未婚女傳教士的通稱,由「姑娘」擔任護理工作是那時的常態。台灣特有的殖民時期——日治時代——「看護婦」制度,護理人員在醫院內的地位仍然不清,從給醫師泡茶、奉茶,至病人的照護、伙食,包括買菜,全部包辦,彷彿是「萬能雜工」,地位僅高於雜役人員。直到二次大戰結束(1949 年),「國際衛生援助機構」是美式現代護理得以進入台灣的背後推手,透過提供獎助學金至美國進修、專家來台交流與軟硬體設備的補助,從此,台灣護理始與世界接軌。
總言之,由台灣護理師的教育史探究,可以看見台灣醫療界是根本的父權社會結構性壓迫所構成,台灣護理界一直從屬於醫療界,至今仍然是醫療界的最基層主力;而護理工作源自人類母性本能,有性別差異,而性別差異又連結宗教「犧牲」、「奉獻」,形構了台灣護理界面對不合理不公義命運。
這種性別歧視被記錄在過去所有的社會制度中,嚴重影響護理人員個人及其職業;護理史,不僅僅是護理專業發展的歷史,其面向還包含女性在歷史當中的地位、醫學及健康照護體系中的父權主義、護理人員的角色扮演是源於母性、職業與性別的緊密關連、醫護關係即一種性別關係等;而政府、社會對護理人員的刻板期待和對護理議題的冷漠態度,正是反映過去社會大眾普遍對女性存有的刻板印象。
而外婆曾遭遇到醫院內同事的刁難,正是台灣性別歧視的時代脈絡,且當時漫無目的工作讓她覺得人生了無意義,感到絕望,但外婆因有基督教作為精神支持,讓我看到作為一個長老教會基督徒的台灣護理師所展現的堅毅力,外婆已用青春歲月貢獻台灣社會,我非常以外婆為榮,所以大學也選擇護理系就讀。
文.江晨揚(國立陽明交大護理系大學生)
張天泰(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