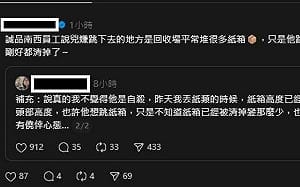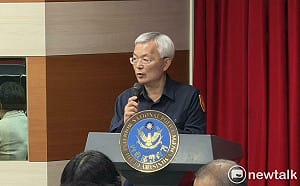「中國加油!還我釣魚寶島!還我船長!」一位身穿軍服在大街上高喊口號並大力揮舞著紅旗的青年,昔日街頭的熱血愛國主義者,如今卻成了時時抱怨中國社會、吐槽現實不公的「憤青」。
在《少年小趙》中,導演杜海濱將一個90後的青年從滿腹的愛國情操轉變為對現今中國社會心存不滿的過程記錄地十分細膩,也點出了現代社會因網路發達與資訊流通,間接造成城鄉間的資訊不對等,使得中國許多懷抱初心到大城市讀書的青年體會到自己對國家、對中國共產的主觀意識已不再像從前那般深信不疑。整部紀錄片對於中國青年如何反思覺醒刻劃細膩,使人印象深刻。
「憤青」是「憤怒青年」的縮寫,指的是中國國內一群不滿社會現狀的網民,通常具有非常強烈的愛國情懷且具有較激進的思想。近幾年來,中國憤青逐漸增長,原因很簡單:生活不順遂、社會經濟壓迫、中國政治疏漏。中國房價暴漲導致大城市內出現以青年組成為主的蝸居蟻族群體,以及政府財政方面的腐敗造成中國社會矛盾越來越多。而憤青多為市井小民,對這樣的時局感到憤怒卻又無法改變現狀,只能在網路上抒發自己對社會負面狀況的不滿。
不只是中國,台灣在這幾年間的青年憤怒現象也逐漸明顯,但台灣對於憤青的定義可以從「台灣憤青的愛國情懷上並非如中國憤青的強烈,兩岸青年對於國家的認同感程度的不同」來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從近十年來看台灣青年,台灣青年憤怒現象提高的因素主要和青年期待與社會現實落差有關。從1993至2013這20年間來看,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從6.3萬人升到22.9萬人,飆漲百分之兩百六十三;碩士畢業生更是從1萬人上升到6萬人,飆漲百分之五百,然而,台灣現階段市場職缺的釋出數量卻不敵高學歷的畢業青年數量,造成畢業生難以就業的問題。此外,根據勞動部的統計,2016年大學畢業生起薪約兩萬八,而碩士畢業生的起薪也只有約三萬三;若考慮到物價指數,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起薪也較十多年前倒退約百分之八點八。國內私立大學高學貸,造成許多學生在畢業之後仍長期承受著學貸壓力,而低薪的現況更是壓著這些青年喘不過氣,導致現在的青年多抱持著過一天是一天的心態,對未來沒有希望,也對政府的不作為感到憤怒無奈。
這一代的青年雖然相較於上一代生於教育及物質皆富足的世代,但也是薪資所得最低的世代,加上現在社會資源不平均的問題,青年對未來沒有希望也是導致後來爆發像是太陽花學運主要癥結點,青年貧窮導致他們對未來的恐懼與不安:M型化社會反應的貧富差距、買不起房子的青年越來越多。青年世代害怕服貿簽署後,台灣成為第二個香港,並且認為上一代佔領了較好的資源。這些資源並不會在社會中流通,反倒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這種情況也類似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所抨擊的關鍵因素。
面對社會問題,青年除了自力或依賴父母幫助,還可能依靠政府;但現在的政府似乎無法回應青年在畢業之後所面臨的不安與無奈。高中畢業後歷經大學、研究所,等到畢業後出了社會,發現社會的現狀不符合我們所期待的時候,就會產生失望和無力感,而這樣的心態可能導致青年政治冷感。而身處在網路時代,個人接受到的負面情緒容易在網路的同溫層之間散播,並且會在青年的同溫層中發酵及擴大。
雖然幾次的學生運動對台灣政治產生實質的影響力,但歷經這些後政府仍未針對青年對社會不滿的根源做出調整,高房價、青年起薪低仍是未被解決的問題。社會問題不是一時之間能夠解決的,但或許在未來,政府能在歷經過這幾次社會運動後理解新一代青年的思考模式以及青年的號召力,也使得更多人因為關注、參與及認同而對於投入政治參與感興趣,或甚至是對促進政府改革、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抱有期待。作為一個台灣青年,我認為現在台灣年輕人注重物質和具體的事物,包括我在內,對於抽象的精神層面較為不信任,像是愛國心。因為兩岸的長久以來的政治關係,導致我們對國家這個詞沒有安全感,但是我認為青年如果要改變現在的台灣社會,可以先從自己開始為出發點:充實自己且更要關注當前台灣的社會發展及國際情勢的演變,有一個「身為台灣青年即有背負新一代國家責任的勇氣和使命感」,且青年間的團結也可以使得台灣社會走向更美好的道路。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