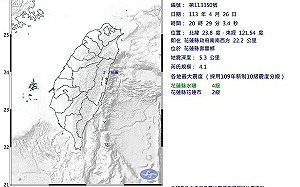文/秦晋
2014年1月12日下午4点46分,小弟弟金生抽泣着告诉我,“平生在10分钟前去世了”。只觉得心中一阵悲痛,痛得刻骨铭心,仰望苍天,倍感无奈,悲哀地长长叹息。平生的去世,给他的亲人——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悲伤和遗憾。


我1988年底离开中国,至今25年,其间只返回过两次,总共时间不超过40天。2013年中,我安排了两位弟弟在8月中下旬到台湾旅游观光,借此机会我们兄弟骨肉得以相见,主要目的是与平生相见。一切手续齐全,平生夫妇买好了机票,我也为他们订好了旅馆,只等到时候台北相见。恰在此时,平生体检查出罹患早期肝癌。平生倒是镇静自定,问中山医院医生,是否可以等他台湾之行回来以后施行手术,医生表示反对,动手术切除第一要紧。平生接受了医嘱,还宽慰地告诉我,因为是早期的,完全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命运真捉弄人,谁曾想,这次失之交臂,竟让2006年1月初我们兄弟的短暂的相聚与分别成了诀别。平生病情危急,消息传来,为了骨肉亲情,为了能在与弟弟平生天人永隔之际见上最后一面,我在1月2日走进了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要求与领事直接会谈,尽管在过去一年里已经有了连续三次申请中国签证被拒的经历。领事馆内一位年轻官员官员接待了我,听了我的口头陈述,留下了我递交的弟弟病危通知书,承诺将我的签证申请立刻上报。出了领事馆大门我就走入对面的签证服务中心加急申请签证。
1月7日上午,在递交申请3个工作日以后,我再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见了值班领事,并且递交了书面陈述。
本人郁文龙,持澳洲护照。在过去的一年中曾经三次申请签证被拒绝。我弟弟郁平生肝癌手术后状况恶化,危在旦夕。故1月2日(上周四)来申请签证,期望返回回中国见最后一面。我申请的是加急签证,至今没有信息。昨夜得知弟几乎离世,心急如焚。家人都在努力赶回中国。我自知个人情况特殊,希望中国政府网开一面,放行回中国以尽人道。本人长期持与中国政府不同政治观点,此番回中国,为弟弟与平生话别送行,不做此事以外的事情。
郁文龙(秦晋)2014年1月7日
值班领事告诉我,我的签证还是在等待之中,而且明确告知如果拒签不会给予理由,目前还没有国内上级进一步消息,同时还暗示我这次申请签证的结果估计与以前几次相同。
1月10日一早得知躺在病床多年的老父亲突然大口吐血。急急去中领馆再次要求签证,递交陈情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弟弟郁平生病情危重,在澳洲的直系亲属尽量返回中国上海,我加急签证去中国,至今已8天。昨日下午(1月9日)侄子郁洋去病院探视我的父亲、他的祖父郁家林,父亲已经很久不认人不言语了,昨日却认出了小孙子来看望他,居然有了反应,并且谈了一段时间话。但是今日凌晨却大口吐血,生命垂危。刚才接到弟弟郁金生的电话得知此厄讯。
作为家中长子,父亲生命垂危,根据中国传统的人伦排除艰险争取见最后一面。谨此通过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向中国政府再次恳请予以放行。本人感谢在先,感谢中国政府能够出于人本主义和道义原则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本人首先承诺,在中国期间不从事与请求放行给与签证事由不相关的任何事情。
郁文龙叩谢
2014年1月10日
见到的还是前一次的那位值班领事,我急急地把陈情书从窗口递交了给他,他接受了。但是签证准许与否仍无消息。
1月12日中国时间凌晨时分守夜的小弟金生来电,告知平生此时痛苦万分,不欲求生,只求解脱。我随即问是否可与平生通话。金生让平生接听,他神智清晰,可以感觉到,他听到我的声音是激动的,远隔重洋呼唤着我。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也许此时是我们兄弟间最后的声音交汇,也许是诀别之际,由于我的中国签证受阻,面见话别没有指望了。由于他这个时候病痛十分厉害,我对弟弟平生说了一些鼓励宽慰的话语,不忍心与他长时间说话,只能强忍着悲痛和悲愤。9个小时以后,弟弟平生离开了人世,死亡报告书上说是死于肾衰竭,得年仅55岁。次日1月13日星期一上午直奔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再一次书面陈情,要求去中国奔弟弟平生之丧。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我弟弟郁平生已经于昨日2014年1月12日北京时间下午1点30分许溘然长逝,得年55岁。
骨肉分离、生离死别是人世间的巨大伤痛,无人可免。1月2日我提出申请回中国与弟弟临终话别,签证申请至今未有回复,我与弟弟郁平生兄弟骨肉最后一面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是一个重道德伦理的国度,中国政府理应垂范。现在本人再次通过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恳请,予以放行返回中国上海奔弟弟郁平生之丧。同时看望一息尚存危在旦夕的老父亲生前一面。
本人再一次承诺,在中国期间不从事与请求签证事由不相关的任何事情。
郁文龙(秦晋)
2014年1月13日
这次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两位官员出来向我说明,其中一位女性官员诚恳地表示,他们完全知道我的紧急情况并且理解我的心情,一定继续报告国内“有关方面”,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我深知我的中国签证不由他们批准,必须上报国内“有关方面”。八年前返回中国,中国有关部门官员面有得色地告诉我:当我们获知你的签证申请,我们很有信心地放你入境,很快地批准了你的申请。因此我知道,当时我的签证由中国有关部门核定,而且做的不露痕迹,完全像是一个普通的签证,按规定的四个工作日及时发出。以今天的情况看来,这个情况没有变化,我获得签证去上海奔弟弟之丧由“有关方面”作出。这次“有关方面”不再像8年前那样信心十足,予以放行。我在无奈焦灼中等待。
1月14日,小弟金生按约与“有关方面”长期保持联络的魏先生就我奔丧之事进行了会谈。据弟金生的反映,魏先生对我家老二平生的去世表达了哀悼之情,也一定会向有关上级汇报我家所发生的情况,至于是否特别“恩准”我回上海奔丧,决定权在上,他无从知晓。金生告诉魏先生,平生的追悼会安排在“头七”日举行,也就是1月18日。如果中国政府有意愿对我放行的话,我应该在1月16日澳洲时间中午12点之前获得通知,这样方可坐上当天晚上或者1月17日飞机飞赴上海。过了1月16日中午12点,仍未得到签证批准通知,基本可以理解为“有关方面”对我处置是不予放行。但是还是怀抱一丝希望,通话上海的小弟,让他询问魏先生,并且委托金生向魏先生表示,基于对方工作的职责,多年与金生因我而发生的互动和往来,形成了双方的友善并且相互理解关系,我借此机会向魏先生表示谢意,对他的“以友相处”以及参加平生追悼会的善意表示欣慰,同时敦促弟弟金生接受魏先生这个善愿。我们也定存留在心,决不虚情假意,虚以委蛇。尽管没有得到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签证核准的通知,我对申请签证过程中相遇领事们表示我对他们的理解,应该说他们还都敬业,也有人情。
无奈之下上网找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留言板,贴上以下文字:
中共中央办公厅:
我是旅居澳洲的原中国公民郁文龙,1988年离开中国来到澳洲,由于持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政见而没有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延长和保留,现在持澳洲护照。
2014年1月12日,我的同胞弟弟郁平生不幸去世,而老父亲已经罹病卧床多年,状况也是危在旦夕。我于1月2日向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申请返回中国签证,至今无任何消息。弟弟的追悼会按照传统习惯将于1月18日举行。中国政府官方渠道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以及中国境内的国安或者国保系统对于我的签证申请都没有给与正面答复,本人迫不得已越级“拦轿击鼓”。寻遍互联网只在这里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留言板,不论效果如何,是否找对府第衙门,我只期盼升堂审理我的案子。
中国固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多以孝仁治天下。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中国是一个重道德伦理的国度,中国政府理应垂范,中国政府又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之下,其间的关系和顺序不言自明。
郁文龙(秦晋)
2014年1月16日
我不获签证奔丧,是立场的双方各自坚持。中国政府坚持了“春天般温暖、夏天般火热、严冬般冷酷”多种不同的区别对待,而我则坚持了对中国民主自由的追求始终不渝这条基本底线。
最后,我只能委托女儿在亡弟的追悼会上代我向弟弟平生做最后的道别: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对人生这么理解:人的生命有两层,一层是肉身,另一层是灵性。灵在人在,灵去人亡。肉身必然经过成住坏空,或者说生老病死。有的人长,有的人短,长的不足喜,短的也不足悲,都是命定。而灵性却是永恒不朽的,不停地在宇宙天地间循环轮回。天地无穷,人生短暂。我们在天地间获得人生,再长久也是短暂的。纵观弟弟平生你走过来的人生路,也是平安幸福的,夫复何求?彭祖八百,蜉蝣须臾,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都是万物各自造化。
为兄别无所能,一得世间高僧大德为你诵经超拔,二求上天金身诸神为你理天引领。弟弟平生你可迎着光明直飞而上,不复回还。其实为兄不应为你太过悲伤,实在是欠缺修持,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骨肉亲情所牵引。为兄人间凡尘心愿未了,待愿了之后与你相逢,一起遨游在天。
平生,我的骨肉兄弟,我们在人世间永别了,一路平顺好走!
痛定思痛,弟弟平生不幸早逝固然有其病理原因,但是其他相关原因不可忽视。平生很不幸,遇到的上海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医师王鲁是一位缺乏医德之人,也许他的医术不低。在平生手术前后摆出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以后平生因手术后发烧和体内存有积液几次去就诊他都置之不理。听侄子说起过这位王鲁医师甚至有一次竟然让平生拖着病体在做B超室等待6个多小时,然后居然很不耐烦地不看B超报告扬长而去,视病人为仇寇。如果我的弟弟平生在中国有钱或者有权,按照他的病情是可以继续存活下去的。只可惜他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无权无钱,只能忍受无德医师的傲慢。作为病人,心中的悲怨可想而知。平生的病情演变和恶化与王鲁医师的缺乏人性惘顾人命不无关系。令人悲哀的是,像这样一位披着白大褂替病人切除肿瘤的人,本身却因受社会风气的熏染成为社会的肿瘤。小弟金生的同事以他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告诉金生,现在的中国,医生有不少是缺乏医德之辈,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他们希望病人按照潜规则送红包,得了红包动手术,银货两讫,以后不再相干。
我上海的家人在服从医学界潜规则的时候缺乏远见,给了一个数目不大的红包,这就像西汉王昭君不贿赂画工毛延寿而被丑化远嫁北胡一样。我不知道以后平生不停的医治用药的花费是多少,做一下事后诸葛亮,如果大胆地把这笔花费有远见地如数给了那位缺乏医德的王鲁医师,也许能够获得他的用心医治,平生情况也许可有另外一个结果。
我哀悼弟弟平生,他去得如此匆匆,看着他去年春天时候露天起舞、唱着卡拉OK的欢快视频,已经昨是今非,不禁潸然泪下。我们之间的骨肉亲情,从小一起长大历历在目,仿如昨日。
我们家三兄弟,我老大,平生老二,金生老三,分别出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从小一起玩耍,一起成长。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是我们孩提时候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文革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校园向社会敞开,空旷的操场和草坪,成了我们这些儿童少年玩耍的地方。大字报是冬天时候烤火取暖的主要燃料,夏天的时候跳进校园内河嬉戏消暑,华师大大门外的篱笆墙总有几处被顽皮孩子扒成的可容一人钻进钻出小洞,这些小洞就成了校外孩童进入华师大玩耍的主要通行之道。最让我们喜欢的并且模仿是“地道战”里面的山田中队长和“平原游击队”里面的松井大队长,惟妙惟肖地学着样钻进我们搭建的“地道”,整天价日的一起游戏,好几十个孩子一起尽兴地从夏天到冬天,在从冬天到夏天,无所事事玩了一整年。最大的孩子67届初中毕业生,最小的就是我家还没有入学的小弟弟金生。我家三兄弟都在其中,今天想来好像就在昨天。
平生1965年进师大附小,1970年进师大二附中。我们俩既是兄弟,也是校友。平生进入中学以后,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平生从小身手矫健,打得一手很不错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在邻里街坊相近年龄段中没有对手。平生天生音色很好,很能唱,小的时候我们兄弟可以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所有唱段都能唱下来,并且把所有的台词都能从头到尾对下来。说真的,这不是本事,实在是当时我们可以娱乐的内容太贫乏,这些成了我们兄弟可以不需要代价的娱乐和游戏。后来听说他唱卡拉OK时总能得到不少掌声,很可惜,我们兄弟在一起尽情开怀唱歌的机会好像只有一次,1997年10月我从澳洲回到上海的那一次。
平生1975年中学毕业,进了上海“614”造币厂的技工学校,两年后毕业,被分配到上海“542”造币厂,一直工作到2013年7月被诊断出病状,前后近40年。平生的一生都是在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生活,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波动,比较安稳,所以养成了比较安逸平淡的习惯,不求发达,但求无过,平日里就是上下班,夫妻孩子乐乐融融。
自从1988年11月我去国澳大利亚,在逝去的25年间,我们兄弟仅相处不到40天,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更是一个悲哀和无奈。开始时候每年的中秋或者春节,我总会去电话问候在国内的父亲和两位弟弟,拾人牙慧地引用王维诗或者苏轼词表达对远隔重洋的亲人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如今已经不再。
我家三兄弟天然之性都纯朴,对父母孝敬,相互之间兄友弟恭。我们的母亲去世的早,母亲的早逝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没有母亲早逝,“风树之悲”也许不会在我们兄弟心中如此强烈,所以才会对父亲更加孝敬。话说过来,父母在不远游,但我还是远游澳洲,而且还回不了中国膝下尽孝,我的职责全部让两位弟弟承担了,他们俩争相为老父亲洗浴,看护着老父亲最后的人生旅程,为兄的我感到很是对不起自己的弟弟,尤其平生在手术之后,念兹在兹带着病体去看望老父亲,更让我感觉对他亏欠太多太多。现在弟弟平生竟然先于老父亲匆匆离世,留下老父亲由小弟弟一人守护。而我又关山阻隔,有家难回,有国难奔。不禁悲歌一曲:悲歌当泣,远望当归,思念亡弟,郁郁累累。欲渡河无船,欲归家无人,心思不可状,痛楚阵阵。
有一件事情我常提醒弟弟平生回忆,母亲去世前平生去庙里求签,据平生的回忆,当时庙里的方丈取出两支蜡烛,分别放在了父母亲的位置上,父亲的一支蜡烛点燃后火力强盛,一冲而起,而母亲的那支蜡烛就火苗微弱,很快熄灭了。我们的母亲几天以后就去世了,我们的父亲正如那支蜡烛所体现的那样,一直燃烧到今天,27年过去了,还在燃烧。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感悟到冥冥之中一些东西,尽管我们看不到。
我生活在澳洲,经常思考和摸索,对人生有了新想法,认识到了人的生命分两个层面,而普通人只看到一层,却不知道另一层。一层是肉身的,另一层是灵性的。肉身的必然要经过四个过程:成住坏空或者说生老病死。有的人长,有的人短,都不足为喜,也不足为悲。都是业力所致,不断地在宇宙天地间循环轮回。因为人的灵却是不朽的,所以人生不是从娘胎里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那一刻。
我们能成为兄弟,是累生累世因缘和轮回,缘聚而合,缘去而散。在一个家庭里的人与人,因为血缘和共同生活而产生了亲情,当分离的时候不免感觉痛苦。人的肉身如同衣物和皮囊,套在了灵上,一旦坏了,坏衣服或者坏皮囊就一定脱去,这个灵就要离去根据这一世人生的修为转去下一个地方。人生要潇洒写意,来去自如,平平静静,不带怨恨。天地无穷,人生短暂。我们在天地间获得人生,再长久也是短暂的。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生必有死,天地日月和人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息。
我家遭遇不幸,得到了闻讯朋友和同仁的安慰和激励,兹摘录几则:
秦晋
听到这消息非常替你难过,专心争取回国,希望你节哀,也祝愿你回国的努力顺利。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充分理解你的。需要我做什么,千万别客气。我17号中午到悉尼,不需要接待。如果你回国成行,请你告知我。
拥抱你!
开希
秦晋:
您好!
多年来和藏人有过来往的您,无需我多解释,人世间是“无常”的,就像我离开拉萨翻越雪山流亡印度的时候对未来有着各种创璟。事实上梦想不断的在破灭,父母先后离开人世,在西藏的亲人无时不刻期待着和我见上一面,一直都没有实现,表面上非常乐观幽默的我,内心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毕竟这个世界上最悲伤的莫过于离开亲人和故土,还好我们藏人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之所以我能够非常坚强的客服这些痛苦,勇敢地面对现实.........
因此,您在兄弟离世前该做的都做了,无需过度悲伤,要坚强的面对未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不是吗?
我也按照藏人的传统特习俗别为您的兄弟祈祷,嘱托印度和西藏境内的朋友们为他到寺院里供酥油灯,祈颂经文等。
达波代表也特别让我向您转达问候,向您的家人们致以问候,请您节哀顺变!
我也向阿底峡说了,他肯定会联系您的,毕竟您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
保重身体!
达珍
秦晋:
听说了,没敢打搅你,替你吃了三天素。
现实无法挽回,现实很是残酷,但是请接受现实,节哀顺变。
与虎谋皮,结果可想而知。心里有,哪怕山高水远,令弟在天在天之灵会理解你的。
你是坚强的,即便是偶尔袭来的脆弱,你依旧是坚强的。
保重。
xx
前绿党领袖Bob Brown、悉尼大学政治学教John Keane授、澳洲外交论坛主席Colin Chapman、我从事民主运动长期的支持者Sue Bloom和 Kerry Wright等通过邮件和电话分别向我表示了慰问和鼓励。在此也一并谢过。
Dear Chin Jin,
I am sorry I won't be able to catch up with Wu’er Kaixi. And that is terrible news that you could not visit your homeland when your brother died. A more humane China is coming, thanks to your good work and the work of others who believe in a free democratic China.
My best wishes,
Bob
秦晋,很抱歉这次我不能会见吾尔开希。当你的弟弟去世的时候却不能奔丧,这是一则非常令人错愕的消息。一个有情义的中国会来临。谢谢你的勤奋努力以及其他坚信民主人士的不懈努力。谨致以良好的祝愿。布朗
Dearest Chin Jin,
Please may I offer my deepest sympathies. The passing of one's brother, I know from experience, is very hard; but the insult of being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paying respects is unforgiveable. My thoughts are with you.
Let's meet as soon as I'm back from Berlin, on February 9th. Until then, my warmest wishes...John
最亲爱的秦晋,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慰问。根据我的经验,亲人亡故一定是非常的痛心,但是拒绝奔丧是不可原谅的罪恶。我与你同在。···最深切的问候,约翰
一位讲师宽慰我说:“你为弟弟已经做到了孝悌忠信,完全地尽了心”。弟弟平生匆匆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死非死者的不幸,乃是生者的不幸。我未能与弟弟最后一面话别,甚至遗容也未能一见。谁之罪?我不禁仰天长向故国期待月明中。
2014年1月22 癸巳年十二月二十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