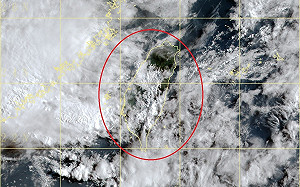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稱讚葉公超是一位「學貫中西的中國文藝復興人」。「文藝復興人」是一種極高的評價,讓人聯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但丁等人。20世紀的中國,承受得起這個評價的人,屈指可數如梁啓超、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人。在這群「中國文藝復興人」當中,葉公超述而不作、惜墨如金,沒有日記和自傳,雖多年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駐美大使等顯赫職務,其文學、學術和政治生涯鮮為人知。
旅居紐約的台灣學者湯晏,因喜愛艾略特及其詩歌,而關注到第一個將艾略特引入中國的葉公超,進而研究葉公超作為外交家的成敗榮辱,然後十年如一日地耙梳史料,爲葉公超寫了一本極具特色的傳記。湯晏認為,葉公超的一生出入於兩個世界之間,一個是文學和學術的世界,也就是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艾略特的世界;另一個是政治與外交的世界,也就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世界。
葉公超早年留美歸國,任教清華和西南聯大,講授英美文學,研究和評論艾略特的詩歌,即便在抗戰的硝煙裡,也弦歌不絕。在抗戰後期,葉公超跟胡適一樣棄學從政,投身外交事務。在國府敗退台灣前夕,又開啓10年外交部長生涯,代表台灣簽下《中日和約》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無人知道,如果葉公超沒有以學人從政,能否成就更高的文學事業;同樣也無人知道,如果沒有葉公超,台灣的弱國外交能否安然度過50年代。
「飛鳥盡,良弓藏」,國民政府在聯合國阻止蒙古加入聯合國的外交活動失敗之後,蔣介石以2道金牌召葉公超回國,隨即免去其大使職位,用艾略特的詩句來形容就是「烏雲卷走了太陽」。在半軟禁狀態下,葉公超鬱悶地度過了最後的20年。他孤身一人,與妻子感情淡漠,此前兩人長期分居,其妻留在美國加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當時,葉公超奉命回台灣述職時,連隨身衣服都未攜帶,還是胡適借給他衣服。1975年蔣介石去世之後,他才獲准出國訪問。再次回華府,已是17年之後的1978年,如同「白頭宮女在,閒話說玄宗」。
晚年20年的漫長歲月,連重返學術界、到大學教書的願望亦不能實現,比之同樣擔任過駐美大使、後來出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來更爲不幸。葉公超和孫立人,一文一武,都是深受美國和西方尊重的傑出人才,本是「國家的柱石」,卻遭「武大郎開店」的蔣介石嫉恨,不幸成為「國家的敵人」。孫立人長壽,活到兩蔣政權過去、台灣步入民主制度,在生前獲得官方的平反昭雪;葉公超個性激越剛直,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鬱鬱而終。
本書對葉公超晚年20年的生活一筆帶過,只有幾頁描述,誠然是一大缺憾。或許日后可以寫一本續集,如同《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那樣的《葉公超的最後二十年》。葉公超在其風華正茂的壯年時期,「飛揚跋扈爲誰雄」,其獲罪的原因是喜歡臧否人物、甚至「侮辱國家元首」。在晚年幽居歲月,他謹言慎行,不留下任何文字。傳記中記載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葉公超剛去世,蔣經國即派遣秘書長馬紀壯藉口蔣經國曾有一份重要文件必須送還總統府,到其寓所大肆搜尋,甚至開啓私人保險箱,卻一無所獲。蔣經國要找的不是什麽重要文件,而是搜查葉公超有沒有回憶錄或日記留下來。葉公超生前已料到會發生此種情況,所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過,這可苦了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
艾略特的世界比杜勒斯的世界美好
1926年,葉公超遊學劍橋大學,結識艾略特,但生性內斂的艾略特並未與這個東方青年有過深交。葉公超此後致力於譯介艾略特的詩文,10年後,葉公超的女弟子趙蘿蕤譯出《荒原》全詩。次年,《荒原》的首部中譯本出版,葉公超爲該書作序。在抗戰的離亂中,此書未能引起轟動,但在艾略特作品的中文翻譯史上堪稱大事。
以詩歌而言,如果說19世紀是丁尼生的時代,那麽20世紀就是艾略特的時代。胡適不喜歡艾略特,大概其性情單純務實、缺乏詩人氣質,讀不懂艾略特的敏感細密、充滿形而上學思考的詩歌。葉公超和徐志摩則激賞艾略特,他們觸摸到艾略特詩歌中對人類現代文明崩壞的先知般的預感。葉公超認為,艾略特的詩所以令人注意者,「在他有進一步的深刻表現法,有擴大錯綜的意識,有爲整個人類文明前途設想的情緒」。
艾略特很像王國維,他沒有像王國維那樣自殺,但在《荒原》中表達了對死亡與救贖的深刻思考。《荒原》開頭的題詞是:「因為我在古米親眼看見西比爾吊在籠子裡。孩子們問她:你要什麼,西比爾?她回答道:我要死。」艾略特自己說,他在政治上是保皇黨,在宗教上是英國天主教徒,在文學上是古典主義者。不過,他所信仰的天主教不是中世紀的天主教,而是被美國和英國的清教徒精神洗滌之後的現代天主教。葉公超沒有宗教信仰,他認為艾略特的重要性「不在他的宗教信仰」,這個思路讓他難以更深入地進入艾略特的世界。《荒原》以及艾略特的其他作品,都在有意識地模擬聖經的文體和故事,與清教徒時代的偉大詩人米爾頓的《失落園》一樣,揭示被罪所捆綁的人類的苦難狀態以及對上帝恩典的仰望。
如果葉公超繼續停留在艾略特的世界裡,研究、創作和講學,他在文學和學術上必定能留下更多著述。湯晏認為,「自文學革命以來,除胡適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像葉公超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刻意栽培了那麼多的人才」。這恐怕是傳記作者對傳主的過譽之詞。葉公超在學術和教育領域只停留了10年左右,且大部分時間都在抗戰的顛沛流離中,很難說有多大的學術成果、並培養多少真正受其熏陶的學生。錢鍾書和季羨林等人不過聽過他的課而已,並未傳承其學養和人格,此2人在中共政權下的種種表現都不堪深究。平心而論,在文化教育界的影響,葉公超恐怕比不上蔣夢麟、梅貽琦、傅斯年、羅家倫。艾略特的世界更有永恆的價值,可惜葉公超再也沒有回來。
另一方面,艾略特不僅僅是偉大的詩人,也是對政治和公共議題有真知灼見的公共知識分子。艾略特對「何謂民主國家」及言論自由等議題有深刻論述,本書似乎沒有論及這一部分,或許葉公超也未接觸艾略特此一面向。若是葉公超對艾略特這方面的論述有所瞭解,恐怕在投身政治活動之前,會有一番更為謹慎的評估。艾略特認為,民主表現爲議會政體,存在兩個政黨,一黨當政,一黨在野,不論當政或是在野,兩黨都不可歷時過久。「一個民主國家中公民的作用,在於爲了全體人民的美好生活而輪流執政。在一個民主國家,人人都應該懂得如何治理和被人治理。成為完全的統治者,成為完全被人治理的狀態,則可謂喪失人性。」以此衡量蔣介石政權,不就是一個「喪失人性」的政權嗎?
艾略特重視公民教育。他指出:「在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社會旨趣』應該意味著全體國民的思想和氣質方面可以分辨之處,它產生於一國的共同精神氣質,而這種氣質的表達,則要通過百家爭鳴的學術宗師,他們各持己見,有時見地相左。」反之,「在一個極權主義社會,『社會旨趣』可能意味的內容,會在少數當權者頭腦中形成公式,它是根據一種特殊的政治—社會理論演繹而來,通過各自手段強行灌輸和長期訓導,從而施加於人。」
葉公超在1928年與胡適、徐志摩等友人一起創辦《新月》雜誌,那段時期他不曾寫過政治評論,但他當然知道胡適等人發起的人權議題討論,由此導致南京政權對《新月》雜誌和書店的威脅、查封。艾略特曾強調言論自由之重要性:「在一個民主國家裡,科學家和學者以及藝術家,他們應該治理各自的領域:一部交響曲,居然被指爲立場偏差,或者一首描寫不幸愛情故事的憂鬱詩篇,居然背上失敗主義和思想頽廢的罪名,或者一種生物學理論,被指含有顛覆作用,這個時候,民主政體就無從談起。」這段話也可用來批判蔣政權對言論自由的戕害。
你不是轎夫,你是詩人
葉公超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之情進入政府外交部門服務。他在短短4年內從一名局外人升任外交部長而且連任10年,堪稱奇跡,但要說他在這個領域取得多大成就,恐怕還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首先,在專制體制下,獨裁者壟斷一切,正如湯晏所說,「在中國凡事大大小小都是由蔣介石一個人作主」——在中國大陸,蔣未能實現「一統江湖」,除了與共產黨和日本人周旋外,還要跟國民黨各個集團和派系調和折中;到了台灣之後,蔣終於成為小朝廷的獨裁者,可以獨斷朝綱了。在此背景下,作為職業外交家,要通過外交工作推動國家的民主富強,其騰挪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現代中國,個人才華的發揮受限於低劣的社會制度:中共常常炫耀周恩來是外交奇才,周只是毛的走卒;周恩來比不上葉公超,因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劣質;而葉公超比不上顧維鈞,因為南京政府比北洋政府更糟糕。
好的外交家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實現其淩雲之志。而民主制度之下,國民對外交事務亦有知情權。艾略特說的這段話,葉公超大概未曾讀到:「從前的外交政策在任何一個國家裡,無非是為數不多的人關注的事宜;但如今天下發生的一切大家都要始終關注,每個受過教育的公民都理所當然必須知曉。」葉公超從事的外交活動,哪一件不是服從老蔣的命令呢?即便明知老蔣的命令錯了,也只能違心地執行,然後在背後痛罵一番——厲行特務政治的國民黨,早已在他周圍安插了專打小報告的小人,葉公超對蔣的種種「大不敬」言論被搜集、記錄、匯報。之後,才有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葉公超口誅筆伐,稱之為「葉逆」、「葉奸」,甚至說「留美之文化買辦,凡長於洋語者,無不以一等奴隸自居爲得意」,將所有精通外語、有留美生涯的人全都罵在裡面。弔詭的是,蔣介石聘用日本人對付共產黨,日軍在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在其庇護下逃避戰犯審判、充任顧問。蔣敗退台灣後更是高薪招募日軍軍官組成「白團」,對待這些軍官比對待手下將領親密百倍。這難道還不算是「賣國」嗎?
其次,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之後,朝廷縮小了一百倍,外交也縮小了一百倍。葉公超作為風雨飄搖的小朝廷的外交部長,實在沒有多少外交可辦。即便他不被老蔣罷黜,單靠他個人在華府兢兢業業、廢寢忘食,也無法改變日后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美國及西方大國紛紛與中共建交的趨勢。正如歷史學者戴鴻超在《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一書中所論:「中國大陸是一個地廣人稠,具有龐大而未開發的自然及人力資源的國度。在國際政治的交易中,是一個很大的籌碼;蔣介石失去了大陸,便失去了這個籌碼。他後來据有台灣,在面積方面僅及大陸的千分之三,這籌碼是無可比擬地微小了。如果外交具有一種賭博的性質的話,蔣到台灣時,已輸掉他大部分的賭本;而他的對手中共、蘇聯及美國都擁有很大的賭本,他不可能獲得勝利。」葉公超輔佐蔣介石,只能勉強維持小朝廷的顔面,他在任時擁有大使的名頭和禮遇,幾年之後,他的繼任者只能屈辱地接受「妾身不明」的「代表」的處境。
湯晏過高評估了葉公超在外交上的成就和地位,他認為:「外交上葉公超和蔣廷黻是蔣介石手上的兩張王牌。蔣介石有一個遐想:認為葉公超、蔣廷黻是他的兩個轎夫,總有一天,他們會把他抬回南京中山陵。」蔣一生南征北戰,當然知道惟有靠武力才能回到中國,不可能單單靠外交上的努力。軍事爲主,外交爲輔,歷來如此。不過,「抬轎人」的比喻非常生動,葉公超是抬轎人,但他本質上是詩人,詩人要爲真善美說話,讓他閉嘴是不可能的。他對蔣介石不可能愚忠到底,他知道轎子上坐的是什麽人:「在與蔣介石接觸過的美國人眼中,蔣介石是個教育程度不高,國際知識有限的人,馬歇爾及魏德邁等人即認為蔣介石只是軍校高中生的程度。」而葉公超一旦逆龍鱗、說真話,厄運就如期而至。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非此即彼的悲劇命運
未能阻止蒙古加入聯合國,成為葉公超外交生涯的終點。但這是由當時的國際大勢決定的,非葉公超所能左右。進入60年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已搖搖欲墜,蘇聯將蒙古入聯案與非洲毛里坦利亞入聯案捆綁在一起,若台灣否決蒙古案,則毛里坦尼亞案也會遭否決。由此,10多個非洲國家就會遷怒於台灣,甚至投票反對台灣佔據的席位,要將其否決權連根拔除。此種嚴峻局勢,連一向挺台灣的美國都表示無能為力。葉公超認為,必要時在蒙古問題上可作出讓步。他的這一務實觀點,又跟其他論點聯繫在一起,如不反對兩國中國、主張削減軍費、限制特務和黨棍的活動、不要妄談反攻大陸等等。這些又都是蔣介石最忌諱的、不能觸碰的「神主牌」,獨裁者當然容不下任何有獨立思想的下屬。
蔣介石對蒙古入聯案的態度是「寧可玉碎,不能瓦全」,似乎有錚錚鐵骨。但當美國施加足夠大的壓力,蔣又軟下來。美方駐聯合國代表魯斯克對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說,蔣的做法是「政治自殺」,如果一意孤行,美方將「與台北不往來」。美方檔案記錄的措辭是「washing out hands off」(洗手不幹),這是非常不客氣的說法。蔣介石垂頭喪氣地接受了現實,未在聯合國對蒙古入聯案投反對票。這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自取其辱。
但是,蔣介石立即罷黜葉公超,以洩心頭之恨。他不敢直接對抗美國人,就用罷免美國人欣賞的駐美大使的方式來向美國人示威。這是何等幼稚、怯懦和可笑的做法。湯晏感嘆說:「在蔣毛主宰的海峽兩岸,其治術和帝王心態竟能與封建時代並無二致。」而絕大多數的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只能在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作出選擇;像哲學家張君勱和經濟學家張公權那樣既反對毛也反對蔣,在1949年之後選擇流亡美國的,少之又少。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獨裁者。毛澤東打敗蔣介石,只能說明毛比蔣更加殘暴、更加血腥、更加冷酷無情、更加不擇手段。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出席共產黨及工人黨代表大會時,在發言中大放厥詞,呼籲來一場核戰爭:「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一定還要多。」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里亞蒂在晚宴上問毛:「有多少意大利人會挺過原子彈啊?」毛很冷靜地回答:「一個都不剩。你為什麼覺得意大利人對人類而言很重要呢?」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訪華時,毛澤東再度鼓吹核戰爭,並說中國不怕死一半的人。
毛澤東有多壞,並不能反過來推導出蔣介石有多好。毛的這番言論早已爲天下所知,蔣建議美國向中國投放核彈卻不為人知。這個細節在親蔣的美國學者陶涵的《蔣介石傳》中也有記載。1958年10月22日上午10點,杜勒斯在台北與蔣介石會談。白天會談的內容兩國都未公布,但晚宴前的講話流傳出來。談及金門局勢時,杜勒斯說,用常規方法無法摧毀共軍炮火。蔣說,可以使用若干戰術性而非戰略性核子武器。杜勒斯說,任何戰術性核子武器,足以消滅共軍炮火者,至少同時消滅一百萬人,等同於廣島、長崎事件之重演。這時,葉公超插話說,使用清潔性(即無放射性)核子武器如何?杜勒斯解釋說,核子彈藥必須觸及地面爆炸,空中爆炸無濟於事。但既經使用地上爆炸的武器,必將殺害甚多生命。而且,敵軍有可能對台灣使用核子武器報復,「到時候什麽都不剩了」。杜勒斯的這席話將蔣介石嚇住了,蔣馬上改口說要「研究研究」。在與杜勒斯的談話中,暴露出蔣介石知識不足,對現代核子武器的殺傷力不太清楚。葉公超亦如此,他的本行是文學和哲學,而非政治與軍事。
湯晏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凡是對蔣介石有利的,未必對中國人有利。」對台灣人來說亦是如此。湯晏對蔣提出嚴厲批評:「蔣介石爲了生存和自己的利益,而與杜勒斯討論可能要用美國人的核子武器來殺傷二千萬中國同胞。試想在1百年、2百年後,歷史上如何評價蔣介石。如果蔣介石厚愛於中國,則根本不應該爲了自己及洋人的利益,與杜勒斯討論使用可怕的核子武器來對付中國大陸。」知道這個細節之後仍崇拜蔣介石,就是沒有心肝和缺乏理性。葉公超、胡適等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大悲劇在於,他們有一流的智慧,中國卻沒有華盛頓式的領袖。在帝王般專橫的領袖與瘋狂的民族主義民意之間,他們無地彷徨。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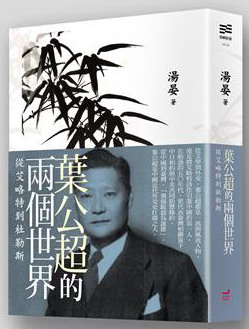
旅居紐約的台灣學者湯晏所著的《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 圖:翻攝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