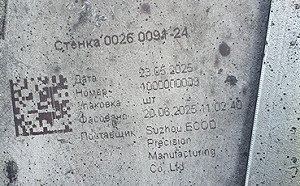地方首長卸任後命運大不同,有的更上一層樓,進入內閣,或者企圖角逐大位,但更多的是官司纏身,甚至逃亡海外被通緝。不可諱言,後者以國民黨居大宗,這與他們和地方長期以來千絲萬縷的利益掛勾有關;議會淪為政商命運共同體,檢調看情況辦案,媒體自動失靈。
全站首選:PO偵辦京華城案11檢察官潑血照涉恐嚇! 戴瑞甯、林惠珠羈押禁見
能當上縣市首長者,自然多非泛泛之輩,例如前雲林縣長廖泉裕畢業於台大電機系,在他那時代,可是多少理工科的第一志願,但卸任後因貪污治罪條例被雲林地方法院判刑兩年,廖泉裕卻在全案定讞前一天從桃園機場離境,雲林地檢署在同年9月30日發布通緝。
廖泉裕第二任縣長時,1995年12月號《遠見雜誌》 第114期(對,又是遠見)是怎麼報導他的?「曾是全國每人所得最後一名,廖泉裕要把雲林縣推向前三名,靠著大型工業區帶來的信心,廖泉裕早已抹去窮縣縣長淒苦的容顏,他相信,他會為雲林發展史留下一筆。」
結果是,陳定南不要的台塑六輕,就是廖泉裕為雲林縣爭取來的,猶記當時,廖泉裕及議長張榮味主動拜會王永在,甚至發動萬人遊行歡迎六輕在麥寮興建。這項政績,留給雲林縣民的資產,除了回饋金,還有空氣汙染、癌症村,抗爭悲憤至今不斷。
和苗栗縣劉政鴻一樣的命運,缺乏遠見的報導,是如何在地方政治中迷失?
高學歷、好條件的地方首長淪落至斯,地方議會又如何?筆者曾因為工作關係,拜訪中南部四個縣市議長,結果發現這四位議長都是大哥級的;議長之一的幕僚看過我們的拜會內容後,甚至淡淡的說,「我答應就算數,反正議長也看不懂」。
本來應該監督縣市長的縣市議員,在地方幾乎不分藍綠,一樣和樂融融。同黨的議員,宛如縣長的跑腿小弟,幫忙打點和接待。也因此,地方公務員根本不可能得罪這些議員,許多工程標案,議員公然介入之深,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更遑論什麼議會監督的代議政治。
國民黨來台後,扶植地方派系,使其互相牽制,為國民黨所用,因此而有所謂黑、紅、黃、白等派之稱;後來更有張派、廖派等等以姓氏為主的派系,各據一方。之所以如此,因為任何人選上縣市長後,大權一把抓,資源充沛,往往就是黑白通吃,統一天下。一旦下台,政亡人息,也就是被清算的開始。
劉政鴻卸任後,傳出監院及檢調要查他9年任內的預算浮濫的問題,但不管是大筆開銷毫不手軟以致負債648億,或者不當徵地、破壞古蹟和生態的事蹟斑斑可考,都非一朝一夕之事,為何卸任後才要來偵辦?難道是地方政商掛勾現象的最後宿命?而前仆後繼者,依舊絡繹不絕。檢調和地方首長的關係,更是耐人尋味。
台中金錢豹,以前附近就算有槍擊聲,通常不會上媒體,也看不到檢調介入偵辦的跡象。某位已經卸任的縣市首長,任內用一位由檢調系統轉任的親信機要,後來這位親信拿走了他10億元跑到海外,該首長卻連吭都不敢吭一聲。原因為何,不想可知。
國會殿堂上的立法委員都是由地方選出,但地方政治如此腐朽敗壞,如何想像從這種穢土中會產生優秀傑出的國會議員,為國家定出長遠發展的法案?而種種的問題,均由於整個地方政治是如此地不透明,即使在網路時代,依然停留在透過人脈網絡勾串利益的共生環境;光亮照不到的地方,如何能夠清除汙穢?曾經號稱田莊阿鴻的立委,後來會一路成為農地殺手的縣長,也就不意外。
坦白說,地方政治腐敗,無法清明,如果媒體失靈也該負責任的話,其實是最可哀憐的一環。因為,多少具有理想性格的地方記者,以前或還有監督政府、伸展抱負的機會,在置入性行銷大行其道之後,幾乎個個是戰敗的公雞,若不同流合汙,也只能黯然離開媒體;甘於從中大賺利頭的記者當然大有人在,他們成了政商檢調媒利益共同體的一環,但其角色,其實最卑微。
許多記者,無分地方或全國性媒體,他們即使不助紂為虐,卻也是幫忙誤導閱聽眾的共犯。五星級縣市長的頭銜,在劉政鴻之後,幾乎已成了另一種汙名,但其實從廖泉裕時代就已經發乎端、行之遠,只是如今才被發現如此狼狽不堪;不知以後的縣市長,還有多少人還想花錢買這頂發臭發酸的桂冠?
傳統主流媒體的經營者,對於地方新聞,不是棄守,就是無魚蝦也好,完全從商業方面考量,讓地方新聞成了點綴,不是凶殺命案就是連環車禍,這樣的媒體當然不可能監督地方的發展。台北雖然被稱為天龍國,但也因為媒體密度最高,一切都攤在陽光下,反而讓許多事情有了轉變的可能。
雖然媒體在整個地方利益共生的生物鏈中,最是卑微不堪,坦白說,在這幾個害蟲中,要翻轉地方,還是只能先從媒體做起,而且無法寄望傳統媒體,不是記者不行,而是媒體結構使然;反而必須由不受政商利益牽絆影響的地方公民或獨立媒體做起。
自己的新聞自己報,並非只是一個口號,而是阻止地方政客繼續殘害家園的一種迫切需要。在已往媒體壟斷的時代,這樣說,或許不切實際,但是公民奮起的年代,不僅可能,而且正在改變台灣的媒體和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