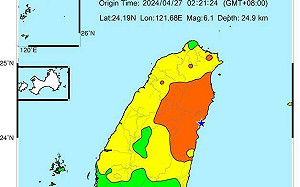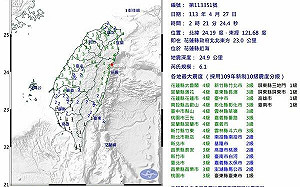在國際酒店內吧台喝酒的人,通常以歐美或日本人居多,因此不論在台北或國外,我總是吧台的「老外」,要嘛被認為是日本人。幾天前我在紐約The Carlyle酒店的Bemelmans Bar喝酒,那晚先後兩次被鄰 座的「老美」問道:你是不是住在這家酒店的日本客人?我微笑的告訴他們,I am Taiwanese;而在紐約,我還可以說我住在Downtown女兒家。
先是一對來自明尼蘇達州的退休夫婦到紐約親友家過感恩節,家就在Upper east side酒店附近這一帶。話題就從「你是否來自日本開始」(有如稍早的本地人總把來台的「老外」認為都是美國人)。滿頭白髮的Gary之前任職於美國Easter Air Lines,他 問我是否知道這家航空公司,我說我知道它曾經在70、80年代風光一時,但在90年代就「消失」的航空公司;他們很訝異我「知道」Easter Air,我說我也已滿頭白髮了,我們三人同時都笑了起來。 (Easter曾是美國「四大」國內線的航空公司,80年代末期發生多次勞資衝突,因清償債務於1991年關閉。當年我從Time雜誌陸續看到這段演變。) 他的妻子幾年前從學校老師退休。我告訴她,我在1970年代 曾教過5年小學,她很好奇問那後來呢?我說當時台灣在蔣介石的戒嚴時代,教科書充滿「不真實」的內容,我教不下改行當記者,曾採訪過旅遊新聞,因此對航空業略知一二。
約20多年前,他們曾經去過北京等地旅遊;又知道我來自台灣,他們問我對之前馬習會的看法。我說,我一向主張海峽兩邊要平等互動與交流,但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都是各自獨立自主的國家;就如同大西洋兩岸的英國與美國,縱使同文同種也不需要成為一個國家。這對過著悠閒退休生活的夫婦,曾歷經過冷戰、越戰時代,對台海問題並不陌生,也知道兩邊政體的差異。
聊到Bemelmans Bar,我說過去十幾年每次到紐約,總會到此喝個幾次,我們都喜愛Bemelmans那種帶有「鄰家友善」的氣氛;接著我們聊起紐約幾家國際酒店的Bar,如St. Regis,Gary馬上接著說The King Cole Bar。我 問他是否去過Park Ave.上Regency酒店改建後一樓的Bar,他說,還好(我也有同感)、很現代感。我問他是否去過東54th 街的Monkey Bar,他說,聽說過但還沒去過。我說那也是我常去的一 家,客人都是在Midtown一帶的白領上班族,餐廳的牆壁如同Bemelmans都是畫作,但題材都是當今美國知名的媒體人、影視人物、社交名流。
約6點過後,他們一離去,馬上就有一位年約50餘、滿頭灰髮的女士坐下來,她把一本厚厚的小說放桌面上,Tim走過來,還沒問她要喝甚麼,她就直接說Chablis。這是Burgundy北邊的一個產區,一款以Chardonnay釀出口感Dry,帶有礦物香、白果香的白葡萄酒;1980、90年代台北亞都曾挑Chablis做為House wine的一種,但由於Chablis相較一般白葡萄酒價位高,酒店基於成本考量,Chablis就不再用作House wine;更不用提,甚至台北其它國際酒店的葡萄酒單都未必有Chablis (多數的 答案是:台灣人不喜歡喝白葡萄酒,喝Chablis更寥寥可數,或許吧。)
酒尚未上桌,她就迫不及待翻閱這本新書;趁她喝第一口Chablis,我瞄了一下封面,原來是兩三個月前才出版,廣受媒體評論、推介的小說Purity(作者是Jonathan Franzen)。我曾稍微瀏覽一些書評,無法跟她聊這本小 說;但我很喜歡也喝過不少Chablis,我問她該瓶Chablis口感如何?她說,Wonderful。並回問我,你也喜歡Chablis嗎?接著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有趣吧,不到兩小時,就被問兩次「你是日本人嗎」,還好,不是被認為是中國人。雖然The Carlyle所 屬的Rosewood酒店集團在2011年被香港「新世界」集團取得經營,但The Carlyle的客人還是以歐美為主,至少在Bemelmans Bar我尚未看到「老中」的臉孔。
從她一件式簡約的穿著,也看不出化妝,加上直接點Chablis,我問她是不是住在酒店附近的常客,她說,她兒子住在附近,因為感恩節她從麻州劍橋住家過來與孩子相處幾天。問我住那裡,「幾天前,我陪剛生完產的女兒,帶嬰兒從台北回紐約Downtown的住家」她立即恭喜我做Grandfather,隨即從皮夾掏出兩個孫子的照片給我看,話題就圍繞在子女身上;我從iPhone秀出剛滿兩個月孫子的照片給她看,她一直讚美他的可愛。
彼此聊起子女的工作,我告訴她,女兒從NYU取得碩士學位後,就在紐約工作、戀愛、結婚。她說她也是NYU、經濟學系畢業,先生畢業於MIT。她隨即給我一張名片,她自創這家位於麻州劍橋的公司,頭銜是總裁,同時跟我解釋主要業務是為非洲許多國家的國營金融機構轉型為民營化與重整。我告訴他女婿畢業於耶魯經濟學系、哥倫比亞MBA,目前在紐約一家金融機構做事,她說她知道這家公司。(回家後我上網google,原來她是對非洲的銀行金融機構相當有影響力的人,她常被紐約時報、Business等商業新聞報導。我在Bemelmans Bar常認識一些在各行各業各有一片天的 人。)
當我回答她我是台灣人,她則告訴我她是愛爾蘭人,我順口說,難怪妳喜愛閱讀文學,諾貝爾文學獎最多的得主就是愛爾蘭人,我跟她聊James Joyce的短篇集Dubliners(都柏林人),及Jonathan Swift的 格列佛遊記等一些愛爾蘭作家。
接著她主動問我台灣在馬習會之後政治是否有什麼變化?我說,還是一樣,雙方各有自己的政府、軍隊,台灣人繳稅給自己的政府而不是北京。最重要的中國從未統治過台灣,台灣就像美國是一個移民建立的國家,雖然主要的人是來自大陸的漢人,不像美國是一個由多元種族建立的國家。但台灣從大航海時代就與歐洲有諸多接觸,就像英國人或愛爾蘭人的思維往外看;而歷來的大陸政權與人民多屬Middle Kingdom性格。 因此台灣人不同於中國人。但她問我,可是你們又不想獨立,我回答她,這可能是主政KMT與馬英九給外界的印象,明年總統換人,至少不會像馬政府一直往中國傾斜,台灣人的民主化與美式文化的普及化應該會與美國比較親近,我們都笑了起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