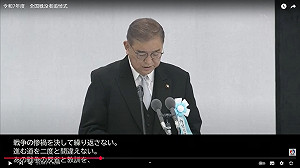此文為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於「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討論會」暨《蔣中正日記(1937-47)》新書發表會致詞稿
遠道而來的潘佐夫教授,前大使胡為真教授,本館前館長呂芳上教授,228紀念基金會藍士博執行長,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中心游惠容主任,參加新書座談的劉維開教授、薛化元教授、黃自進教授、陳翠蓮教授,各位與會的學者專家、愛好學術的朋友以及各家媒體的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
上個星期四,國史館在這裡舉辦紀念終戰80週年系列演講的第一場,當時我們就已公開說明,本館這次的紀念活動包括三種類型,就是(一)本館與臺灣文獻館共同主辦的六場系列講座,從8月延續到11月初;(二)8月15日也就是今天開始舉行三天的「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討論會」,以及(三)402室的小展覽「亮光與暗影:1945年前後的臺灣重要史料微型展」也是今天開幕,目的是希望能比較全面地與國人共同回顧與省思此一關鍵年代的歷史。
敏感的朋友可能會發現,上面說的似乎漏掉交代今天的新書發表會,的確,陸續出版兩蔣日記是我們這兩年的既定工作,不適合納入什麼紀念活動;不過這次出版的1937至1947蔣中正日記,恰好涵蓋中日戰爭8年以及戰後2年,與我們這次研討會的時間斷限相吻合,所以把新書發表會一起來進行不但不違和,而且還能相得益彰才是。
等一下我們邀請做主題演講的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教授,他的大作《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Victorious in Defeat)》,這本書的特色除了充分使用俄文和英文檔案,並且大量引述蔣中正日記,相當能夠呈現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例如他談論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互相承認「滿州國領土完整性」以及「蒙古領土完整性」,顯然對中國很不友善,史達林且在克里姆林宮對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1880-1946)說,他堅定支持軸心國、反對英美,但是兩個月後,納粹德國就攻擊蘇聯了;另一方面,同年4月,美國羅斯福總統雖然允許美國志願飛行員加入陳納德飛行大隊,而且派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來當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但是羅斯福還是準備要跟日本「和解」,不料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襲珍珠港、又去攻擊香港、新加坡(英屬馬來亞),於是英美立刻對日宣戰,第二天12月9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同時也對德國和義大利宣戰,從此中國戰場開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而且影響到,接下來有26個反法西斯聯盟的國家在1942年1月1日發表〈聯合國共同宣言〉,其中所謂「四強」即美、英、蘇、中簽名,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是簽在第四個位置,根據1月3日蔣日記記載—應該是宋子文轉述—羅斯福當場對宋說:「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蔣介石在日記接著說:此言聞之,但有慚愧而已。)
在這新的情勢下,羅斯福邀請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這個戰區除了中國,還包括東南亞部分地區,從蔣介石日記可知,他是在1942年1月2日覆電給羅斯福,「允任中泰越區統帥職之電」;這段經過,潘佐夫教授描述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影響重大,就引述蔣介石的日記說,英美海軍在太平洋戰場的損傷嚴重,「英美此後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決遠東之倭寇,否則英美仍視遠東與中國為次要也。」潘教授評論蔣介石當時的心情:「心情複雜,既感到同情,也有點幸災樂禍。」
以上,我為了介紹潘佐夫教授的大作,特別選這一段歷史,一方面介紹他如何使用各種史料,包括蔣介石日記,可以發現日記在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要說,中華民國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應對日本的侵略,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進入全面而持久的抗戰,主要都是蔣介石在領導,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英成為同盟國關係,局面才開始改觀,同盟國最後贏得1945年的勝利。這幾天我們國史館紀念活動的消息見報以後,立刻有某些媒體、網民(甚至國臺辦的發言人)批評我們使用「終戰」是一種媚日的態度,不直接用「抗戰勝利」是在迴避或曲解歷史……這樣只看標題就攻擊,雖然反映了社會分歧、政治對立的現實,但我們認為是不必要、對我們也是不公平的。
個人在8月7日本館與臺灣文獻館合辦系列演講的第一場開場致詞就說,我父親是雲林鄉下的農夫,在日治時期曾經去南洋當軍伕,所幸因眼疾提早回來臺灣,林內鄉有多位軍伕沒這麼幸運、死在南洋;我從1950年代出生到60年代成長過程中,常聽到家父使用「日人時代」、「降伏(こうふく)」以後如何如何,起初我以為他講的和我們在學校講的一樣是「光復」以後如何如何,因為臺語發音類似(日語發音也是類似),事實上「降伏」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說話、「光復」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說話,實在南轅北轍。這是生命經驗不同使然,應該互相尊重。何況,今天很多人習慣講的「終戰」,字面意義就是戰爭結束(the end of the war),算是中性的意涵。
若要問我個人的意見,我當然認為日本從1931年就開始的侵略中國是不對的,那是從幕府末年到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對中國的認識,從敬畏、學習到輕蔑、歧視的轉變,那是明治政府、戰前政府對內壓制臣民、對外藉著「戰爭」這種國家暴力推動殖民統治、奴役別的民族所造成的結果。最近我讀一本日本學者纐纈厚寫的《何謂中日戰爭?》,他批評戰後很多日本人不承認1945年是敗給中國,而是敗給投下原子彈的美國。
他反駁的理由,是計算1941年太平洋戰爭之前投入中國的日本陸軍有138萬(佔65%),1943年因應美國反攻而抽調一部分去太平洋戰場,仍有128萬(佔44%)在中國戰場;軍費方面,1941至1945年中國戰場415億(佔57%)、南方戰場184億(佔25%),總之1945年日本敗給中國,是從1931年開始持續不斷的所謂15年戰爭——這樣長期的戰爭所決定的。只因戰後日本迅速與美國建立了親密關係,成為「從屬於美國」的政治經濟架構,這個政治過程減少了日本與亞洲各國接觸的必要,也不必透過與亞洲國家的外交來修復彼此的關係。總之,日本不像戰後德國那樣承擔虐殺猶太人的責任,那樣自我揭露戰爭罪行,那樣修補與鄰近國家的關係,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老實承認「敗給中國」這個歷史事實。
這位日本學者還說,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攻擊,使日本自身擁有強烈的受害體驗,進一步促進了日本從加害體驗中解脫,這也是消除了「敗給中國」這一認識的原因之一。作者最後呼籲:通過不斷努力加深歷史認識,我們才能獲得正確地引用歷史和以史為鑒的資格,歷史認識是對過去事實的把握和反省,同時又是對未來方向的啟示。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作為戰爭的受害者)在戰後就開始新一波爾虞我詐的內戰,國共雙方都需要外在力量如美國和蘇聯的奧援,沒有餘暇向日本追究責任,也是重要背景。後來在紅色的中國,常常宣傳抗日戰爭的勝利應歸功於共產黨的努力,顯然也不是歷史事實。但是中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是值得繼續研究的重要課題,國史館修纂同仁這次有十一位參加編纂蔣中正日記(1937-47),我要求他(她)們就各自編輯的範圍,對國共關係做了摘要彙整,有機會再與大家分享。
簡單說,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不得不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沒有繼續剿匪、開始與中共合作抗日,但國共雙方一直是既聯合又鬥爭,起初一兩年聯合較多,後來則是鬥爭較多;正面戰場當然是蔣中正領導的國軍與日軍對抗,「敵後戰場」則是國、共軍及其游擊隊都有,據張玉法院士的研究:「1937至1942年間,國軍及國軍游擊隊在敵後戰場佔優勢,1943年以後,共軍及共軍游擊隊在敵後戰場佔優勢。這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無法有效接收與復員的最大原因。」換言之,國共雙方在敵後戰場的首要目標是擴充地盤、其次才是抗日;共軍為了擴充地盤,常藉著抨擊國民黨不抗日,以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號召更多支持者,使得攻擊國軍或國軍游擊隊的行動「富有正義性」。
當初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的藉口之一是「反共」,結果不但使得蔣中正停止剿共、必須與中共「合作抗日」,而中共藉著八年抗戰壯大自己,進而在戰後的國共內戰藉著蘇聯的協助(以及政治宣傳成功等因)獲勝,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共產國家——日本侵略中國而造就了一個共產中國的誕生——實在是歷史的一大諷刺。另一方面,蔣中正領導全面抗戰,應邀參加開羅會議,最後與美英蘇同盟打敗日本,同一時間且參與創立聯合國、中華民國成為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些事蹟在中國歷史的角度而言當然是重要功業,不容抹煞。然而在2025年的臺灣,回顧八十年前亦即1945年的鉅變,能有什麼不同角度?
國史館今天開始的〈亮光與暗影:1945前後的臺灣重要史料微型展〉就是想要處理這個:當時臺灣一方面有不少知識分子因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而歡欣、而歡迎祖國,接受「光復」的說法,另方面因中華民國政府缺乏現代性,粗魯接收、治理失能,不到一年半就發生二二八事變,展覽中有一節標題是「融入與扞格:臺灣人菁英的困境與二二八事件」,我們挑選林獻堂,王添灯和吳新榮的事例和日記為例,別的段落也有相關的臺灣人日記,可以作為時代變化的見證;我們在展場也整理了蔣介石在1947年3月涉及二二八事件的日記,我在十幾年前參加張炎憲館長召集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撰寫團隊,特別飛去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抄寫蔣介石1947年的日記,就用這個來論證蔣介石的責任。今天恰好出版的就是1937至1947年的日記,在場的年輕朋友,你們不必再飛去美國抄日記了。
另外,1991年史丹佛大學出版第一本研究二二八的專書就是以《悲劇性的開端》(A Tragic Beginning)作為書名,是甚麼時代的開端呢?可以說是臺灣的「中華民國時代」的開端,後來民主化以後被稱作「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開端。這個開端包括美國方面基於開羅宣言的承諾,協助國軍佔領臺灣,有一種「共管」的態勢,這也是美國政府為何在二二八事件中作「壁上觀」的原因,必須到1949年末、尤其1950年初韓戰爆發,美國才改變立場,透過舊金山和平條約對臺澎地位做了特殊的處理。這次的「重要史料微型展」只是要呈現臺灣1945的複雜性,要避免一廂情願的單方說法,不是要提供所有問題的答案。我們要呈現的不只是國府的觀點,還包括美國的、英國的、日本的以及具代表性的臺灣人菁英(如林獻堂、吳新榮、楊基振等等)的觀點。
402室正在展出的「1945前後臺灣」的重要史料,其中有王育德先生的女兒王明理女士最近捐給國史館的史料,就是1975年王育德有感於那位匿居印尼山林三十年的臺籍日本兵(史尼育唔/李光輝/中村輝夫)返臺以後,沒有受到臺日雙方政府應有的重視,而成立「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透過法律的政治的社會運動的手段,奮鬥了12年才獲日本國會通過每人兩百萬日圓弔慰金的補償,可惜王育德已經在1985年(法案通過的兩年前)去世。王育德先生是在1947年228事件之後逃去日本,他的哥哥王育霖律師就是臺南228的受難者。我們要尋求以臺灣為主體的戰後史觀,就不能不注意這樣的事件。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明天和後天共有24篇論文在這裡發表,這24位學者接受邀稿以後,分別就自己近年的興趣和心得撰寫了論文,應該可以客觀呈現臺灣學術界在這個領域,現階段的研究成果,這部分的意義讓大家各自發掘、各自領受,我就不必多說。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史館長陳儀深 照片:國史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