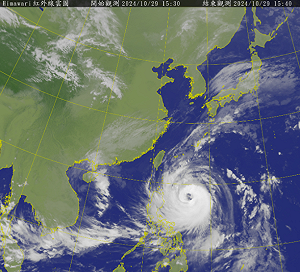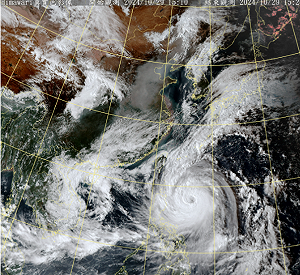美術課被借去上「國文」(中國語文)或英文課,應該是許多台灣人共有的經驗。而四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台灣」更是在教育中被極小化也被輕賤了。而正如數年前的遊戲/電影「返校」告訴我們的:被學校等國家機器所壓迫埋葬的,不只是美術本身與台灣相關知識、更是反抗、自由、創造的靈魂。
召喚自由靈魂與創造能量的強大法器
蔡潔妮博士的新書《書寫一部台灣美術史:一段爭議的政治進程》正是我們返校認識台灣美術的最佳讀物、也是召喚自由靈魂與創造能量的強大法器。
全站首選:快訊》中選會人事同意:主委游盈隆過關、藍白封殺3親綠委員
如前述,台灣性被中華殖民體制全面壓迫,藝術部門也不例外。尤其雪上加霜的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公,本土民眾往往更需要掙扎求生,不敢致力於追求文化藝術等、不易快速變現的志業,許多家庭甚至連購買顏料樂器都有困難(文學活動的物質條件相對沒那麼嚴苛)。
投身藝文活動的本土人才較少,讓(原即握有大權的)殖民統治者更能壟斷發表作品與評論的機會。隨著時代進步,漸有更多本土人才投入藝術活動,但華殖集團仍然掌握主要的話語權,本土藝術創作者也常陷入「台皮膚、華面具」(註一)的窘境。
本書作者投入十多年的心血,深入眾多美術與與社會科學資料、訪談多位相關人士,為連續殖民下的台灣美術歷史做了完整的記錄。而由獨到視角所提供的理解觀點,是發展真正屬於台灣的藝術所必須、也對建立自尊自信的台灣國族有所助益。
全站首選:卓榮泰終於秀赴日4張「自費」單據!包機費用208萬元
因為本書作者在相關領域的學識、投入的心力都遠非筆者所能望其項背。除了讚嘆,筆者無法做任何補充;但筆者身為二二八受難者遺族、精神科醫師,有些感受與聯想願在此分享。
藝評家對國族創傷主題的敵意
本書第六章「國族創傷下的正義被去合法性」,詳細地討論了二二八美展及其遭到的批評攻擊。書中提及:因為政治禁忌,二十世紀末才出現較多紀念台灣國族創傷的公開展覽,因為以二二八相關者為大宗,因此作者統稱為二二八美展。
筆者的外公劉家榮是在二二八屠殺中殉難的台灣菁英,但因為殖民壓迫,這個人這件事都成為禁忌;家母不被允許懷念慈父、我們兄弟無從得知先祖的風采。
二二八紀念活動 重建過去連結與自信
解嚴後逐漸出現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包括紀念音樂會與美展藝展,對我們而言有以下的意義:招魂、慰靈、哀悼、重建與過去與前人的連結、重建家族名譽與成員自信。
然而,遲到數十年的哀悼儀式,卻受到許多蛋頭學者藝評家的扭曲與攻擊,這正是對死難者遺族(也是受難者)的二度傷害。
如同本書的敘述,這些批評有幾個論點:違背藝術自主性、畫出排外的界限、忽略女性的存在。本書作者都已經提出了精采的批判,但我也想以我的方式,接續地提出反駁。

首先,藝術自主性指的是「評論藝術品優劣時、只應考慮作品藝術價值」(姑且不評論此信念是否正確),而非「創作藝術品時、不應有其他目的、不應追求其他價值」。
如果如上所述,文藝復興三傑為信仰而創作的聖母子圖、最後的晚餐、創世紀…,林布蘭與梵谷回顧個人生命的自畫像、寫實主義畫家描繪庶民生活的畫作,乃至與二二八紀念作品最相似的哥雅《1808 年 5 月 3 日的槍殺》、畢卡索《格爾尼卡》…不也都沒有藝術價值、甚至不該出現了。
自稱沒有其他動機 往往對自己動機毫無反省…
而且,我從事心理相關工作多年,深知「人類行為必然有多重動機、也受到多重因素影響、雖然可能本人沒有察覺」。人類創作藝術品,即使並非有意追求財富名聲社會理想這些明顯的外在動機,也必然同時在處理內心的其他需求。
自稱單純沒有其他動機的作品或評論,往往是對自己的動機毫無反省、或是不敢公開自己的可恥動機。
例如,藝評家看似中立地高舉「藝術自主性」(還是錯誤解釋)批評二二八美展,可能是在掩飾自己的冷血、對台灣人的輕賤、對華殖宰制結構的依賴。
真要強調「藝術自主性」,那麼這些以「創作者政治動機、女性主義、作品出自狹隘的國族主義」來批評二二八相關藝術作品的評論家,才真正違反了「評論藝術品優劣只應考慮作品藝術價值」的原則。
女性遺族的苦難只是父權壓迫?
也有些學者藝評家標榜女性主義,攻擊二二八美展的作品總是以男性為主角、忽略女性的苦難。甚至狂言:女性遺族的苦難來自父權壓迫、而非來自大屠殺事件。
「苦難來自父權壓迫、而非來自大屠殺事件」的說法是可笑的。這就像對性侵受害者說:「你會有心理創傷,是因為受到階級壓迫(or 因為貞操觀念)、而不是因為你被性侵。」
就以我的家族為例,如果外公不死於二二八,我外婆就不會成為受人欺凌的寡婦、家母就不會成為失怙的孤兒、家中的財產就不會被殖民官員巧取豪奪。怎麼能說她們的苦難與屠殺無關呢?
而且,指責二二八美展忽略女性並不公平。正是因為長期言論禁忌,遲至五十年後才能公開舉辦紀念美展,而紀念大屠殺總是從死者(多為男性)開始、之後才會談及其家人親友的苦難;「獄外之囚」的出版就是證據。
而所謂的或是偽裝成女性主義者,無視於這些女性悼念亡夫亡父的心理需求、否定相關美展最初的努力與貢獻,又反對二二八美展繼續舉辦、斷傷這些受難女性成為畫作主角的機會…可以說:正是因為這些標榜「女性主義」的學者藝評家、受難女性遺族承受了二度傷害。
假稱女性主義 攻擊台灣國族主義
很遺憾的,這種「以女性主義為武器、偏重攻擊台灣國族主義」的現象,並不只限於當年的二二八美展。
究其實,各政黨、各種國族主義運動、階級運動…中都看得到性別壓迫,但中國國民黨與僞台灣民眾黨明顯比本土政黨嚴重,而天朝主義左派的民陣(人民民主陣線)可能最為嚴重(檢討性侵受害者),但總有些進步女性主義者只放大檢視台灣國族主義團體。
另一種對二二八美展的批評,則是指斥這樣的美展出自狹隘的國族主義,辦展就是粗暴劃定界線、排除他者(中國流寓者)。
然而,身無殖民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對大屠殺的受害者群體說這話,就像是加害者指責性暴力受害者「太重視身體界限」,是極度殘忍且無恥的批評。而且,作為曾經遭受大屠殺、語言文化也持續遭被壓迫的群體,建立界限與群體意識、藉以凝聚自保的力量,是理所當然的。
相對的,殖民者曾指責本土台灣人為日奴、並大規模虐殺本土人士、持續剝削並貶抑受殖者文化;所謂學者無視於此更粗暴的劃界排他行為、而嚴厲批評未曾傷害他者的台灣國族主義,豈不可笑。

後殖民理論學者無視台灣殖民處境
在本書第六章(前段所提「國族創傷下的正義被去合法性」)看到幾位研究後殖民理論的知名學者,他們都無視於台灣本土族群受到殖民壓迫的事實、反而對解殖實踐(包括本書所述「視覺藝術的解殖實踐」)多所攻擊。
之所以如此,或可舉(被視為台派的)某作家近十年前的說法為例,他反對「中華民國對台灣殖民統治」,因為:沒有殖民母國、「殖民者與受殖者明顯的外表差異」不存在。
殖民:外來者對在地族群的制度性壓迫
但是,殖民行為的定義是:外來者對在地族群的制度性壓迫;持續存在的殖民母國、殖民者與受殖者的外表差異…都不是必要條件。
事實上,遷佔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都已被學界討論已久、甚至有專門期刊,在這兩三種類型的殖民狀態中,經常不存在殖民母國、也經常不存在「殖民者與受殖者間外表差異」。(註二)
然而,前述的錯誤說詞(否認「台灣受到 ROC 殖民統治」)卻得到許多知識青年贊同,或許說明了:
無論是大學生或知名學者,只要本身對壓迫無感(或許身屬殖民者群體)、習慣了殖民結構、甚至已在此結構中獲得權位與利益,就可能以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自我蒙蔽、否認殖民壓迫的存在。
甚至,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當權者(政界學界或藝文界)也會打壓任何挑戰不義結構的論述。
因為挑戰流行論述、可能引發爭議,本書/論文被法國學者高度肯定;回到台灣,本論文卻因其爭議性被學術期刊拒絕刊登,或可印證前段所述的論點。
兩大展藝評圈賤斥台灣性
在本書的最後兩章,作者以威尼斯雙年展與台北雙年展為例,討論近三十年來台灣藝術圈的權力移轉、描述發表與評論的權力,如何被牢牢掌握在小圈子手中。
你不孤單 看不懂台灣拗口的藝評
這個小圈子透過特殊的「評論寫作風格」打造評論的權威,寫出一整批讓人「看不懂」的藝術批評,多使用拗口複合的文法、一大堆模糊的引用文獻,連留美藝術家史筱筠也自承看不懂:
「……我後來其實都不太看藝評了,因為反正看不懂,或是跳著看,然後一直覺得自己有閱讀障礙。」
在此同時,這小圈子也嚴防台灣性出現在兩大展中、或是以輕蔑的態度將任何的台灣各色都稱為「地域性」或「自我東方主義」,同時卻毫不質疑其他作品出現的中國特色、自豪作品或展覽中的「國際化」。
不存在沒有地域性的國際化作品
這裡的荒謬不只存在於對台灣性與中國性的厚此薄彼,也在於基本邏輯:「國際化」正是建立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交流,沒有地域就沒有國際;正如不存在沒有個別特色的「普世標準人」、沒有地域性的「國際化作品」也不可能存在。
身為精神科醫師,書中的描述讓我想起 Melanie Klein 的理論「妄想分裂形勢」(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以及相關的自戀(Narcissism)。
為討好國際藝評圈,掌握藝評話語權的小圈子必須否認本身必然有的「地域性」、並將之投射至生存環境中的他者「台灣」(相對於小圈子習以為常的「中華」)、再附贈一個看似更有學問的負面詞彙「自我東方主義」。
其實是中華藝評人以傲慢的態度貶抑台灣、將台灣邊緣化他者化;也就是說「中華藝評人如同西方殖民者、以『東方主義』的方式對待台灣」,卻把自身的「東方主義」栽贓給台灣,稱之為「自我東方主義」。
自閉的中華性將台灣他者化
這樣一來,兩大展藝評圈就可以自我感覺良好、可以宣稱與國際接軌,忘記本身更為自閉且地域性的「中華性」、且以自我否認的方式完成另一種「自我東方主義」。
這小圈子的自戀、自閉同時展現在幾個方面:抱著優越感看待台灣、拒絕接觸現實中的台灣社會與人民(或以高度抽離的理論框架來代替真實的接觸)、拒絕以聽得懂的語言來溝通。
這也符合本書作者貫穿全書的分析架構:在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情勢,殖民者以不同的方式操弄「中國性」「世界性」「台灣性」三者,藉以維持「中國性」的優越地位、「台灣性」的從屬位置。也就在這裡,我們仿佛夢迴當年(如本文開頭所描述):學校裡沒有台灣、或者只被視為鄉土語言,而美術課被借去上「國文」或英文課。
作者:陳俊光,台灣精神科專科醫師。竹東二二八受難者劉家榮的外孫,他沒有因為這段經歷而逃避政治,反而更加勇於面對,從野百合學運到反大埔徵收都有他的影子,並在大埔事件之後,進行了政治暴力下的心理創傷研究。
註一:「台皮膚、華面具」:概念來自 Franz Fanon 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書中描述: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因為政治社會的不平等,黑人常有意無意的認同白人、否認自己的「黑人」性,就像戴了白人的面具;而這種現象又近一步鞏固了白人的優勢地位。本文作者在 2009 時,引用此概念寫了「台皮膚、華面具」一文,文中用詞與描述現象或許已有變化,但整體統治結構並未被解體。
註二:「殖民母國」(metropole)是相對於「殖民地」(colony)而言,但並非「殖民行為/主義」(colonialism)所必須。可以說:先前某作家主張「有母國才可以稱為殖民」,其實是混淆了「殖民地」與「殖民行為/主義」。
「從自在國族到自為國族」一文有更完整的討論,包括本書中重要的觀念「從自在國族到自為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