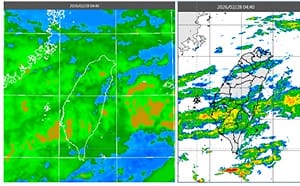圍繞美國主導提出的「和平理事會」構想,國際社會最核心的疑問並非多了一個處理衝突的機構,而是這樣的機制是否正在改變過去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安全治理慣例。答案其實同時存在兩個方向,在形式與法理層面,和平理事會並未完全凌駕聯合國,在實質運作與權力配置上,卻已明顯偏離多邊體系原有的設計邏輯。
從法理結構來看,和平理事會並非完全繞過聯合國而存在。相關安排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框架下成立,授權範圍以加薩走廊的戰後穩定與治理為核心,並設定明確期限與任務邊界。這讓美國主導的機制在國際法形式上仍具正當性,也避免直接挑戰聯合國憲章的法律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和平理事會並不是一個脫離聯合國的非法組織,而是一個掛靠在聯合國授權之下的特殊安排。
問題出現在實務設計與權力運作層面。和平理事會的組成方式與決策邏輯,已不再遵循主權平等與集體決策的原則,而是引入高度交易化的制度門檻。草案設計中,成員資格與席次長短與出資金額直接掛鉤,永久參與權被明確與高額資金承諾綁定,決策權隨財力集中。這樣的結構,讓和平理事會在運作上更接近企業董事會,而非以公共責任為導向的國際組織。
這種轉變也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角色出現微妙位移。安理會仍然負責授權,卻逐步退出實質治理核心,從衝突處理的中樞,轉為為他國設計的機制提供合法性背書。過去安理會即使陷入僵局,至少仍是唯一具有普遍性與法理權威的安全決策平台,如今卻面臨被功能性外包的風險。
加薩走廊成為這套新治理模式的第一個實驗場。和平理事會被賦予對停戰監督、重建資金、治權安排與去軍事化的整體統籌權,實際上主導了戰後治理的關鍵方向。地方社會與既有政治實體在決策結構中的位置相對邊緣,治理權力集中於由少數國家與政治人物主導的理事會之中。這樣的安排,雖然以效率與穩定為名,卻讓和平逐漸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由外部管理與資本運作維繫的狀態。
對多邊秩序而言,真正的衝擊不在於是否需要改革聯合國,而在於改革的方式是否正在改變國際治理的價值基礎。當和平機制開始以出資能力決定參與深度,當治理權力由少數人長期掌握,聯合國長期累積的普遍性正當性便被逐步侵蝕。聯合國沒有被正式取代,卻在實務中被降格為眾多權力平台之一。
從台灣視角觀察,這樣的轉變具有高度警示意義。國際秩序正在從以規則與程序為核心,轉向以效率、資金與政治影響力為導向的治理模式。和平理事會是否成功運作仍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加薩走廊已成為一個象徵性節點,標示出全球安全治理正從安理會模式,滑向董事會模式。這不只是中東問題,而是整個多邊體系未來走向的縮影。
對關心規則為本秩序的國家與社會而言,關鍵不在於支持或反對某一位政治人物,而在於是否願意接受一個以財力與個人權威為核心的平行安保機制,逐步改寫原本以國際法與普遍性為基礎的聯合國架構。這場關於和平理事會的爭論,本質上是一場關於全球治理未來形態的選擇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