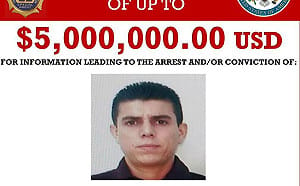2025年12月19日台北捷運張文隨機殺人案,讓人聯想到的,並非單一犯罪的震驚,而是日本學界多年來反覆提醒的一個核心命題:暴力往往不是突發,而是社會情緒長期累積、卻未被制度承接的結果。在日本對無差別攻擊的研究中,重點從來不只是「兇手怎麼了」,而是「社會如何讓挫敗無處安放」。此一視角,對理解台灣近十餘年的隨機殺人案件尤為重要。從鄭捷、洪淨到張文,三起案件橫跨十年,卻共享某些結構性的相似條件:高度孤立、失序的人生軌跡與一個缺乏出口的挫敗感。我們應該關注的,並非只是個人心理狀態,而是制度如何界定問題、如何切割責任,以及哪些情緒被視為「不屬於任何單位處理」。
在台灣,失業、挫敗、精神困境分別被交由不同制度處理:就業是勞動政策,精神健康是醫療,犯罪是司法。當一個人同時卡在這些制度縫隙中,沒有任何一個系統真正承接其困境時,暴力便成為一種被錯誤理解為「最後出口」的行為。這樣的結構,與中國近年頻繁出現,而被網民稱為「獻忠事件」的隨機殺人現象,有著令人不安的高度相似性。中國的「獻忠現象」,並非只是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在政治高壓、經濟下行及言論封閉下,情緒長期被壓縮的結果。當不滿無法透過制度申訴、公共討論或社會支持被轉化,只能向內爆發反噬。不同的是,台灣即使擁有相對開放的社會條件,但若制度持續忽視情緒累積的風險,將挫敗個人化、病理化,那麼「隨機暴力作為宣洩出口」的錯誤想像,便可能被複製。
然而,暴力的門檻,並不只來自個人處境,也受到整體社會的情緒氛圍所影響。從日本與中國的案例可見,當官方長期煽動仇外、仇日情緒,暴力的心理門檻即被降低。2024年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刺殺身亡,正是仇恨外溢的悲劇後果,這起事件並非孤立個案,而是發生在中國多年「仇日教育」與民族主義動員的背景之下。因此,我們不禁要提問:仇恨是如何被制度化?在中國,歷史教育、影視作品、官方敘事與社群平台,共同生產了一種高度簡化的敵我想像。當仇恨被包裝為「愛國情感」,暴力便不再顯得那麼不可思議。深圳事件後,中國官方一再強調「個案論」,否認仇日教育的存在,這正是典型的制度切割:將結構性情緒問題,重新推回個人犯罪。值得警惕的是,這套情緒動員模式,並不會止於中國境內。透過社群平台、短影音與認知作戰管道,仇恨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可輸出的政治技術。近年中國官媒與網路社群大量製造仇日、仇美敘事的同時,也逐漸將台灣納入「敵對想像」之中,倘若這類情緒被有系統地向台灣社會輸出,疊加本地既有的挫敗與不安,其後果不容低估。
台灣社會往往低估「情緒治理」的重要性,我們習慣在事件發生後,討論刑責、死刑存廢與個人背景,卻很少提及:哪些情緒被制度性忽視?哪些仇恨被默許存在?又有哪些平台與話語,正在降低暴力的心理門檻?當外部的仇恨敘事,遇上內部無處安放的挫敗感,隨機暴力便不再只是「偶發」。因此,從張文乙案來說,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或許並非只是單一無差別攻擊事件而已,而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台灣是否準備好承接情緒?若我們繼續將暴力視為個人失控、將仇恨視為言論自由的邊緣現象,忽視制度如何生產、放任或輸入情緒,那麼隨機殺人恐怕不會止於個案,而會成為一種被錯誤複製的社會病徵。因此,暴力從來不是突發事件,它總是在被忽視的地方,慢慢累積。能否正視這一點,將決定台灣社會是繼續在事後震驚,還是開始真正處理那些尚未爆發的情緒。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