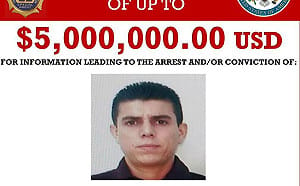近月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在國會表示「若中國對台動武,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導致一連串中日外交風暴。2025年11月9日,日本媒體報導高市首相的這番言論,引發各界高度關注。隨後,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堅於11月8日在社群平台X(原Twitter)轉貼相關新聞,並寫道:「那種擅闖進來的骯髒頭顱,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斬掉。你們做好覺悟了嗎?」這段文字被廣泛解讀為針對高市首相的人身威脅。該貼文雖隨後刪除,但11月10日日本政府以「極端不當言論」提出正式抗議。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媒體與多部會,也對高市首相的「台灣有事論」發動聯合譴責,並警告若日本介入台海可能導致「慘敗」。而日本方面,首相並未收回言論,官房長官亦強調將持續抗議。
這場從國會發言-社群恐嚇-正式外交抗議-媒體與官方共同放大的一連串事件,不只是一次外交失控,而是一套制度化邏輯在運作。若不從制度 (institutional) 的角度分析,只看表面言論與情緒,只會忽略其深層動因與後果。以下,我們或可從建制的觀點來分析,指出這種「狼式外交」如何被制度化,如何成為一種可複製的治理工具。中共對日本的施壓,已發展成一種「複合治理工程」。此一結合人身恐嚇、訊息策略與制度誘因的混合機制,其核心在於:「誰在生成文本、誰在放話、誰為之背書、誰因此升官」。這無異於建制觀點的日常行政實踐,而非全然是抽象的「民族主義高層動員」(那只是宏觀敘事的一部分)。真實運作的是:在外交部、總領事館、官方媒體、公務員升遷評價制度等制度內部,有一條被默認甚至鼓勵的路徑,通往「強硬、對抗、恐嚇」。
首先是「文本生成與放話機制」,薛堅的網路發文並非個人情緒發泄,而是有先後脈絡的政治展演,其內容與時機都緊接高市早苗的國會發言,且馬上被日本與美國政府與媒體注意,足見其背後有預設的政治投放目的。中國外交部與國防部等多部會隨即針對「台灣有事論」聯合放話,將之上升為全面警告;其次是「官媒與輿論機制」,在這場風波中,中國國內媒體與官方傳播結合,不再僅限於傳統外交聲明,而加入強烈敵意與人格攻擊元素。這不只是簡單的宣傳,而是系統性的訊息策略:透過歷史敘事、主權模糊點、領土爭議,將「國家利益」以情感與憤怒包裝,使公眾認同一種對外敵意。這種輿論攻勢,不再是偶發,而成為體制內可以調動的資源;再者,是「官僚激勵結構」,近年來,國際媒體與觀察者不斷提到某些中國外交官因為其「敢言敢鬥」而獲得晉升。例如,過去被批為「戰狼式」的官員,在其任期結束後,被調任更高職務或特別代表,成為制度內可見的「升遷路徑」。這告訴我們:在中共體制內,外交官是否「合作協商」,可能不及其是否「對外強硬、鬧事」來得重要。因此,薛堅這種赤裸裸的人身威脅,不只是外交失禮,而是制度所容忍(甚至默許)的政治展演。這種「暴力語言」是可以被寫入考核、升遷條件而成為官僚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制度安排,堪比軍艦巡航或軍事演習更具長期破壞力。
此外,中共這樣的一套制度化敵意機制,若從建制的觀點而言,我們不應僅把注意力放在新聞標題與外交官言論而已,值得探問的是:哪些內部文件、指令、考核制度,指引外交官使用粗暴語言?哪些審批流程、誰在背後決策允許這種言論公開化?官媒發文與外交部聲明間有哪些協同機制?此類行為被如何衡量、如何納入官僚晉升或政治資本的考量?唯有透過進一步深層的考究,才能真正理解這種「狼式外交」並非意外,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然而,我們不難理解,中共的目的其實是雙重的:對內,中國正處於經濟下行、房地產債務、地方政府債務、人口老化、青年失業等多重壓力之下,官方若僅專注於內部改革,不僅成本高、見效慢,也可能導致體制合法性危機。而更便宜、更快速、更能產生「凝聚」、「情緒出口」的,即是轉換內部矛盾為外部仇恨,藉由「日本威脅論」和「外部壓迫敘事」,將國內不滿重新導向「外敵」,這不只減少了國內壓力,也凝聚了當局的合法性。對外,這種制度化敵意能在短時間內產生震懾效果:一方面迫使日本、以及可能關切台海的第三方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另一方面,也試圖告訴國際社會,中共有能力、不畏懼且願意動用不同層面的工具-從社群媒體恐嚇、經濟制裁(例如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呼籲公民避免赴日旅遊)、旅遊限制、文化交流中斷等,形成一種低度但廣覆蓋的壓力。這正是複合治理 (composite coercion) 的典型特徵。
然而,這條路線帶來的,是對中共自身外交與戰略空間的長期傷害。每一次粗暴言論、每一次人身威脅,都在積累對中國的「制度性不信任」。對外國而言,中共不再是一個可以談判、有制度性及可預測的對手,而是一個可能隨時因情緒、因內部邏輯而爆發的「危險黑箱」。當一個國家成為如此,他國就更傾向於降低合作、提高警戒,並將其列入安全範疇,此可由最近日本與美國因中國在沖繩、東海及太平洋附近的軍事動作,而加強防衛合作與聯合演習乙事足稽。再者,制度化敵意使外交官變成政治機器,其不再是談判者或斡旋者,而是挑釁者與壓迫者。這樣的制度設計,把外交從理性溝通變成仇恨生產。當制度鼓勵「恐嚇升官」,下一代外交官也會習得這種語言與行動方式,外交人員儼然成為制度化仇敵製造者 (institutional enmity producers)。最終後果,或許不是戰爭爆發,而是「亞洲秩序的制度僵化」,在這種架構下,中日、中美、中台之間不再有互信,也不容易重建合作。每一次對話,都可能因過往的「言語恐嚇歷史經驗」而變得懷疑與對抗。
綜上所述,管見認為如果國際社會(特別是日、美、台),要對抗這種制度化敵意,不應僅依賴外交斥責或經濟制裁,更需要透過公開中國外交、媒體與官僚制度操作資訊,使得恐嚇、仇恨、生產敵意的機制暴露在全球觀察者之下;國際間也應考慮長期制度耦合(institution-building)來建立地區安全架構,讓合作、互信、對話成為制度化、常態化,而非因一時言論高潮而破裂;最重要的是,增進文化與話語防禦(discourse defence),加強自身媒體素養與公共外交,用理性、透明、尊重歷史的敘事回應,而不是落入對方「仇恨-反仇恨」的陷阱。如果我們只把這當成一連串外交事件,就永遠停留在「今天罵一句、明天反罵一句」的惡性循環,但如果看成制度問題,就有可能中斷這條製造敵意的結構,讓未來的亞洲秩序至少有合作、對話與妥協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日關係的危機,不僅是地緣政治的震盪,更是我們能否讓制度變回溝通工具,而不是仇恨機器的試金石。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