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珍古德(Jane Goodall),並不只是懷念一位自然學家,而是在回望一個人如何改變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她的一生,讓科學更有溫度,也讓人類重新學會謙卑。
在1960年代之前,科學界深信「人類獨一無二」:只有人類會製造與使用工具,只有人類擁有文化與情感。然而她改變了人類對動物的理解,在非洲的岡貝森林裡,26歲的她以驚人的耐心觀察,記錄到黑猩猩會折樹枝撈白蟻、分享食物、展現母愛與悲傷。這一發現推翻了學界的教條,也動搖了人類自居為萬物之靈的輕慢。從那一刻起,科學被迫承認「人並非自然的主宰,而只是生命長河中的一支延續」。
在她之前,研究動物多依賴捕捉、解剖與短期觀察。她開創了全新的研究方法,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她長年駐守叢林,給每一隻黑猩猩取名,而不是冷冰冰的編號;她用共情去理解牠們的情緒與社會結構,以觀察、理解、尊重取代測量、控制、支配。這種以個體到群體、從行為到文化的觀察,被視為現代靈長類學與動物行為學的分水嶺,也讓動物有個性與文化成為可以被科學驗證的命題。
1960年代的科學界仍是男性的堡壘。她讓科學突破性別與學術的壁壘,她既非名門出身,也沒有大學學位,卻憑直覺與勇氣被劍橋破格錄取為博士生。面對冷嘲與質疑,她用成果回應,不靠權威,不靠儀器,而是靠長年與自然為伴的真實經驗。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女性不能做科學」這種偏見的最有力反證。
珍古德沒有停留在論文,她讓科學走入社會與行動。1977年,她創立珍古德研究協會,推動靈長類保育;1991年,她發起根與芽計畫,讓全球青年參與環保。她從科學家成為行動者、教育者與聯合國和平使者,讓保育不再只是專家語言,而是人類共同的信念。
珍古德用一生留給世界的啟示是,我們並非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動物有情感、有文化,值得尊重;環保不是抽象理想,而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在氣候危機與生態崩壞的時代,她的聲音依舊溫柔而堅定的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人,究竟是自然的破壞者,還是守護者?」。
珍古德的偉大,不僅在於改寫科學,更在於她讓我們重新理解「做人」的意義。她用一生告訴人類:謙卑,不是退讓,而是一種更深的智慧。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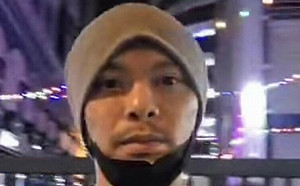


![11/29-11/30 [流量政治學第二屆營隊] 免費報名參加](https://images.newtalk.tw/resize_action2/300/album/project/1/69033cad7782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