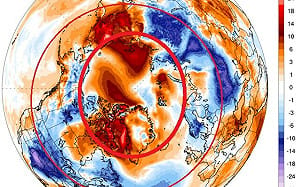留下來的是語言:漢娜鄂蘭專訪(上)
許多不是唸哲學系的人對哲學感興趣,我也是。唸大學時對存在深感困惑不解(當然現在還是不太瞭解),因此就會閱讀關於存在主義方面的哲學書籍,結果越看越疑惑,不過這樣的疑惑是有形狀的,比較能清楚而非模糊的發問。當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閱讀到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的一小部分作品。雅斯培問說,為何偉大不能與清楚在一起?意思是為何偉大的思想都必然是晦澀難懂、深不可測?所以他打破過去哲學家那種獨善其身的傳統,走出來接受電台與電視台訪問,用生活語言、具體的例子談抽象的思辨與道理。
雅斯培談世界公民、真理與溝通、存在與理性。眾所周知,漢娜鄂蘭是雅斯培在海德堡的高徒,兩人並維持終生的友誼與持續的對話。雅斯培的哲學思想對大思想家鄂蘭有深遠的影響。
雅斯培說,「政治的概念是建立在多數、多元與相互制衡上,而在政治空間裡,自由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政治現實。」對政治概念與現實的瞭解,使他的論述不流於空泛,這個特色在鄂蘭的作品也可看到。鄂蘭在《黑暗時代群像》(鄧伯宸譯)論雅斯培,感覺也像在談她自己的理念。
我們看到鄂蘭誠實勇敢地進入公共領域,充分實現其主觀才能,也就是說,她的作品、講學、演講是她實實在在的活動與聲音,而這就是向公眾證明她活著的結果。同時如雅斯培所言,公共領域也是一個精神領域,其間所呈現的就是人文,她的思考與書寫增加了人文厚度。
康德曾說:「一篇哲學文章的難度究竟是真正的艱深還是僅屬於小聰明所製造的煙霧,只要從它被接受的程度就可以見真章。」
我個人覺得對某一領域的深度探測,就像爬高山,攀上頂峰會遭遇到的艱深過程是很真實的,這種真實的艱深會吸引願意對存在進行冒險的人,更何況其間的奇花異草、雄偉的美景常讓人喜悅、驚顫,甚至靈光一現若有所悟。
我在2013年10月10日看完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後回家上網意外看到1964年10月28日漢娜鄂蘭接受德國記者高斯(Gunter Gaus)專訪的影片,這是個難得一見的經典訪談,從中我們看到鄂蘭誠實熱切、智性火花四射的風采。影片是德語發音,有英文字幕(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高斯:以妳的高知名度與受到的尊崇,妳覺得身為女性在哲學圈是不尋常或特別的嗎?
鄂蘭:我恐怕要抗議。我不屬於哲學圈。我的專業是政治理論。我既不覺得自己是哲學家,也不相信已被哲學圈接受。不過你開場白提到的其他問題,像是哲學一般都被視為是男性的職業。這種現象不會一成不變!將來女性當哲學家是完全可能的。
高斯:我認為妳是哲學家。
鄂蘭:你要這麼認為,我也沒辦法,不過我自認不是。我早已與哲學一刀兩斷,如你所知,我學的是哲學,不過這並不表示我要跟它在一起。
高斯:可否請妳更精確闡明政治哲學與妳做為政治理論教授之間的差異。
鄂蘭:我避免「政治哲學」這種說法,政治哲學載負傳統極大的重擔。不管是學術或非學術,當我說到這些東西,總會提到哲學與政治之間的張力。這種思想人與行動人之間的張力並不存在於自然哲學。跟每個人一樣,哲學家能客觀看待自然,當他說出對自然的看法時,是一種客觀的普世看法。但是當他面對政治時,他就無法客觀或中立。從柏拉圖就這樣了!
高斯:我瞭解妳的意思。
鄂蘭:多數的哲學家對所有政治都懷有敵意,僅少數例外。康德是個例外。此種敵意對整個問題極為重要,因為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這個主題的本質。
高斯:對政治的這種敵意妳不願參一腳,因為妳相信這樣一來會干擾妳的工作。
鄂蘭:沒錯,對這種敵意我不願參一腳!我要以不受哲學遮蔽的眼睛注視政治。
高斯:我瞭解。現在讓我們把話題轉到女性解放,這對妳一直是個問題嗎?
鄂蘭:是,當然,這類問題一直縈繞著我。事實上我一向都有些老派,認為某些職業並不適合女性。女性下命令看起來不佳,若她想保有女性特質,最好不要把自己放到這樣的處境。我不知道這樣的看法對還是不對。我向來或多或少無意識,或說或多或少有意識地依此生活。問題本身在我個人生活遭遇裡不扮演任何角色,我一向做我愛做的。
高斯:妳的作品相當重要,因為內容是關於政治行動與行為所依據的知識。妳會想要以這些作品達到廣泛的影響嗎?
鄂蘭:你知道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必需非常誠實地說,我是這樣說:當我在書寫時,對於我的作品如何可能影響別人並不感興趣。
高斯:那完成後呢?
鄂蘭:那就完成了。我注重的是瞭解。對我而言,寫作乃在尋找這種瞭解,是瞭解過程的一部份,某些東西因此得以有系統地表達。如果我有極佳的記憶力能將所思考的每樣東西記住,我非常懷疑我會寫作!我很清楚自己的惰性。我注重的是思考過程本身。一旦能夠把事情想通我就很滿足,如果能把思考過程恰如其分地寫出來,我也會很滿足。你問到我的作品對他人的影響。帶點反諷地說,影響力是男人的問題,男人總想要很有影響力,不過我視它是一種表面。我有沒有想像自己有影響力?沒有,我只是想瞭解。又如果別人所瞭解與我的瞭解一致,也會讓我滿足,有如在家的感覺。
高斯:你下筆容易嗎?你型塑概念不費力嗎?
鄂蘭:有時容易,有時難。不過通常是除非思路順暢,否則絕不下筆。
高斯:直到妳想通了。
鄂蘭:是。我完全知道我想要寫的才下筆。通常是一氣呵成,快慢取決於我打字的速度。
高斯:妳對政治理論、政治行動與行為的興趣是妳目前作品的中心。就此觀之,我發現妳與休勒姆教授的通信似乎特別有意思。這當中妳寫到:「妳年輕時對政治與歷史都不感興趣。」鄂蘭女士,身為猶太人,1933年妳26歲時出走德國,是否妳對政治的興趣以及不再對政治與歷史無感,與這些事件有關?
鄂蘭:是,當然。1933年不再可能無感。甚至在那之前已不再可能。
高斯:對妳也一樣?
鄂蘭:是,當然。我熱切地看報紙。我有意見。我不屬於任何政黨,也無此需要。1931年我就確信納粹會掌權。我與其他人爭論這點,不過一直要到出走後我方能有系統地思索這些東西。
高斯:對妳剛剛說的我有另一個問題。若說妳確信納粹掌權已不可擋,妳不會感到採取行動加以阻止的必要嗎?比方說,加入一個政黨,或者妳不再認為有意義?
鄂蘭:我個人不覺得有意義。如果我當時這麼想,或許會做些事情吧,不過以現在回想過去,實在很難去說這種種。我當時是認為無望。
高斯:在妳的記憶裡有沒有一個確切的事件導致妳轉向政治?
鄂蘭:1933年2月27日火燒國會事件,以及當晚緊接著的所謂保護性居留的非法逮捕。如你所知,遭逮捕的人被關在蓋世太保的地窖或集中營。這是個窮兇惡極的事件,不過卻被後來發生的事掩蓋了。這對我是當頭棒喝,從那時起我感到有責任。也就是說,我無法再當個旁觀者。我試著以許多方式盡己之力。不過真正讓我出走德國的是……我從未提及這件事,因為它沒什麼結果。
高斯:請告訴我們。
鄂蘭:我本來就打算移居外國。我立刻想到猶太人無法再待下去。我不想當二等公民在德國四處遷屣。同時我也想到事情會繼續惡化,不過我終究未能順利離開。說實在的這帶給我某種滿足。我被逮捕,因而必須非法離開這個國家!稍後再跟你說怎麼離開的。我想我終於有所作為了,這對我是立即湧上的欣喜!至少我不是毫無作為,沒有人可以這樣說我!猶太復國組織給我機會,組織裡幾位領導人是我的好友,特別是會長布魯門費德,不過我不是該會會員,而他們也不強迫我加入。在某種程度上我受到他們的影響,特別是他們散播在猶太人之間那種讓我印象深刻的自我批判,不過在政治上則毫無瓜葛。1933那年布魯門費德與另一位你不認識的人來找我說:我們要將一般狀況下做出的所有反猶太言論都收集起來,比方所有各種專業俱樂部、各類專業期刊的反猶太人言論,總之,就是彙整不太為國外熟知的資料。在當時做這些資料的彙整就是納粹所稱從事「恐怖宣傳」。沒有一位猶太建國組織的人做得來這件事,因為若被發現,整個組織就會曝光。他們問我:「妳可以做嗎?」我回答,「當然。」我異常欣喜。首先,這看來是頗具智性的想法;其次,它讓我感覺終於可以有所作為。
高斯:妳因這項工作遭逮捕嗎?
鄂蘭:是,我被發現。我相當幸運,在關了八天就被釋放,因為我與逮捕我的警官作了朋友。他蠻迷人的!他從刑警被調升到政治部門,因此失了準。他不斷對我說,「平常辦案子就是有個人在我面前,我只要查檔案就知道怎麼回事,不過我該拿妳怎麼辦?」
高斯:那是在柏林嗎?
鄂蘭:是在柏林。不幸的是我必須對他撒謊,因為不能讓組織曝光。我跟他胡謅,而他一直說:「我把妳捉到這裡,我要放妳出去。不要找律師!猶太人現在沒錢,省下來吧!」這同時組織經由成員幫我找來一位律師,我把他送走。因為逮捕我的這個人有張開朗、正派的臉孔,我信任他,認為與那位誠惶誠恐的律師相比,他更有辦法讓我出去。
高斯:然後妳就出去,因此可以離開德國?
鄂蘭:我是出去了,不過得非法越過邊界,因此還有案底。
高斯:鄂蘭女士,我們先前提到的通訊一事,妳明白拒絕休勒姆多餘的警告,他要妳務必留意與猶太民族之間的休戚與共。妳寫到:「對我而言,身為猶太人是我生命無可懷疑的事實,我也不打算改變任何這樣的事實,我甚至在童年時期就這麼認定。」關於這個我有幾個提問。妳1906年生於漢諾瓦,為工程師之女,成長於柯尼斯堡。妳是否記得戰前德國猶太家庭出身的孩子是什麼樣子?
鄂蘭:我無法如實為每個人回答這個問題。就我個人的記憶,我並不是從我家得知我是猶太人。我母親是個十足非宗教人士。
高斯:妳的父親早逝?
鄂蘭:我父親早逝。聽起很怪,我的祖父是自由派猶太社區的長老,也是柯尼斯堡的公務人員,我來自柯尼斯堡一個古老的家庭,不過,猶太人一詞在我仍是兒童時從未在家中聽到。我第一次聽到反猶太字眼是從街上的兒童口中聽到的,說什麼不值得在此重述。這之後可以說就被「啟蒙」了。
高斯:這對妳是個震撼嗎?
鄂蘭:不算。
高斯:妳那時是否感覺——我現在有些特別?
鄂蘭:那是不同的事。對我一點都不震撼。我心裡這樣想: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有感覺自己特別嗎?有!不過今天我已無法為你解明。
高斯:妳如何覺得特別?
鄂蘭:客觀而言,我覺得與身為猶太人有關。比方,當我是較長的兒童時,我知道我看起來像猶太人,跟其他小孩長得不一樣,我很自覺到這點,但不是那種自卑感。我的母親、我的家也跟一般有些不一樣。與其他猶太小孩甚或與我們有關係的小孩的家相較,我家實在很特別,只不過對一個小孩而言很難搞清楚是什麼特別。
高斯:希望妳進一步說明妳家有何特別之處。妳說妳母親從未認為有需要向妳解釋妳與猶太民族休戚與共的關係,直到妳在街上碰到的事。妳的母親已失去妳在給休勒姆信上宣稱自己擁有的猶太識別嗎?這種猶太識別對她已不重要了嗎?她被同化成功,或至少她是這麼認為?
鄂蘭:我的母親不是理論派,我不認為她對這個有特別的想法,她參與社會民主運動,是社會主義月刊那個圈子的人,我父親也是。這個問題對她不重要。她當然是猶太人,也不可能讓我受洗!若她發現我否認自己的猶太身份,她不打我耳光才怪!否認自己的猶太身份?無法想像,想都不用想!不過這個問題在20年代我年輕時較之我母親那個年代更形重要。在我長大後,這個問題對她比起她早年更顯重要,不過這是外在環境因素使然。我自己則從未認為自己是德國人,這是就日爾曼民族、非就公民而言。我記得在1930年左右與雅斯培談論過這點。他說:「妳當然是德國人!」我說,「別人看得出來我不是!」不過這對我不構成干擾,我沒有自卑感,問題不在此。再回到我家哪裡特別。所有猶太小孩都會遭遇到反猶太主義,這戕害很多孩子的靈魂。我們不同之處在於我母親總是耳提面命不可被這種東西擊倒,必須捍衛自己!當我的老師做出反猶太的言論,主要不是針對我,而是針對其他猶太女孩,特別是東歐猶太學生,我的家訓是,立刻起身,離開教室,回家,一五一十報告每件事。然後我的母親就會寄出掛號信,事情到這裡對我而言就全部處理了。我賺到一天假不用上學,真是太棒了!但如果是小孩說的,我們是不准在家裡提,遭受到小孩的言語攻擊你自己捍衛自己。因此這些對我不構成問題。有些行為準則讓我保有我的尊嚴,我在家裡受到完全的保護。
高斯:妳分別在馬堡、海德堡、佛萊堡師事海德格、布特曼與雅斯培,主修哲學、副修神學與希臘文。妳如何會選擇這些主題?
鄂蘭:我常想到這個問題。我只能說打從14歲起就一直很清楚要唸哲學。
高斯:為什麼?
鄂蘭:我閱讀康德。那你會問,為何閱讀康德?是這樣:可以這麼說,我要嘛唸哲學,要嘛把自己淹死。但這可不是因為我不愛生命!就如我之前說的——我有加以瞭解的需要,這種需要很早就有了。家裡的圖書室藏有所有書,我只要從書架取出。
高斯:除了康德,妳還記得哪些特別的閱讀經驗?
鄂蘭:有。首先是雅斯培的《世界觀的心理學》,我想是1920年我14歲時出版的。然後我閱讀齊克果,這樣還蠻搭的。
高斯:就是這樣接觸神學的?
鄂蘭:是的。它們能以這樣的方式兜在一起,對我而言,它們相互隸屬。我有一些疑慮就僅若是個猶太人,那他會怎麼處理,怎麼進行。我有困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自行解決了。希臘文是另一件事。我一向喜愛希臘詩歌,而且詩在我的生命佔著極重的份量,所以我多加選希臘文,這對我簡直易如反掌,因為我本來就在唸。
高斯:真讓我印象深刻!
鄂蘭:你誇張了。
高斯:鄂蘭女士,妳是如此早慧。這是否有時會讓妳與妳的同學在日常關係上有走獨木橋之感,甚至感到痛苦?
鄂蘭:若我有自覺到這點,大概會如你所說。我想每個人都像那樣。
高斯:妳何時理解到妳錯了?
鄂蘭:有些晚,我不想說有多晚,因為不好意思說。我天真得可以,部分歸於家教。我家從不談成績,談成績與野心都被視為是自卑作祟。總之,當時的狀況我不是完全清楚。有時在人群中經驗到自外於人群的陌生感。
高斯:一種妳認為是來自於妳的陌生?
鄂蘭:是的,完全是。不過這跟才華無關,我從未將之與才華扣在一起。
高斯:結果是妳年少時有時會輕視別人?
鄂蘭:是,很早就曾這樣。我經常為此所苦,因為明知道不應該、不可以有這種輕視感。
高斯:妳在1933年離開德國到巴黎,妳在那裡的一個組織工作,協助在巴勒斯坦的猶太青年,妳可以告訴我這方面的事嗎?
鄂蘭:這個組織將14歲到17歲的猶太青少年從德國帶到巴勒斯坦,提供他們在吉布茨集體社區的庇護所。因此對這些猶太墾區我相當熟悉。
高斯:從非常早期?
鄂蘭:從非常早期,當時對他們深懷敬意。孩子在那裡接受職業養成與再養成。在鄉下有大營地,孩子在那裡準備被送往巴勒斯坦、上課、學習耕作,最重要的是增加體重。我們幫他們治裝,從頭到腳,也必須做飯給他們吃。最重要的是幫他們拿到文件,也必須處理他們的父母親,當然還要幫他們準備錢。我的工作大致是這樣,我與法國女性一起工作。你要聽我是怎麼決定接下這個工作嗎?
高斯:洗耳恭聽。
鄂蘭:我出身全然的學術背景,就此而言,1933年給我不可磨滅的印象。先說正面,再說負面的。或許應先說負面再說正面。當今的人常以為德國猶太人在1933那年震驚不已,因為希特勒掌權。就我與我的同輩所知,這是個讓人玩味的誤解。希特勒的崛起自然是壞事一件,但這是政治的、非個人層面。我們無須等到希特勒掌權才知道納粹是我們的敵人!任何非弱智的人在此四年前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我們也都知道非常多的德國人在幫納粹撐腰,因此1933年的事不可能讓我們震驚不已。
高斯:妳的意思是1933年的震撼來自於從一般的政治事件到個人層面這樣的事實?
鄂蘭:不是,也或者是這樣。首先,當人移居國外就從一般政治變成個人命運;其次是朋友的配合。個人的問題不在敵人的所作所為,而是我們的朋友做了什麼。當時那一波「配合」風潮,算是自願成分多,總之,不是在恐怖的壓力下,而是像是在人的四周形成一個虛無的空間。我生活在智識環境,但也知道其他人。在知識份子之間,可以這麼說,相互一致是鐵律。知識份子以外的不是這樣,這我不會忘記。我離開德國時滿腦想著:不要再來一次!(當然有些誇張)我再也不願與知識圈有任何瓜葛。同時我不相信當時的猶太人與德國猶太知識份子會表現不一樣,若他們的境遇有所不同。這不是個人意見,會這樣與這個專業、與身為知識份子有關。我用的是過去式。如今我有更多的瞭解。
高斯:我正要問妳是否現在還這麼認為呢。
鄂蘭:不再像過去那樣。不過我仍認為這是屬於知識份子的本質,也就是為每件事杜撰概念。不會有人去責備如果有人為了照顧妻兒而配合。更糟的是有些人真的相信納粹!在很短、非常短的時間就信了。也就是說他們編造希特勒概念,從某些面向看是有趣得不得了的事——十足異想天開、有趣、複雜的事!超乎尋常!我覺得怪誕可笑。今天我會說他們陷在自己的概念裡。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不過當時我並未能看得如此清楚。
高斯:就是這個對妳特別重要的原因讓妳出走知識圈,開始從事實用性質的工作?
鄂蘭:是的。現在來談正面的。我理解了我一再提及的一句話的意義:如果一個人遭受攻擊是因為身為猶太人,那就以猶太人捍衛自己,不是以德國人、不是以世界公民、不是以人權支持者或任何身份,而是以作為一個猶太人我能有什麼特別的作為。其次,與一個組織共同工作的意向很清楚,有史以來我第一次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共事。他們是唯一準備好的人。若加入已被同化者將不知所云,更且我一點都不想跟他們有任何關係。在我離開德國前關於蘿荷兒.范恩哈根的書已寫好。猶太人的問題是該書的重點。我以「我想要瞭解」的念頭進行書寫,不在討論我本身是猶太人的問題。不過隸屬於猶太教成為我那時的問題,而我自己的問題是政治的,十足政治的。我只想做實用工作,僅猶太人的工作。本著這樣的想法我在法國尋找工作。
高斯:直到1940年。
鄂蘭:是。
高斯:然後二戰期間妳前往美國,在那裡擔任政治理論、而非哲學教授。
鄂蘭:謝謝啊。
高斯:妳在芝加哥教書。你先生也是教授,在美國教哲學,你們住在紐約,於1940年結婚。歷經1933年的幻滅後,妳再度成為一個國際性學術圈的一份子。不過我想問的是妳是否會懷念前希特勒時期的歐洲,一個永不再回的時期。當妳回到歐洲,在妳的印象中哪些保留下來,哪些是無可彌補地消失了?
鄂蘭:前希特勒時期的歐洲?我不會懷念。我可以告訴你什麼留下來,語言留下來。
高斯:那對妳意義重大嗎?
鄂蘭:重大。我一向有意識地拒絕失去自己的母語。我一向與法文和英文保持某些距離。我能說流利的法語,目前用英文寫作。
高斯:妳現在用英文寫作?
鄂蘭:我用英文寫作,不過從未失去與它之間的距離感。你的母語和其他語言差異甚鉅。簡單地說我本身的狀況是這樣:我默記相當一大部分的德文詩歌,它們一直在我意識中。我再也無法這麼做了。我會用德文做的事不允許自己也同樣以英文來做。不過我現在膽子大了,有時也會用英文做,但大抵是保持某些距離。德語這種本質的東西留下來了,我一直有意識地加以保留。
高斯:甚至是最悲慘時刻?
鄂蘭:始終一如。我思忖,要有什麼作為?又不是德語發瘋。其次,母語無可取代。人是會忘記自己的母語,我看過。有些人講新語言講得比我好,我的口音還是很重,而且常常不合語言習慣,他們都使用正確。不過他們的使用方式是一個陳腔濫調接著一個陳腔濫調,因為當人忘記自己的母語,在母語裡所汲取擁有的富饒就枯竭了。
高斯:母語遭遺忘的例子,妳覺得是箝制的結果嗎?
鄂蘭:是,常常是這樣。我看到的人是因為震驚所導致。真正決定性的不是1933年,至少對我不是。真正決定性的是關於奧許維茲。
高斯:那是什麼時候?
鄂蘭:1943年。剛開始我們不相信,雖然我先生和我預期什麼事都會發生。但我們實在無法相信這件事,因為軍事上無此需要。我先生之前是軍事歷史學家,對軍事有所知悉。他說,不要這麼容易受騙,不要把表面的東西當真,他們不可能這樣過頭!然後一年後我們終究相信了,因為我們有證據。那是真的震驚。在那之前我們都說:人都嘛會有敵人,很自然的,為何一個民族不該有敵人?但這次截然不同,那是猶如一個深淵被打開。我們以前的想法認為每樣事都可彌補,就如政治上某種程度所做的一般。不過這一次行不通,根本不該發生這樣的事。發生在那裡的事,我們無法跟自己和解,誰也做不到。至於其他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每件事有時真的艱難:我們很窮、被追捕、我們必須逃跑,千方百計度過難關。不過我們當時年輕,我不否認有時覺得好玩。但奧許維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其他事我個人是可接受的。
高斯:德國自1945年以來已脫胎換骨,妳也常來,許多妳的重要作品都在這裡出版,鄂蘭女士,我想聽聽妳對戰後德國的看法。
鄂蘭:我1949年首次回到德國,應一個猶太組織之邀為猶太文化資產進行復原工作,主要是書。我帶著極大善意回來。我對1945年後的看法是這樣:發生在1933年的事實在不重要,若與其後所發生相較。當然朋友的不忠傷害很大,我就直白說了。
高斯:妳個人有此遭遇?
鄂蘭:當然。不過一個人若成了納粹,寫納粹相關的文章,他就無須對我忠實。而我從此未再跟他說話,他也不再需要跟我聯絡,因為我視他不存在,一翻兩瞪眼。但他們並非都是兇手,以我今日看之,他們陷入自己的陷阱,也不是願意看到後來的演變。因此對我而言,似乎正是在奧許維茲的深淵裡應有個溝通的基礎。許多人際關係也是這樣。我與人爭辯,不容易被說服,也不是很有禮貌,想什麼說什麼,不過最後與許多人還是和好如初。就如我之前說的,他們就只是認為自己屬於一個民族,而非公民,投入納粹主義幾個月,最糟的幾年,既非兇手也非告密者,就是為希特勒編造概念。不過大抵上一個人回到德國最棒的經驗——除却帶有強烈情緒的認知經驗,這種希臘悲劇情節的關鍵——是在街上聽到德語,這對我真是無以言喻的喜悅。
高斯:這是妳1949年回來時的反應?
鄂蘭:多少吧。現在事情都回到正軌,我反而覺得距離加大,以前經驗事情情緒波動很大。
高斯:因為妳認為這裡的情況恢復過快?
鄂蘭:沒錯。而且常常不是我認同的復原方式,不過我不覺得要對那樣的事負責。我現在是從外部來看,也就是說,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投入,也許是時間的推移使然。15年可不是什麼都沒有!
高斯:妳變得比較冷漠?
鄂蘭:冷漠太強,是距離,是有距離。
高斯:鄂蘭女士,妳的書《艾希曼耶路撒冷受審紀實》在西德出版,自從在美國出版後,就引發熱烈的討論。猶太人的反應,特別是反對聲浪,妳指稱說,部分是基於誤解,部分是基於別有用心的政治活動。尤其是最讓反對者反感的是妳提出質疑說,猶太人消極接受德國人屠殺是該受責怪,或他們的罪疚來自某些猶太委員會的配合。很多關於妳的問題都是因這本書而起,因此我想問:關於妳書中缺乏對猶太人的愛的批評,妳感到痛心嗎?
鄂蘭:首先,本著友善的態度,我要說,你自己就是這個活動的受害者。在書中我從未譴責猶太民族的不抵抗,倒是代表以色列政府的郝斯諾檢察官這麼譴責。我稱這些問題針對著證人而來是既愚蠢又殘酷。
高斯:書我看過,我瞭解妳說的。不過有些批評是基於妳書中許多章節的語氣。
鄂蘭:這是另一件事。我能說什麼?而且我也不想多說。如果他們認為寫這些東西只能用嚴肅的語氣寫。。。那他們就錯了,不過我多少可以理解,話說回來我依舊會笑。不過我的確認為艾希曼是個丑角。讓我告訴你。我把三千六百頁警方調查他的卷宗仔細從頭到尾閱讀一遍,過程中不知大笑幾回!批評我的人視我這樣的反應不良,那我也莫可奈何。不過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就算死前三分鐘,我可能還是會笑。而這就是他們說的語氣。語氣明顯帶有反諷是真的,而這種語氣是我個人的。當譴責我的人以我指責猶太人作為理由,除了是個惡意的謊言和宣傳,再無其他。語氣之說是針對我個人的異議。而對這個我莫可奈何。
高斯:妳準備承受?
鄂蘭:很願意。能怎樣?我總不能跟他們說:你們誤解我了,事實上我心中所想的是這樣或那樣。這實在荒謬。
高斯:根據這點,我要引述妳個人的陳述。妳說:「我一生從未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不管是德意志民族、法國人、美國人,或勞工階級或任何這類東西。我僅愛我的朋友,這是唯一一種我知道與相信的人與人之間的愛。更且這個猶太人的愛對我誠然可疑,因為我自己是猶太人。」我的問題是:作為一個政治活躍份子,難道不需投入一個團體,這種投入某種程度而言不是愛嗎?妳不怕妳這樣的態度是政治貧瘠嗎?
鄂蘭:不會。我反而認為另一種態度是政治貧瘠。首先,隸屬於一個團體是一種自然狀態。當你呱呱落地你就隸屬於一個團體。其次,當隸屬於一個團體是因為加入或組成一個組織,則是完全另一回事。此類組織必須與世界有關連。人會形成團體通常是基於共同的興趣。直接的個人關係上,人可談愛,在真正的愛裡這當然是最重要的存在,愛也存在某種友誼裡。在這樣的愛裡,人可獨立於他與世界的關係,因此隸屬於歧異甚深不同團體的人,彼此仍可保有私誼。不過若弄混了這些東西,將愛帶到談判桌上,坦白說,會一敗塗地。
高斯:妳認為猶太族群的愛是非政治?
鄂蘭:我認為它是非政治、是無世界狀態。而我真的認為這是個大災難。我承認猶太民族是典型無世界民族,這種狀態維持了數千年。
高斯:「世界」在妳的術語裡是指政治空間?
鄂蘭:是政治空間。
高斯:職此,猶太民族是非政治的民族?
鄂蘭:不完全是這樣,因為猶太人社會某種程度上也是關乎政治。猶太人宗教是國家宗教,不過要在相當的保留下,政治概念才有效。猶太民族遭受被驅散的痛苦,所有人都是流浪者,在這種情況下,此一無世界狀態產生一種相濡以沫特殊的溫暖,不過當以色列建國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高斯:有些東西消失了嗎?這樣的消失讓妳感到遺憾?
鄂蘭:是,為了自由人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因他們的無世界狀態彰顯出的獨特猶太人情是一種非常美麗的東西。你太年輕因此無緣經驗到。此一極美的東西外於所有社會連結,完全敞開心胸、無一絲偏見,我經驗過,特別是從我母親身上,我母親對整個猶太社居也是這種態度。當然所有那些東西的逝走是很大的損失。為了自由人付出代價,我曾在我的萊辛講詞裡說過。
高斯:1959年在漢堡的演講。。。
註:限於格式無法一次貼完,因此分上下回貼文。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