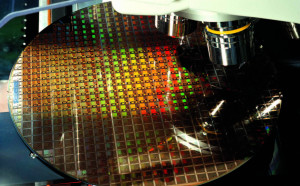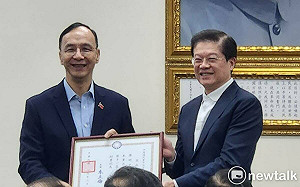榮大布行
1998年一個冬日早上我趕著到文化大學教書,火車就要進站,急忙跑去剪票口,突見一個熟悉的身影也匆忙走到入口處。那不是公公嗎?
我跑過去扶住他,「爸,您要去台北做什麼?」
「要去批布啦!」
這一問一答莒光號就進站了,我們坐上火車,窗外冬陽灑著晶寒的歡氣。
公公沒和我們住在一起,彼此卻意外在新竹火車站碰面,坐同一班火車到台北,感覺有些奇異。
那一年我公公已85歲。
公公自二戰終戰後就在新竹市大同路開布莊賣布,老一輩的新竹在地人應該多少對榮大布行有印象。我結婚時公公在一樓的店面早已一分為三,其他兩間分別是金店與委託行,他自己的布店僅剩一個小地方,賣著玩的,雖然如此,他還是蠻認真做生意。
其實我公公不講話的時候看起來有幾分嚴峻,不過常常有他蠻可愛的地方。記憶中有一回傍晚我在老家二樓辦公室用電腦,那天他心情可能不錯,當他從我身旁走過時,突然停下來,跟我說起唸小學時的片段情景,說到興奮處,哦,就在我面前一邊踏步擺手一邊唱日本國歌君之代!這是我對公公最鮮明的記憶。
我公公育有十男三女,多有所成。不過在89歲前依舊過他賣布、騎腳踏車的儉樸生活。一天裡若能賺個千把來塊,午飯喝杯啤酒,晚上睡個好覺,就心滿意足,臉露成就的微笑。
由於家族龐大,媳婦眾多,公公乾脆給每個人自由,也從不命令誰要做什麼,當然有時候也不太認識新進門的媳婦。外子是他子女中最後一個結婚的,外子年紀又比我大一些,所以我是那個常常被他忘記的媳婦。
有一次中午我回大同路老家陪他吃飯。吃飯時公公跟我有說有笑,只是眼神似乎帶有懷疑。我吃飽後走去客廳,公公小聲問在老家幫忙做飯的姪女阿玉,「那個女的是誰,怎麼在我們家吃飯?」阿玉忍不住哈哈大笑說,「伊是阿國的牽手,您的媳婦啦!」
阿玉是二哥的女兒,年紀比我大,目前已有個小孫女,所以呢,我已經當嬸婆祖嘍。
說到回公公家吃飯,就像外子說的,是一場災難。因為公公節儉成性,所以吃不完的菜啦、魚、肉會一溫再溫,而且菜色幾乎天天一樣。有一回在老家附近開診所的小叔回去吃個便飯,看到桌上黑壓壓的一片,嚇得拔腿就跑!
還沒變成老人家時,大概都覺得老人家應該蠻接受自己老了,可是我公公打破我這樣僵化的印象。在他86歲時,有天晚上突然對著鏡子端詳,然後回頭跟我說:「奇怪,我怎麼會有這麼多白頭髮?」
生於日治時期的公公,2007年在老家過世,享年94歲。他過世時我人還在從丹麥飛回台灣的飛機上,不過我完全不知道,因為外子不願我擔心並未以電話告知,就是那麼剛好在我十月五日回國那天他過世。
公公認識我十一年,但他大概從來都不清楚我叫什麼,不過不知他是否一直誤以為我是他的孫女,所以看到我時常跟我說故事,說他年輕時怎樣打拼、怎樣買地,只是他都淡淡地說,沒什麼炫耀的表情,就是回憶小學生活時會變成小朋友的樣子。
榮大布行隨著公公的過世完全落幕,像一抹夏日午後吊在竹竿上的影子,無聲隱逝。

公公與我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