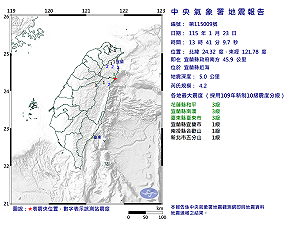邁克爾•麥克福爾《俄羅斯未竟的革命》
全站首選:因應開學返校!高鐵加開12班「大學生5折優惠列車」1/27開搶
建立在暴力和恐懼上的社會是不能改革的,我們面臨的複雜歷史任務是拆除其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根源的制度,這種理解來得太遲了。--雅科夫列夫
全站首選:黃國昌怎麼選都輸!新北最新民調攤牌 吳靜怡:藍白合一碰到他就破功
邁克爾•麥克福爾是美國著名的俄羅斯問題專家,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他長期居住在莫斯科,親眼目睹了很多改變蘇俄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的發生,並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邁克爾•麥克福爾以前是研究南非問題的,為了瞭解蘇聯在南部非洲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而赴莫斯科訪問。由此,他接觸到蘇聯的一批異議人士,他回憶說:「當時,我並不認為這些民主聯盟的活動家會有任何成功的機會,但我對他們的毅力產生了興趣,對他們的特殊使命表示同情。…他們表現出了以自由的名義挑戰強大政權的勇氣,即便這種挑戰對他們的個人幸福而言是一種巨大的風險。」正是受到這種勇氣的感染,麥克福爾重新確定其個人生活和學術研究的方向,轉而研究俄羅斯問題。
無心插柳柳成蔭,90年代之後,俄羅斯讓人眼花撩亂的諸多變革與政治鬥爭,果然為麥克福爾提供了豐富的、富於刺激性的素材,讓他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俄羅斯未竟的革命》這部深入研究俄羅斯艱難轉型的著作。麥克福爾的結論是,蘇俄的案例揭示了締造社會契約的重要性,他解釋了俄羅斯精英結盟的努力為什麼失敗,以至於產生2個對立陣營的暴力對抗和一個遲滯的民主化轉型。換言之,蘇聯解體之後20年,俄國並未完成民主轉型,只是艱難地邁出了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的第1步。
俄國轉型之難:沒有可以啟動的民主傳統與典範
俄國的民主轉型比大部分中東歐國家都更加緩慢而艱難。麥克福爾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在尋求創建一個新的、同民主政體相符的制度環境的時候,俄羅斯領導人很少能從蘇聯體制中找到可以利用的相關制度。在拉丁美洲、南歐甚至中東發生的民主轉型中,被威權主義統治所壓制的原有的民主制度只是被再次啟動,這是一個比建立新制度要有效得多的過程,然而,俄羅斯領導人沒有這樣的制度可以重新使用。」一言以蔽之,俄國歷史上缺少可以啟動的民主傳統與典範,索爾仁尼琴心儀的東正教、「杜馬」制度等並不足以孕育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自由。
在沙皇的絕對君主專制與列寧-史達林式的現代極權主義之間,俄國有過一個曇花一現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以克倫茨基為代表的臨時政府促進了俄國的民主和自由,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都享有充分的自由,罷工成為現實。秘密員警、鞭刑、流放西伯利亞,以及死刑都被取消了。但是,正如《俄羅斯史》所指出的那樣「雖然臨時政府顯示出的自由主義給俄國帶來了有益之處,但它沒有克服困擾著國家和1917年國家統治者的異常困難。」臨時政府的領導人深信法治,堅持認為俄國將來的主要問題只能在一個充分民主的制憲會議中解決。然而,當時深受戰爭之苦的民眾,對憲法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和平與麵包。只存在了短短的8個月的自由主義的臨時政府,並未獲得民眾的認可和尊重,也未能在他們的記憶中留下深切的痕跡,當然更不可能成為一種可以復活的歷史經驗。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中東歐國家大都有悠久的民主傳統和長期的民主實踐。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在1918到1938年間有過長達20年的「第一共和」時期。1920年2月29日,由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了捷克的第1部憲法,明定捷克的國體為民主共和國。該憲法一方面吸收了當代歐美憲法中的進步精神,一方面也兼顧捷克的歷史傳統。一戰之後,經過成功的土地改革及發展工業,捷克成為東歐新興國家中經濟結構最為健全的國家。《東歐諸國史》指出:「捷克的政治體制,大致符合它的國父馬薩里克的崇高理想,如能持續發展,必將成為鄰邦的楷模,東歐民主的重鎮。」儘管此後捷克深受納粹德國和蘇俄之蹂躪,但普通民眾並未忘懷「第一共和」時期的民主自由與欣欣向榮。哈威爾等知識份子更是從「第一共和」的歷史經驗中汲取靈感,勾勒出未來民主捷克之藍圖。
不同的傳統決定了不同的現實。所以,俄國轉型之難與捷克轉型之易的差異並非偶然,亦非機遇與人力可以改變。
沒有公民社會,便沒有民主制度的鞏固
民主比獨裁好,即便是劣質的民主,也比優質的獨裁好。蘇聯當年的共產黨獨裁,比起大多數政局混亂的第三世界國家好得多,普通民主如果不去挑戰共產黨的地位,可以享受免費的住房、醫療及子女教育,基本上可以衣食無憂,可謂「優質獨裁」也。但是,人不是豬,人具有上帝之形象,人天生便有追求自由與尊嚴的訴求。所以,再優質的獨裁,也無法滿足人的這一需求。
正是對自由的渴望,使得蘇聯原有的獨裁制度無法持續下去。當制度的轉型啟動之後,上層的決策一夜之間便可以實現政權的更迭,比如戈巴契夫宣佈蘇聯解體並將政權移交給葉爾欽。從戈巴契夫到葉爾欽,他們都發佈過若干法令,申明廢除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實行多黨制、推行普選、保障人權等。但是,政府承諾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及文化權利,與公民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堅守,根本就是兩碼事。如果僅有前者而沒有後者,再好的法律和再開明的統治者,也無法鍛造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麥克福爾認為,俄國的民主制度迄今未能鞏固和穩定,未來仍然存在諸多變數,像普亭這樣的威權主義者對民主的威脅不可低估。「如果普亭總統或者是類似於他這樣的人物,能夠在長時間內保持大眾的支持和軍隊的效忠,那麼,他和他的盟友就能再次最終處在一個改寫政治遊戲規則的地位上。」那麼,前克格勃官員、作風強硬的普亭,為何能獲得較高的民意支持呢?這恰恰說明俄國民眾的精神世界尚未「去卡裡斯瑪化」,他們心甘情願地臣服於彼得大帝、史達林以及類似的人物腳下。即便沒有沙皇,他們也要呼喚一個出來。換言之,俄國依然是一個「臣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在這一點上,中國和俄國堪稱孿生兄弟:習近平上台之後1年多事件便實現「九權合一」,許多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不但對其法西斯化的行徑毫無警惕與批判,反倒為其鼓吹,並幻想習近平是「通過集權的方式改革」。
俄國民眾公民意識的淡薄,首先應歸咎于共產黨長達70年的「全能主義式」統治。在蘇聯時代,國內根本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組織,工會、共青團、婦聯、紅十字會等組織都是獲得官方財政支援的半官方組織,甚至可以說是黨的分支機搆。麥克福爾指出,「蘇維埃制度把私人生活堆砌在社會組織的金字塔裡,它們在名稱上模仿公民組織,但在實踐中被用來控制社會。結果,當這個制度開始崩潰的時候,公民社會必須從頭開始重建。」私人生活的領域基本消失了,人們都像幼稚園的孩子那樣,眼巴巴地等待黨和政府來安排他們的衣食住行,而不知道如何獨立地生活。
其次,由於經濟改革出現一系列失誤,俄國的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個寡頭群體手中。這個階層利用財富控制媒體、影響選舉、打壓公民社會,正如麥克福爾所觀察到的那樣:「在後共產黨時代的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可能是社會中惟一有組織的部門。」與之相反,「中產階級--西方大多數公民組織的資助者--在俄羅斯卻發展緩慢。」麥克福爾經過調查發現,在當今的俄國,只有9%的公民參加非政府組織。更讓人擔憂的是:「公民組織占人口的百分比越來越小,對國家越來越不感興趣並且日漸與國家脫離關係,它反而在私人領域追求狹隘的議程。運動誤入歧途已有若干年。」
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和文化氛圍,它不僅需要被政治家所篤信,也需要獲得普通民眾的支援。但是,麥克福爾發現:「俄羅斯不發達的公民社會使得國家能夠以不受以大眾為基礎的社會的制約而進行統治,這種國家責任的缺失反過來損害了大眾對民主的信心,並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阻礙了民主文化的發展。」
在黑屋子裡如何抓到黑貓?
俄羅斯民主轉型的困難,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無論是戈巴契夫、葉爾欽等在上掌權者,還是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地位超然的批評者,以及大部分不由自主身陷其中的普通民眾,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麥克福爾對俄國所走過的並仍然在跋涉中的這條「光榮荊棘路」充滿了「同情的理解」,他說:「考慮到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在駕馭由共產主義統治的轉型時面臨著廣泛的變遷議程,我們對在政治自由化開始僅10年後,就期望在蘇聯或俄羅斯建立起的自由民主制,可能是過分樂觀了。解散一個帝國,把計劃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在共產主義專制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民主政體,這三重挑戰甚至會難倒美國那些充滿智慧的國父們。」用參與過戈巴契夫時代後期的經濟政策的制定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涅基佩洛夫的話來說「在黑屋子裡逮住黑貓容易嗎?」
事實上,當時包括戈巴契夫在在內的領導人,連他們要尋找的是一隻什麼樣的「貓」都沒有弄清楚。戈爾巴喬只是感覺到「為了更好的生活,應該作某種改變」,卻未能釐清這些變革的實質和方法。他的顧問們,他的左右兩邊的反對者們,更是固執己見、誇誇其談,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亞歷山大‧涅基佩洛夫用這樣一個比喻形象地描述說:「改革的『飛機』遇到暴風雨,不是因為不清楚確切的目的地就起飛了,而是因為這架『飛機的機組和乘客』不去共同確定航向,卻在『飛機』上打得不可開交。」戈巴契夫本該與葉利欽同舟共濟,2人卻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戈巴契夫掌權的時候,對葉爾欽的迫害毫不手軟;而葉爾欽奪權後,對戈巴契夫亦極盡羞辱之能事。
從「819」政變到葉爾欽攻打議會所在的「白宮」,都是因為蘇俄既沒有透明的資訊傳播系統,也沒有協商妥協的文化習俗,使得持不同觀點、立場和利益的群體之間的對立一步步地發展到不可調和、必須使用武力解決的地步。直到今天,俄國的權力結構仍然沒有穩定下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間的劃分,以及作為「第四權」的新聞自由,還有總統和總理之權力分割,都未塵埃落定。對此,麥克福爾也有同感:「在蘇聯後期,蘇聯政權的幾乎每一個制度安排都存在著問題,這給形成政治行為體之間的關聯式結構幾乎沒有留下什麼餘地。缺乏持續的協商談判也限制了對立雙方之間的資訊溝通。在行為體關於擴大的改革議程的偏好極不確定的情況下,對立雙方傾向於對敵人做出最壞的評價。」可以說,這種拒絕妥協的「你死我活」的「敵人意識」,以及對民主的本質缺乏歷屆,對俄國的民主化進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阻礙。
變革難,但變總比不變要好。那些宣導變革的人們,無論經歷了怎樣的挫折和失敗,無論承受了多大的壓力與誤解,他們都有資格接受歷史的敬意,畢竟俄羅斯超過9成的民眾在民調中宣佈,決不願意回到史達林時代。這就是對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這2位針鋒相對的改革家事業的肯定,正像麥克福爾所下的結論:「特別是同當代發生的巨大的社會革命相比,蘇聯-俄羅斯轉型還是相對成功地在短時間內建立了一個民主機制,雖然有著缺陷和脆弱不堪。」確實,與那些死不改革的國家相比,俄羅斯的民主前景大有希望--俄國正在走向民主,而中國還沒有啟程。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