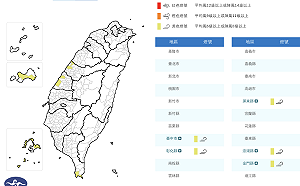台灣核三廠2號機已於5月17日停機除役,象徵台灣邁入「非核家園」,不料,立法院民眾黨於5月20日提出並通過「核三重啟公投案」,8月23日將舉行公投。支持核三重啟者認為核電在邁向2050淨零排放的路上扮演關鍵角色,強調電力需求持續上升、綠能進度落後,「重啟核三」是唯一選項。
然而,這樣的說法過度簡化了能源轉型的複雜性,也忽略核能在安全、成本、時效與社會風險等面向上的根本問題。
- 核三重啟無助長期穩定,更將拖慢能源轉型
核三廠共有兩部機組,總裝置容量為1,874 MW,發電量占全台不到4%(依2022年數據為3.9%),即使兩部機組全數重啟,對2050淨零目標的貢獻也非常有限。更關鍵的是,核三廠一號與二號機組分別於1984年和1985年商轉,當初的設計壽命為40年。根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核能電廠延役最長可延長20年。若核三廠能順利申請延役,其運轉執照最長可展延至2044年和2045年,因此,即使重啟成功,核三廠的運轉壽命在法規上也很難延續到2050年。屆時仍須重新面對除役與核廢料問題。這種「延命式解法」,非但無法支撐長期穩定供電,反而排擠真正具備永續潛力的能源選項,例如太陽光電、風力與儲能系統。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24年報告指出,全球能源轉型的主流是加速再生能源部署、智慧電網建設與儲能發展。即使核能在部分國家仍有角色,其建置成本高、工期長、集中式風險高的特性,已使其在能源系統中難以擔任核心角色。德國、義大利等國正是在這些考量下,選擇全面執行非核政策,全力投入綠能與電網轉型。
- 核三安全風險難解,延役等於對抗科學事實
核三廠鄰近恆春斷層帶,儘管歷年來曾進行耐震補強,其設計標準是否能符合最新的地質研究成果,值得深究。最新學術指出,恆春斷層具有高活動性,其潛在規模可能遠超過初期設計假設。
此外,核三兩部機組的反應爐分別運轉超過39與36年,材料脆化為其最大風險。長期受中子輻射影響,爐心鋼板的延展性會降低,導致結構脆化,這是物理性老化且不可逆。即便提出延役申請,也需通過高度複雜的安全評估與結構更新,過程曠日廢時、成本驚人,風險卻仍無法完全消除。
我們不能忘記福島核災的教訓,即使發生機率低,一旦失控後果將是無可挽回的社會災難。風險不可承受,就不應是可接受的政策選項。
- 核電非便宜能源,而是財政黑洞
核能常被包裝宣傳為「低價清潔能源」,但這種說法忽略其全生命週期的高昂成本。若從建廠、運維、保險、除役到核廢料處置,核電的真實成本遠高於表面數字。
以美國加州魔鬼谷(Diablo Canyon)核電廠為例,根據美國加州政府與太平洋瓦電公司(PG&E)的協議,延役初期貸款額度高達14億美元(約新台幣450億元)。總體估算未來五年內總成本將高達118億美元(約新台幣3,800億元)。台灣若欲重啟核三,同樣需耗費巨額資源,重新採購燃料、補強設施、更新安全系統,專家估計其總支出可能高達數百億元以上。
相較之下,根據台電與國際能源總署(IEA)資料,台灣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每度電成本已降至2元以下,且技術成熟、建置時間短、無燃料成本,具備規模經濟效益與可擴展性。若選擇將稀有資源投入老舊核電廠,而非擴大分散式綠能與智慧電網,只會拖慢能源轉型並加重全民負擔。
- 核廢處理仍無解,重啟只會製造更多風險
核三廠乾式貯存場雖已興建完成,但因地方政府反對與民眾疑慮和抗爭,迄今未獲啟用許可,導致燃料池空間將近飽和。若貿然重啟核三,將立即面臨燃料無處安置的窘境。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迄今無解。台灣自1980年代即開始推動場址選定與訂定《高階核廢選址條例》,至今仍停留在草案階段,這反映出社會對於核廢料處置的無場址、無立法、無社會共識的困境。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2022年報告,目前全球僅有芬蘭的「奧爾基洛奧托(Onkalo)」設施獲得營運許可,計畫於2025年正式啟用,但尚未實際處置任何高階核廢料。瑞典、日本、法國等核能大國,現也仍處於選址、審查或建設階段。而韓國慶州的中低階核廢料(如工作人員輻射防護衣與工具)處置場耗時20年才興建完成,高階核廢最終處置場亦未有解決方案。這代表高階核廢的最終處置仍是全球共同面對的難題。這也是為何許多國家在推動能源轉型時,選擇將發展重心放在再生能源上。
結語:擁抱非核轉型,打造真正永續的能源安全
支持核三重啟者希望以「穩定電力」為名,企圖說服社會重新擁抱核電,但這是對能源轉型難題的懶惰回應。重啟核三不但耗時、燒錢、風險高,更將核廢料問題延宕給下一代。
台灣應堅持非核轉型路線,全面加速再生能源部署、儲能系統建設、電網升級與民眾參與,打造以分散式、智慧化、低碳化為核心的新型能源體系。這才是真正保障全民安全,為台灣建立真正永續的能源政策。
文/蘇勳璧(中台灣教授協會常務理事)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