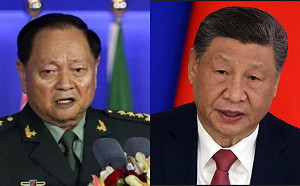太陽花之前,鄭南榕是一個被世人遺忘的名字,教科書中絕對不會提到,他只是被少數人權活動人士熟知;太陽花之後,鄭南榕浮出水面,被年輕一代視為“台灣國父”,甚至在使用“臺灣國”的護照貼紙時,很多人都用鄭南榕的頭像。
在“空間悼念”的意義上,台北那條鄭南榕紀念館所在的小巷被命名為“自由巷”,台南也有一條街道被命名為“南榕大道”。正式命名爲“南榕廣場”的地方則有兩處:一處位於宜蘭縣中興文創園區,鄭南榕因父親於中興紙廠工作,其兒少時期在紙廠園區內成長,園區內設立南榕廣場乃是理所當然。這裡成為人們追尋鄭南榕腳蹤的第一站。廣場內設有以兩面三角形所組成的紀念碑,一面為鄭南榕的手稿「爭取百分之百自由」,另一面是由知名建築師黃建興題寫的「南榕」二字,背面另附上南榕廣場記事。第二處位於高雄鼓山區中華一路868號,廣場內設有公共藝術供民眾欣賞。鄭南榕生前雖未在這一帶生活過,但高雄以紀念鄭南榕彰顯其“人權之都”的特質,也算是相得益彰。
全站首選:是否攻台成習張決裂關鍵? 張又俠被捕 專家:未來有這5種可能性.....
我要寫的南榕廣場,並非以上這兩處,而是一處並未正式命名的南榕廣場——台南成功大學學生心目中的南榕廣場。
我很喜歡成功大學的校園。大正時代昂揚典雅的紅磚建筑,蘊含著日本當年“脫亞入歐”的雄心壯志。後來,日本進入昭和時代,大步走向軍國主義,窮兵黷武,頭破血流,但大正時代近代化的理想並沒有錯:脫離專制獨裁的亞洲,擁抱民主自由的英美,仍是日本和台灣都需要好好補上的一課。
我更愛的是鬱鬱蔥蔥的百年老榕樹,根深葉茂,婀娜多姿,如母親般默默注視著樹下匆匆行走的青年學子。一屆又一屆學生,來了又離開,唯有榕樹在此生長與安息、陪伴與安慰。在這座校園裡讀書的學生,真是有福的。
當前熱搜:嘆民眾黨紛擾「不願被利用」 林子宇:不願同流、也願離開
從成功大學校史館出來,就是“南榕廣場”——此前,成大師生在口頭上稱之為「榕園」。以廣場而論,空間並不大,卻並不顯得擁擠狹小。這裡找不到任何“南榕廣場”的標誌,因為“南榕廣場”這個名字不被校方認可,某些保守派人士對這個名字“談虎色變”,竭盡全力阻止其定案。
2013年11月,成大校方拆除了成功、勝利兩校區之間的圍牆,將出現的新空間設立成一處校園廣場。校方委托學生社團聯合會,辦理廣場的命名活動。台文系學生邱鈺萍提出,以“南方榕樹”的概念將廣場命名為「南榕廣場」,同時亦可紀念成功大學校友鄭南榕——雖然鄭南榕在成大讀書的時間並不長,但成大畢竟是其母校。“榕”,既是懷樹,也是懷人,偉大的人,往往具有樹的品質——堅韌而樸素、安靜而謙卑。以“種樹的詩人”自居的吳晟說過,樹可以沒有人類,但人類不能離樹而活。在他眼中,那些可愛的樹:
亦成蔭。以新葉
滴下清涼
亦成柱。以愉悅的蓊蔥
擎起一片緑天
如此美好的詩句,説的是樹,也是人——如果沒有鄭南榕,今天的台灣人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嗎?
徵名活動期間,成大的師生先後提出10個名字。在11月30日投票截止前,有3千8百名師生參與投票,“南榕廣場”以971票的高票,在10組備選名稱中脫穎而出。剩下的程序就是校方對投票結果加以確認了。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校方突然出爾反爾。
為何校長視民主程序如兒戲?
原以為已經塵埃落定的結果,卻在投票資料呈送校方時變了調。成大主任秘書陳進成以“該命名活動沒有實際效力,投票活動只是跟學生宣傳有要蓋廣場這件事”為由,表示廣場名稱必須送交校務會議,才能拍板定案,等於否決了師生的表決結果。
於是,成大零貳社及學生會發起連署抗議。學生施壓後,成大校長黃煌煇承諾將廣場命名一事,納入12月25日校務會議的議程中討論。然而,校務會議當天,卻將廣場命名案從主管會報中刪除。如此出爾反爾、瞞天過海,使立法院葉宜津立委提出公開質詢,南榕廣場一事登上各大媒體版面。
之後,校長黃煌煇以電子郵件及學校網站發出“致全校師生一封信”,提出校園需遵守政治中立與宗教中立的原則,校內相關設施均應避免涉及政治性活動與特定政治意識形態,暗指南榕廣場名稱失當。
此一說法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學生認為,政治本來就無所不在,食衣住行皆與政治有關,校園也離不開政治。所謂校園必須遵守政治中立和宗教中立,並不是學校不該有任何涉及政治或宗教的語言或名稱,而是當特定政黨或宗教進入校園活動時,學方不能出面為該團體表態或背書。如果校長的邏輯成立的話,「零貳社」也要求校方將“中正堂”撤名——這不是政治性的名稱又是什麽呢?校長作繭自縛,無法回答。更有人追問,若“南榕”這個名字是政治,“光復”這個名字難道不是政治嗎?於是,有學生以落實校長“政治中立”的立場為由,自行拆除成大光復校區的「光復」門牌。成大校方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有苦說不出,“光復”門牌至今尚未修復。
不過,官僚們總有“撒豆成兵”的伎倆。經過一番幕后操作,在校務會議上由材料系教授林光隆臨時提出修正案,建議直接取消廣場命名。校長黃煌煇表態支持説:「大家要叫廣場什麼名字都可以,既然有人仍把自由廣場叫做中正紀念堂,大家當然可叫新廣場為南榕廣場。」他順便幽了自己一默:「也可以叫黃煌煇廣場啦!」引起在場代表一陣大笑。
我真不知道旁人怎能笑得出來,我唯有一聲嘆息——這樣一個有著知名學者頭銜的大學校長,如此“無知者無畏”,在嚴肅的校務會議上開這種粗鄙狂妄的玩笑,將低俗當作睿智,實在是對成功大學的羞辱。這種人不配當校長。
當校方確認“程序上沒問題”後,會議代表針對「取消廣場命名」的修正案舉手表決。100名校務代表中,70票贊成、21票反對,最後以懸殊差距,取消了廣場的命名。幾十名並非民選產生的“代表”就能否決3千名學生投票的結果,權利的不對等駭人聽聞,讓人感嘆民主化已經30年的台灣,校園民主居然如此匱乏。
校長黃煌煇更在會議中回應説,他不能接受學生讓他“道歉”的要求,因為他要學生辦理活動是“為了凝聚向心力,從來沒有說票選名稱就是最終名稱”。言下之意就是,我是跟你們玩過家家遊戲的,誰讓你們信以為真呢。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們自己太傻太天真。
更荒腔走板的是,當零貳社等學生社團自行舉行南榕廣場命名儀式之時,成大主秘陳進成對媒體表示,尊重民主多元聲音,學生有充分表達言論空間,校方開放態度不會干涉,但“若有固定裝置,校方會在活動結束後清理”。對於廣場名稱,「隨人喜歡叫什麼就叫什麼,目前成大沒有正名命名的廣場」。表面上看,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寬容姿態,而“清理”一詞則綿裡藏針、威權猶在。而“隨人喜歡叫什麼就叫什麼”這句話,充滿了“只要我有權在手,我就根本不在乎”的痞子气。難怪有人説成大不是校長當家,而是主秘做主。帝制時代的中國,若皇帝太昏庸,必定有飛揚跋扈的太監頭子出現,此種權力模式再度在一所現代大學中重演。
英國史教授不知道英國史就是自由史?
在此次校務會議上,如果説校長黃煌煇的“不當幽默”只能算是“茶杯裡的風波”,那麽歷史系教授王文霞的發言才是石破天驚。王文霞説:「鄭南榕的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因為他是害了他自己的生命,任何對生命的傷害,都是絕對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她又説,鄭南榕「以死來解決問題,這種方式其實是一種暴力的方式,這個暴力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逃避問題,一方面反映他是沒有能力去處理他命運裡面面臨的挑戰。」她甚至用「炸彈客」來攻擊鄭南榕:「我還要舉一個例子,他很像炸彈客嘛!很像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如此嘲諷、詆毀一位為自由民主不惜犧牲性命的烈士,凸顯了這位資深教授對台灣民主化歷史以及人類普世價值的無知與漠視。
對於王文霞的這番言論,學者沈清楷駁斥説,雖然大家對事實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首先要把事實搞清楚,作為歷史學者的王文霞尤其應當如此。鄭南榕自囚71天期間準備的是「汽油桶」,不是「汽油彈」。鄭南榕的自焚,沒有攻擊任何人,也未向警方投擲汽油彈。就連當時以攻堅戰逼死鄭南榕的刑警隊長侯友宜,也在對外說明中承認:「所有錄影帶沒有鄭南榕投擲汽油彈的鏡頭。」重視史實的王文霞教授,為什麼要扭曲事實呢?她才像是「自爆的炸彈客」,她對鄭南榕的仇恨,其實是對自由的仇恨。
沈清楷進而指出,王文霞提到《法國人權暨公民宣言》,認為法國人權宣言重視生命價值,而鄭南榕不重視生命價值。其實,《法國人權宣言》所提及的生命價值,也保括「反抗不義政府」的價值。鄭南榕的自焚,是為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其精神不僅符合法國《人權宣言》第二條的「壓迫的抵抗」,也就是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抵抗;同時也符合法國《人權宣言》第11條所認為「最珍貴」的人權,「思想及意見的表達自由:包括口語、寫作與出版」,鄭南榕所捍衛的正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王文霞不斷強調「對生命的尊重」,當鄭南榕以生命去捍衛應有的人權價值,不是一種更積極地表達對「生命的尊重」嗎?若王文霞真的像她所聲稱的那樣重視生命的價值,她為什麼不譴責剝奪鄭南榕生命的黨國體制,以及害死鄭南榕的兇手之一的侯友宜呢?原因很簡單,批判當權者要冒風險,攻擊長眠於地下的犧牲者是安全的。
我上網稍稍瞭解了一下,原來王文霞是專攻英國歷史的教授。倘若她真的對英國歷史有所研究,難道她不知道英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丘吉爾的“英國史就是自由史”的觀點?將自由視為一種傳自先輩的習慣性權利,在英國還未形成國家的時候,就已經在英倫住民心中紮根了。然後是大憲章、清教徒革命以及英國率先邁入民主化和現代化。丘吉爾在其巨著《英語民族史》中指出:“哥倫布朝著美洲大陸揚帆出發的時候,國會、陪審團制度、地方自治以及新聞自由的萌芽就已經破土而出。”丘吉爾認為,英美國家所堅持的價值,包括普通法、《大憲章》、英國《權利法案》和美國《獨立宣言》,同時也是對獨裁、專制、暴政的嚴厲指責。如果承認“個人自由和抵制專制權力正是英語民族最顯著的特徵”,那麽一生研究英國史的王文霞教授為什麼如此仇恨爲自由獻出生命的鄭南榕呢?難道她研究的不是以自由爲核心價值的英國史,而是以暴政爲主要特徵的中國史——進而也被幽暗的中國史所毒害和同化?
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王文霞教授居然是台灣高中歷史課綱的審定者之一。那麽,她所審定的歷史課本,向中學生灌輸的究竟是怎樣的知識、理念和價值呢?王文霞本身就是黨國洗腦教育的犧牲品,當她掌握了教育的權力之後,立即華麗轉身,由受害者變成加害者,繼續對年輕一代施行洗腦教育。
這一惡性循環必須被打破。
大學的使命是爲了培養“聽話、出活”的學生嗎?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以工科為主的成大是一所培養「純樸老實」的學生的學校。老師經常批評北部學生「奸詐」,自豪成大畢業生是多年來顧主的「最愛」,同時感概「選成大學生的顧主都是台大畢業生」。
這種學校風格的定位,讓我想起共產黨治下的北京清華大學。上個世紀20年代,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用“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來紀念前輩學者王國維,也以此勉勵清華的莘莘學子。1949年之後,中共用“院系調整”的政策,將清華閹割去勢,讓這所只剩下工科院系的大學淪為“紅色工程師的搖籃”。
當年在清華煽動學運的肄業生蔣南翔當上清華校長,公開宣稱清華培養人才的目標乃是“聽話、出活”四個字。作為清華畢業生的胡錦濤,就是這樣一個“聽話、出活”的木乃伊。那麽,成功大學願意成為類似的“失魂落魄”、唯唯諾諾的大學嗎?
成功大學的學生沒有向頤指氣使的校方低頭,他們在南榕廣場舉行抗議活動,打出了一副意味深長的對聯——上聯是“悼大學精神已死”,下聯是“慟校園民主之亡”,橫批是“朕難容”,鄭南榕的諧音“朕難容”,惟妙惟肖地勾勒出黃煌煇、王文霞等人“小蔣介石”的精神面貌。
成大校方用謊言包裹謊言,結果無法自圓其說。成大學生會權益部長張書睿毫不留情地批判説:「校方簡直是厚顏無恥!」學生們認為,水利系教授高家俊、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在會議中刻意影響其他教師去評斷鄭南榕,指控學生引用外界政治力影響學校,言論非常不妥。儘管校務委員會有其裁決,但學生們拒絕接受,心中已認定「南榕廣場」是不二之名,學生會等社團往後舉辦活動,都會用南榕廣場這個名稱。
在南榕廣場事件中,衝在最前面學生社團是“零貳社”。零貳社的名稱,源自於台語「抗議」的諧音,代表青年願意對社會各種議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且勇於以實際行動挑戰威權。這個社團成立於2008年12月9日,歷經野草莓運動、反國光石化遊行、二二八銅像行動、成大校史事件、南榕廣場事件、成大清潔工勞權事件,成為成大最具反抗精神的學生社團。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林飛帆就是從零貳社脫穎而出。我到台灣訪問時,多次接受零貳社邀請,到成大分享中國人權運動的信息。我相信,誰來當成功大學的校長,並沒有那麽重要;而有零貳社的成功大學,和沒有零貳社的成功大學,絕對是不一樣的。
南榕廣場的爭議至今尚未畫上句號,校方缺乏“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勇氣,或許只有等到校長換人,死結才能打開。不過,我看到一則新聞報道:2014年4月6日晚上,成大零貳社的學生們自辦了一場「南榕廣場落成典禮暨鄭南榕追思會」,為呼應鄭南榕畢生追求言論自由,社長邱庭筠、前社長林易瑩兩人公開表態「我是成大學生,我是零貳社,我主張台灣獨立」。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出席活動,她謝謝學生舉辦追思會並邀家屬參加,稱讚學生不放棄南榕廣場名稱,讓人看見「言論之由」已發芽並長成花朵。鄭竹梅說,自己曾想遠離政治,但最後發現不可避免;對於學生主張台獨一事,她說樂見學生於勇於表達,如果有主張卻不能討論、不能表達,才是讓人害怕的事。
那一天,支持「南榕廣場」名稱的藝文界人士,送來了一份裝置藝術:外觀類似墓碑,擺放的圓型的草坪上,頗有墓園的味道。有人在碑前放花束,鄭竹梅也放了一束。零貳社的學生表示,送作品來的人已預料到作品很快會被校方移走,但基於支持與表態,仍然要做一件象徵的作品。
並非所有的成大教授都是王文霞的同類,成大工程學系副教授李輝煌在活動的致詞中表示,南榕廣場名稱被校方否決,但學生依然堅持並辦揭牌儀式,顯示年輕人對威權的挑戰,也呼應鄭南榕追求的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精神,活動顯示了成大將不只是企業的最愛,也會是啟發社會向前的動力。
以後,我每次到台南,都會來南榕廣場散步,以此表達對這個學生自我命名的廣場的支持。